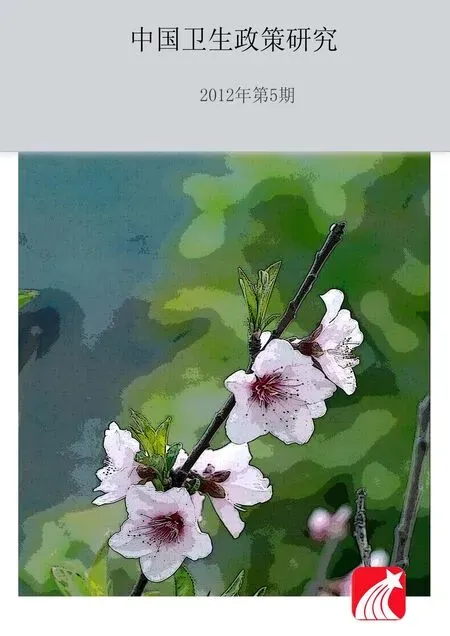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家庭医生制度探讨
谢春艳 胡善联 何江江 王力男 彭颖
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 200040
国外不同国家对全科医生与家庭医生有不同称谓,但内涵基本一致。家庭医生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最经济、最适宜”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模式,是以全科医生为主要载体、社区为范围、家庭为单位、全面健康管理为目标,通过契约服务的形式,为家庭及其每个成员提供连续、安全、有效、适宜的综合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的服务模式。我国新医改明确提出了“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目标,使社区成为实现医改目标的重要载体,国内很多地区在原有社区卫生服务和全科医生服务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多种家庭医生服务模式,但关于家庭医生的称谓各地不同,内容各异,尚在探索、完善阶段。本文主要是以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结合上海市实施的家庭医生试点探索与实践进行的一些思考,因而采用家庭医生的称谓,与国务院提出的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无冲突。
1 国内外关于家庭医生制度的研究现状
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因为其独特的优势,受到了西方很多国家的重视,目前,世界上约有50个国家或地区设有家庭医生组织,有15万名以上经过正规训练的家庭医生为患者提供基本健康服务。[1]在这些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家庭医生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对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比较成熟的国家的总结分析可以看到,尽管存在差异,但在总体上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具有以下特点:在服务目标上,家庭医生凸显“守门人”的作用,在健康管理、调节卫生资源、合理控制医疗费用、双向转诊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在人才来源上,各国对家庭医生有严格的资质审核要求,也建立健全了家庭医生培养制度;在服务内容上,各国家庭医生的服务项目覆盖健康管理各个方面,包括疾病诊断及处置、健康咨询、体检、转诊、家庭访视以及配合其它卫生机构开展专门项目如慢性病管理、计划免疫等;在服务形式上,一是建立与居民签约机制,二是在此基础上建立首诊制度;在服务经费上,最典型的是英国按照人头预付制度。
在我国,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大框架内发展的。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对社区卫生服务明确提出了完善服务功能的要求,强调“转变社区卫生服务模式,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坚持主动服务、上门服务,逐步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2]201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加强我国全科医学学科建设、建立全科医生制度。新医改明确提出了“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使社区成为实现医改目标的重要载体,而家庭医生制度的实施是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近两年,国内部分发达地区开始在原有的全科团队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基础上,探索借鉴国际经验,开展深化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改革的试点工作,如上海、北京[3]、深圳[4]、青岛[5]等,这些地区以常住或户籍居民为范围,建立与居民签约的机制,通过政策手段引导居民自愿在社区首诊,通过预约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指导转诊等服务[6],但均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家庭医生制度的制度设计、模式构建和实施过程仍存在很多困惑和不足,亟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等跨学科视角的研究还很缺乏。
2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家庭医生制度
在医学视角下,家庭医生制度是卫生服务到社区和家庭。在社会学视角下,家庭医生制度是“基于社区、以社区人群为服务对象”的卫生服务。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疾病谱的变化,医学模式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对健康的关注点也逐渐从治疗转向预防,从疾病管理转向健康管理。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社区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社区卫生服务是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的重要环节,是保障居民健康的重要力量,卫生服务模式要实现社区化,要以社会发展和社区建设的理论来指导,不是简单地把医学知识和医院服务应用在社区中。为了克服家庭医生制度缺乏社会参与和社会认同的瓶颈问题,应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
2.1 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的概念从表述的实际意义上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与国家公有形式的资本相对应的来自社会个体、非营利性组织的有形资本,如土地、劳动和资金等;二是来源于社会学对社会资本的界定,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7],后来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资本理论[8-9],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加拿大的政策研究基金会(Policy Research Initiative,PRI)在征求了全球许多社会资本研究者意见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给出了一个新的定义,即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信任、互惠、互助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借助于这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个人或团体能够获得各种资源和支持。[10]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社会凝聚力等。社会资本各要素状态良好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
与有形的社会资本相比,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资本是无形的,更强调社会结构中组织、个人动员和利用有形资源的能力和效率。[11]界定社会资本的因素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社会参与、信任与安全感、互惠与社会支持、人际关系网络、邻里凝聚力、非正式社会控制、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等维度。
2.2 社会资本理论在健康领域的应用
当前提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卫生领域,更多的是强调有形资本,对无形社会资本还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有研究将社会资本引入卫生和健康领域,阐述了社会资本的卫生保健功能,认为激活和利用社会资本是保证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12]国内健康领域对社会资本的测量目前还很少。哈佛大学和山东大学的一项合作研究同时测量了作为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组织成员身份和作为认知型社会资本的信任、互惠、互助,对山东省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进行的分析表明,个人层次的认知型社会资本与自评总体健康、心理健康正相关,村庄层次的认知型社会资本也与心理健康正相关。[13]在社会卫生资源利用策略研究中,研究者同时测量了道德与价值观、信任与安全感、友好互助、人际关系网络、对社区事务的关注和参与等多个维度的社会资本,研究发现,对居民健康具有保护作用的社会资本要素包括“认识本社区内较多的人”、“与同事相处融洽”以及“外出时请邻居照看房子”。[14]对参加新农合支付意愿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参保的重要因素之一。[15]
2.3 社会资本与家庭医生制度的关系
社会资本与家庭医生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
从微观层面来讲,社会资本的发展可以促使社区疏离状态和人际关系的转变,也有利于居民与家庭医生的社会互动模式转变。社区社会资本的引入通过改变城市社区的“原子化”和疏离状态,增强社区信任,改善人际关系,从而潜移默化的改变居民和家庭医生双方的态度、角色和行为,提高对家庭医生制的价值认同:居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家庭医生从被动工作到主动服务,进而转变居民与家庭医生的社会互动模式,由原本防范、对立的关系转变为基于信任和互惠的良性互动,反过来进一步提高居民对家庭医生制度的认同度和参与度,家庭医生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成就感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从宏观层面来讲,社区社会资本是家庭医生制度发展的内源动力。在服务市场的运行分析上,社会资本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间媒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营造一种文化、制度环境,引导人们的参与、合作与信任,成为影响个人态度、行为、决策以及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推动协调的行动来促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得出如下假设:在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社区里,交易成本降低,则制度的僵化或滞后所带来的阻力减小,从而效率也就提高。[16]
家庭医生制度的顺利实施,一方面需要政策和硬件支撑,包括财政投入、信息化建设和医保政策的调整等;另一方面,更需要价值态度的转变,尤其需要赢得社区认同和相关利益方等多方面的社会参与。家庭医生制度在完成居民健康管理功能的同时,还应发挥其提升社区功能、扩大社区支持网络、积聚社会资本的社会功能,实现健康管理与社会功能的整合。
3 建立家庭医生制度中社会资本的激活与培育
要建立家庭医生制度,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个关键问题。以信任、合作与互惠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不是某一社区天然拥有的,而需要经过有目的的培养、演进而逐渐生成,一旦无形的社会资本形成之后,往往会成为社区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制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培养这种无形社会资本涉及到很多因素,比如社会对社区概念的重视、社区整体环境的改善,需要在如何促进信任、寻求合作等方面努力,并且具体的措施与对策之间彼此协同。
结合我国社会文化及卫生保健实际情况,有学者提出社会资本的激活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法律、政策(包括卫生政策、法规)、管理规章制度等;二是教育、培植:道德规范教育、文化教育等;三是引导:文化舆论导向、精神鼓励、社会参与以及受益密切联系等。[12]
从微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的激活与培育需要通过多种形式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互惠与合作,例如居民委员会和志愿者等社会团体可以通过各种活动以增强居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强他们之间的社会资本。从宏观层面,结合家庭医生制的实施来看,社会资本的培育需要通过制度规范、政策引导以及舆论导向和宣传教育,从而推动微观层面的态度、角色行为以及互动模式的转变。在实施家庭医生制的过程中,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有力的政策引导有利于为社会资本培育和互动模式转变创造良好的环境,无论是社区居民还是家庭医生,其态度转变和角色行为的有效发挥均需要规范和引导。例如,居民对家庭医生制的理解需要通过社会动员和媒体宣传来实现,居民某些不合理的医疗需求和就医观念需要通过健康教育来引导,其就医行为和就医习惯需要通过签约、定点医疗、支付方式、报销比例等制度和政策进行约束规范。家庭医生的行为要通过提高待遇水平、绩效考核等各种激励机制进行规范引导,业务水平要通过培训和继续教育不断提升,另外,职业成就感需要通过提高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等精神鼓励进行引导。
4 形成社区社会资本的网络,推动家庭医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社区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制度是社区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社区发展规划应该纳入家庭医生制度;反过来家庭医生制度也离不开社区发展的外部环境和配套支撑。家庭医生制度应作为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核心和根本,不应仅仅局限于社区卫生的层面,还应拓展到包括二三级医院在内的整个医疗服务提供体系,成为整合医疗卫生资源以及社会、社区多方面资源的纽带。
除了社区微观层面的人际社会资本,家庭医生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还存在着多层次的中观组织层面和宏观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包括街道、居委会等基层行政力量;民间社会的很多非营利组织,各种社团组织如志愿者协会、社会工作者团体、社会福利组织、慈善机构、教会组织等;公共卫生机构、二三级医疗机构等其他卫生机构,这些组织对家庭医生制度的认同与支持,多种社会服务、社区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的整合与协同,也是有利于推动家庭医生制顺利实施的重要的社会资本,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整合各方资源。
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发育缓慢和不完全,给社区卫生服务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推迟了卫生服务“社区化”进度。[17]家庭医生服务如果没有社区非营利组织的扶持,家庭医生就会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缺乏和居民沟通的社会桥梁,不利于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同时,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是社区重要的人力资源之一,没有他们的合作,家庭医生服务工作团队工作方式就是一句空话。合理组织、利用社会资本的多层次性,就可以形成社区社会资本网络,有利于家庭医生制度的茁壮发展。
[1]杨秉辉,祝善珠.全科医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David Weller,James Dunbar.General Practice in Australia:2004[M].Fyshwick:National Capital Printing,2005.
[3]方芳.北京“片儿医”联系卡年内发到每户家庭[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半月刊,2008,10(7):30.
[4]王莹.青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亮点[J].山东社会保障,2008(4):20-22.
[5]赖光强.深圳市实施家庭医生责任制项目路径的分析与思考[J].中华全科医师杂志,2009,8(11):813-814.
[6]许岩丽,刘志军,杨辉.对中国卫生守门人问题的再思考[J].中国医院管理,2007,27(8):39-41.
[7]Richardson J G.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Education[M]. 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6.
[8]Coleman J S.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M].Cambridge,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9]Putnam R.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10]PRI.Social Capital as a Public Policy Tool(Project Report)[R].Canada:Policy Research Initiative(PRI),2005.
[11]冯国双,郭继志,周春莲.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中国全科医学,2002,7(7):478-488.
[12]卢祖洵.社会资本及其卫生保健功能[J].医学与社会,2000,13(1):3-5.
[13]Yip W,Subramanian S V,Mitchell A D,et a1.Does social capital enhance health and wel1-being?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2007,64(1):35-49.
[14]白玥.社会资本与社会卫生资源利用策略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6.
[15]张里程,汪宏,王禄生,等.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意愿的影响[J].中国卫生经济,2004,23(10):15-18.
[16]马吏,薛秦香,廉昭.试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影响[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20(1):99-100.
[17]刘军安,卢祖洵,孙奕.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理论及其实践缺陷[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4,20(6):324-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