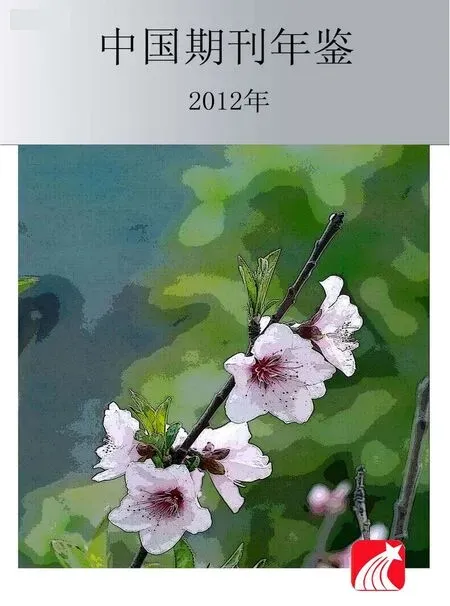关于新闻出版业的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发展
穆广菊
关于新闻出版业的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发展
穆广菊
为了推动我国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国家正在大力促进数字出版内容投送平台的建设。孙寿山副署长在今年七月刚刚闭幕的第四届数字出版博览会上提出“在新媒体环境下,加快大型数字内容投送平台建设,是推动产业快速发展的突破口”。不少大型出版集团已经或正在积极进行,比如中国出版集团的大佳网、天津天下出版网、重庆出版集团天健出版网等,显示出顺应时代变革的积极态势,还有不少出版单位正在筹建之中,一些终端阅读器厂商也进入了内容平台的转型期。
尽管也有不少出版社对建设平台的投入和产出尚在困惑,但是“平台热”迅速升温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怎样建设数字平台,大大小小新老平台之间是否存在竞争,以及相关的数字版权问题该怎样解决,面对数字出版大潮中的这一滚滚热浪,本文仅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一、战略谋划科学布局,行动才是硬道理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国家积极推动的是“数字内容投送平台”。什么是投送平台?简言之就是发行平台,但是“投送”的含义要比发行全面,如果说发行是从里到外,那么投送也同时包括从外到内,当然,现阶段提出的“投送平台”基本重心应是首指发行。
数字化出版是出版业态的一场革命。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毫无疑问要逐步实现出版管理流程、出版业务流程和出版多形态产品、出版投送等诸多方面的数字化转变,数字化投送是出版数字化转型的必然阶段,也是初级阶段,是实现数字出版的第一步。积极推动数字内容投送平台的建设,符合我国当下出版业的实际,也符合出版转型的起步性需要。我国出版业在经过较长一个阶段的观望、困惑、踌躇之后,率然开始了规模行动,这实则是一件好事,是一个进步,它将形成我国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性步伐。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出版单位都需要建设一个数字化投送平台?道理上讲应该是这样。那是因为基础存量资源数字化需要平台呈现,增量资源的数字化发行也需要窗口,它是转型的基础,转型本身就存在显化过去、解决现在和朝向未来的需要,而投送平台的建设使之成为可能。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也未必要一哄而上,不同的出版机构应该根据个体实际,战略谋划,科学布局,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切实可行的举措,落实数字化转型的步骤。
自建平台是一种方式,联合建设也是一种方式。2010年3月,法国8家大型连环画出版社联合推出了一个名为Izneo的“连环画数字化”发行平台。参加“连环画数字化”公司的8家出版社分别是:邦博出版社(Bamboo)、卡斯特尔曼出版社(Casterman)、达高出版社(Dargaud)、德莱古尔出版社(Delcourt)、迪皮斯出版社(Dupuis)、格莱纳出版社(Glénat)、勒隆巴尔出版社(LeLombard)和太阳出版社(Soleil),Izneo发行平台总经理雷吉·阿贝尔说,“将互相竞争出版社的手段集中到一起,可以更好地应对数字化的挑战,同时也有利于作者、出版商、书店和读者等传统图书各相关方的利益。”除了为8家股东服务外,Izneo发行平台也为其他出版社发行目录,这于多方都有利无害。
目前在国内数字出版领域,业已存在多家大型数字化投送平台,图书方面有方正、超星、中文在线、期刊方面有同方知网、龙源期刊等。这些平台经过多年的建设和积累,已经形成了集约性规模效应,较之一些出版集团陆续上线或筹备上线的新建平台,已经建立起较为成熟的运营团队、市场渠道和盈利模式。特别是方兴未艾的移动阅读基地平台的建设,更为出版数字化投送提供了展翅翱翔的无限空间。
那么,新老平台之间将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一定是竞争的关系吗?我不这么看。“专卖”与“超市”双轨行进,数字投送不拒绝纵横捭阖。2008年,龙源就当时合作的2000家刊社推出了18个模版的个性化网站,满足刊社没有精力和财力建设网站的应急需要。当时,有人担心地问,刊社有了自己的网站,还要你龙源干什么?我给他举了专卖店与大超市的概念,中国的杂志发行市场很大,关键是你怎样经营好专卖,又怎样利用超市去整合营销,是可以实现共享、双赢的。
随着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变化,龙源正在改进更加适合各家刊社实际需要的网站建设,不久可以看到更加方便刊社使用的网站平台。刊社只有愿意经营自己的网站才能与你这个集成平台有更好的合作。各家出版集团或出版社甚或是出版社联合体(有如法国连环画出版社联合的例子),打造好自己的投送平台、或以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式,或联合或借船出海或“搭伙借宿”来实施转型步伐,都是可取的、也是智慧的。
以雄厚的技术研发力量和多以横向资源聚合为特色的大型平台,不仅拥有较好的品牌影响力,并且已经建立起较好的市场渠道,就像美食一条街和一家独立的饭店、专卖店和超市大卖场,都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各有各的发展空间,更多的时候也需要合作和借势发展。
坊间有一种声音说,数字出版让一些技术运营公司领了先,如此下去,我们国有的出版行业不就没饭吃了么?这一观点首先是狭隘,其次是缺乏对数字出版内涵的深刻认知。数字出版是国家利益,是我国进入国际文化竞争的起跑线,也是增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推动国家出版业数字化转型途中,“技术公司”为我国的数字出版的发展起到了拓荒的作用。数字出版的成功是全领域的事情,不应有“嫡”“庶”之分。仅就转型期初级阶段数字投送这个环节,目前国内出版业的数字化内容规模、挖掘深度、加工水准、阅读体验其实还差很远,已经出版的存量内容资源和正在出版的增量内容资源都还没有借助数字投送做到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收入,可以耕耘的空间还有很大。我特别赞成今年第四届数博会主题的提法:传统与现代融合,内容与技术共生,这里除了字面本身的意义,我理解其还寓意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深刻含义。
同时,也需要指出,差异化和品牌化,才是平台胜出的关键,也是发展的方向。无论是自家打造平台,要纵深挖掘,种好自己的树,还是横向聚合资源的大型投送平台,发挥规模优势整合营销、抑或是鱼和熊掌兼得的方式,都应以差异化、品牌化经营为要旨。这里所说的差异化,是指的内容特色的差异;品牌化,一是指平台投送的内容必须是优质的、品牌的,另外也是指平台运营需要品牌打造,除了自身过硬,更需要推广给力。
“冰山在海里移动是很庄严宏伟的,这是因为它只有1/8露在水面上。”品牌的建立要做足“水下”的7/8。如果不是品牌性经营策略,风起云涌般建设起来的数字化投送平台,也会像春秋战国,混战一时,浪费资源和时间。
所以,数字化投送平台的建设,必须是战略谋划,科学布局,不是面子工程,也不能靠三分钟的热度,它必须是符合不同出版实体发展真正需要的。自办数字发行或授权数字投送,以自身适合的方式,稳扎稳打,才能获得数字出版征途上的猎猎旌旗。
二、走向数字出版深入阶段,实现知识服务
数字化转型期的出版单位,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是内容的锻造。数字化投送是转型期中的传统出版要走的第一步。出版数字化最终惠及民众的是知识服务。数字发行平台是针对上游资源的,知识服务更多意义上是面向终端读者的。WAP的发展更优于WEB,使得知识服务变得更加快捷。数字化转型要逐步在这其间要实现产品流程的数字化、特别是产品的数字化生产,借助高科技手段实现个性化、智能化知识服务。
从理论上讲知识服务是以知识选取与存储、知识重组与再生产、知识配送与输出为内容的服务,在数字出版现实中,应用户要求可以进行知识生产和再生产;出版单位的知识产品从选题策划到生产都可以一开始就接受市场检验,让用户去评判品质优劣和择优选取;
实现知识服务,丰富的数字内容资源是基础。无论是图书出版或期刊出版单位必须建立自己的数字内容库。英美等国的出版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了未来出版社将以出售数字内容为主要业务,如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兰登书屋、西蒙·舒斯特,他们较早完成了数千种数字图书资源的积累,目前已成为这些企业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实现数字化内容管理非常重要,数字内容的格式尤甚,文本格式将更加有利于知识的选取和重组。
实现知识服务,了解社会个性化需求是关键,在互联网时代,阅读差异化越来越明显,阅读诉求点也越来越具有多面性、时代性。同时还特别要兼顾用户的参与意识、以个性发展为中心的特性是传统出版在数字化转型时不能忽视的。
实现知识服务,高新科技是手段,数字出版可以把出版的内容通过交互式工具和平台迅即传输给消费者,人们能够直接得到他们需要的职业和专业的信息。
知识服务,服务是核心。为了协助图书馆由资源型图书馆向学习型图书馆转型。龙源期刊网通过对3000种期刊信息资源的深层开发,以信息和知识的搜寻、组织、分析、重组为基础,根据用户的问题和环境,融入用户解决问题的需要,提供有效支持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增值服务,推出了以“针对性知识服务”的电子阅览室新产品,从而改变了以刊为单位、让读者去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源的提供方式。
这一提供方式利用人工智力编辑和信息技术,提供人们可能需要的个性化信息和知识服务,实现了读者输入关键词瞬间自动生成个性化信息内容的知识推送服务打造学习型社会是传统出版走向数字出版的革命性意义所在。出版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知识,数字出版将使传播知识达到极致。
当然,一个成熟的数字出版平台需要技术、团队、市场、渠道等多种因素,这些,不一定每一家出版单位都能够具备,在整个数字出版流程中,可以有分工合作,有的可以定位为内容提供方,有些可以定位为运营平台,仍然需要在战略的布局下,选择适宜的方式发展,不一定要“通吃天下”。
三、数字出版呼唤版权保护原则创新,政府援手应对难关
传统著作权法的核心是先授权后使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解决,关键是要探讨实现授权的策略和手段。期刊的作者的追溯授权尤其具有实施难度。随着数字出版的深入发展,一方面,版权纠纷此起彼伏,作者诉讼频仍,律师推波助澜,法院案件高筑,另一方面出版数字化转型建设、网络内容服务仍在“蓬勃”生长着,国家也在大力推动着,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不断推出,更多的人依赖互联网的信息服务。尤其随着移动和终端阅读的兴起。数字化投送和出版从单一权利的授权向多种权利授权、由单一媒体的授权方式向多种媒体授权方式转变,使得网络环境下的版权问题变得更加沉重和突出。
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业界也有不少探讨,我认为,要首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新闻出版总署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出台之前的过渡性政策或行业发展管理条例,营造数字出版良性发展的社会环境。
为什么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我在不久前发表在《出版广角》一篇文章里,曾经援引过同样900多起版权纠纷,美国判侵权的只有几家,而我国则是相反,判不侵权的只有几家的例子。这反映出美国对国家利益的绝对保护态度。美国版权保护秉持内外有别的原则,他们的版权保护战略中,非常重视提升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扩大本国的版权利益;同时注意实现国内的版权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间的平衡,即对内执行创新先于保护,竞争优于垄断的版权保护政策。这一点我们的国家政府一定要看到。
对于当下网络环境下的版权纠纷之乱象,期待政府积极作为。不能把版权问题只看作是单纯是保护作者著作权益的问题,也不是数字出版企业要被官司缠绕多久的问题,事关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版权产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不仅要重视国内的版权保护立法与修改,而且要重视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的问题对数字出版的制约危害,在新的法律法规出台之前,能够从国家利益的角度,通过一些过渡性措施或行政手段,在保护版权的基础上,有效地促进产业顺利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今认为在网络著作权侵权责任问题上,应该重视责任归责原则,且慎用“停止侵权”的手段。她介绍了著作权许可制度的两个理论原则:一种叫做责任归责,没有著作权人的授权就不能使用,如果没有授权就是侵权;另外一种规则就是权利归责,相对来说就是给予补偿就可以使用,这是介入了公权利。到底采用哪种模式,取决于经济利益,要进行谈判。
如果谈判标底非常高的时候才用责任归责,应用上是不轻易判侵权的。权力归责,在美国使用上就是强制许可,先有一个合同进行谈判,谈不成的时候,有一个机构来进行估价。数字出版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情势迫切,建议政府方面建立一个这样的评估机构,这个机构的组成可有政府和行业协会、专业评估公证专家、数字技术统计工程师、知识产权律师等多方组成,是一个非赢利、客观、科学、公正的第三方存在。
版权保护的实质是为作者谋利益。文化知识类内容产品并非私密性的东西,只有传播才会产生更大的价值。著作权人、使用者、社会公众三者的利益并不是对立的,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达到互利共赢,各得其所的。从保护交易和流转角度考虑维权,不能太僵化地使用法律,在新的网络著作权法出台之前,政府可以出台一种介于法定许可的和授权许可之间的模式,在确保著作权人利益的前提下,针对存量资源数字化的追溯加工,如果能够规定期刊社有“完整使用”的授权资格,投送平台和数据库建设可以免去可能的法律风险;在使用者通过协议签署规定了著作权人的权益获得方式后,“行为人在使用他人作品之前已尽到正常注意之义务的前提下,可以不追究其责任”;如果互联网管理条例恢复原来24小时内撤除即不受法律追究的条款,也可以大大地减少法律诉讼的产生,这样做并不影响对作者著作权益的付出,但不是侵权赔偿。
期刊数字化转型,如何获得作者的授权许可,期刊社需明白不具有哪些权利,这是事关数字期刊业的安全运作、合法经营的重要问题。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我们要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具有发号施令的职能,现阶段可出台管理条例,要求出版单位做好与作者之间的使用许可合同。比如期刊社发布的征稿启事中可以明确相关著作权事项,作者投稿则表明作者通过有目的、有意义的积极行为(投稿)表示许可。这种许可方式属于默示许可。从使用者角度看,默示许可免去了与不特定的著作权人个别谈判的成本。
妥善解决数字版权授权问题,关系到文化创意产业和互联网服务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我们要积极地推动版权授权制度的改革,使法律制度更加符合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在现实与现有法律产生悖论的当下,政府或行业协会出台过渡性措施或许是解决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的有效路径。
(作者单位:龙源期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