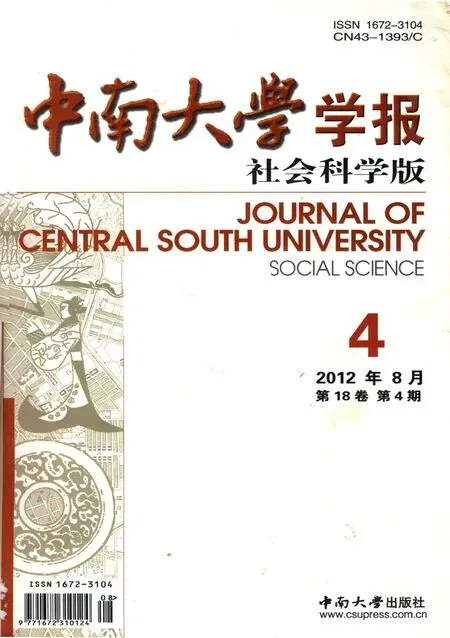《海华沙之歌》之神圣的空间和神圣的时间
张艳萍
(甘肃联合大学人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一生致力于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朗费罗在大学毕业演讲《我国本土的作家》(Our Native Writers, 1825)中呼吁,美国公民应该拿起笔来共同创作表达“我们民族特点”的诗歌。[1](274)而在他的那个时代,美国的民族性远远没有成长到足以代表美国身份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土著文化就成为确立美国民族诗歌身份的必要元素。朗费罗认为使美国作家的作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学的必要方法就是使用美国本土的素材。在他的那个时代,标志性的美国本土题材就是印第安题材。朗费罗自己身体力行,采用印第安题材创作了长篇叙事诗《海华沙之歌》。朗费罗这部诗歌的素材主要来自斯库克拉夫特的著作,即六卷本的《美国印第安部落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史学和统计学资料汇编》和《阿尔吉克研究》。其中,《阿尔吉克研究》收集了一组奥吉布瓦和奥塔瓦的神话和传说。这本书于1856年扩容并重印,书名改为《海华沙的传说》。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就是以奥吉布瓦人喜爱的恶作剧者麦尼博兹霍的故事为蓝本。这部采用印第安人的术语呈现印第安人的传说和习俗的诗歌,在出版后的头几个月就售出了数万册,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后来,《海华沙之歌》不仅被翻译成了每一种现代欧洲语言,而且被翻译成了拉丁文[2](66);不仅为朗费罗赢得了国际声誉,也为美国诗歌赢得了国际声誉。
朗费罗《海华沙之歌》的主要素材来源是斯库克拉夫特所收集的印第安神话传说。在那些印第安神话传说中,有一个人物形象颇具特色,那就是故事家伊阿歌,他以擅长讲述奇异的故事而声名远播。伊阿歌的成功在于他抓住了印第安听众求奇求异的心理。事实上,奇异正是印第安神话传说的基本特色。可以说,那些被朗费罗改造过的印第安神话传说大多具有奇异的特征。而这些奇异的神话传说必然会涉及一些神奇的主题。在印第安神话传说中出现频率较高而且体现了印第安人文化特质的一些神奇主题,包括变形、幻象、巨鱼吞人、人蛇大战、头部的秘密等等,不仅是朗费罗的兴趣所在,也是大众的兴趣所在。本文拟从神圣的空间和神圣的时间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切入,探讨《海华沙之歌》与斯库克拉夫特所收集的印第安神话传说的神奇主题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对立
神圣性与世俗性是相互对立的,二者之间保持着明显的距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圣性与世俗性之间毫无关系。实际上,神圣性产生于世俗性。神圣性如果与世俗性不发生任何联系,那么这神圣性就失去了意义。任何世俗的东西都可能获得神圣性。比如,一块石头,本是平常之物,但一旦使用者将其用作圣物,它就获得了神圣性,而与普通石头拉开了距离。一旦一种平常性的劳动与神圣性相联系,这个行为本身也就具有了神圣性。在提克皮亚妇女编织神圣的席子的过程中,编织者所处的方位、编织者的禁忌、编织者不被干扰等神圣性的表征,使编织圣席的行为与平常性的编织行为区分开来了。尽管这个活动并未涉及与神的直接联系,但它却与神圣性相联系,因为圣席是提供给寺庙用的,而寺庙是敬神的地方。在这个编织圣席的过程中,神圣性表现为“与世俗分离,充满了畏惧和威严,并附带着禁忌”。[4](78−79)所以,神圣性并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从世俗性中分离出来的。世俗性的东西因为个人或群体对待它们的特殊态度而变成了神圣性的东西。惟其如此,神圣性才在与世俗性的对立中显示出了特殊的意义。
二、《海华沙之歌》之神圣的空间
在“海华沙的禁食”这一章里,朗费罗描写了海华沙为人民的利益而禁食的过程。海华沙在森林里搭建了一座小屋,作为他禁食期间的临时住所。《海华沙之歌》中关于海华沙禁食的情节是从《孟达明或印第安玉米的起源》这则神话传说中移植来的。在这个神话传说中,禁食者是印第安青年文志。他的禁食,不是一般的禁食,而是人生中的第一次禁食,也就是印第安男子到了青春期以后举行成年仪式时进行的禁食。文志的家人在森林里为他选择了禁食的场所,并按当地的风俗为他搭建了一座禁食的小屋。那个地方离他家较远,这样就可以避免他禁食期间被打扰。[5](99)朗费罗在移植文志禁食的情节框架时,将文志在成年仪式上禁食这个细节删去了,而代之以海华沙为人民的利益而禁食和祈祷,这是为了突显海华沙的领袖品质,但是,海华沙的整个禁食过程与文志的禁食过程大致相同,因此,海华沙的禁食具有印第安成年仪式的禁食的特征。像所有的印第安成年仪式的禁食者一样,文志的禁食是在一个离家较远的僻静地方进行的。禁食者不是随心所欲地选择禁食场所的,而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来选择的。禁食的场所被认为是禁食者与神灵交往的地方,而文志确实在那里与印第安大神派来的孟达明遭遇了。和文志一样,海华沙也在禁食的地方与大神的后裔孟达明遭遇了。正如达瓦马尼所说:“神圣性天然地存在于信仰和仪式之中。”[4](80)换言之,仪式天然地包含着神圣性。因此,文志和海华沙在仪式上的禁食就充满了神圣性,而这种神圣性首先体现在其禁食场所的神圣性上,也就是空间的神圣性上。
恩斯特·卡西尔认为神话空间意识体现了神圣与世俗的分野。卡西尔是以知觉空间意识和几何空间意识为参照来审视神话空间意识的:人的感觉由于受到种种限制而无法感知空间的无穷性,因而也就无法感知空间的同质性。因此,知觉空间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是具体的,每一个位置都有相应的具体的内容。而几何空间是在对具体空间进行了高度抽象以后建构起来的,在几何空间中,连接成该空间的各点仅仅具有位置的规定性,除了它们所处的相对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外,它们没有具体的内容。也就是说,连接成该空间的各个点仅具有同质性,而不具有各自的特征。而在知觉空间中,每一个位置都有其确定的内容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神话空间与知觉空间是相似的。在神话空间和知觉空间中,每一个点、每一个要素都是位置和内容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位置有与之相应的具体的内容。东、西、北、南四个方向,并不是表示方向的本质相同的区域,而是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的事物。原始民族文化中有方向之神,即东方之神、北方之神、西方之神、南方之神以及下部世界和上部世界之神,这就说明,方向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进而被提升到了诸神的水平。在许多文化中,阴间都被安排在西方,这是因为西方是日落的地方,是光明消失的地方,因而那里就成了充满恐惧的地方;东方则被赋予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意义,这是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光明之源,所以东方就是生命之源,是充满希望的地方。在这些文化中,空间被赋予了特殊的情感和价值,每一位置和每一方向,都被赋予了具体的特征,而这一特征总是可以回溯到神话的基本特征,即神圣与世俗的分野。人在与实在的对峙中,树立起了把自己的感情和意志赋予其上的特殊屏障,这就产生了性质不同的领域。原初性的空间区别,是这样两类领域之间的区别,一种是普通的领域,一种是神圣的境界,后者是从周围事物中提升出来的。[6](94−96)也就是说,神圣的空间不是既定的,而是从普通的空间中提升出来的。一般来说,神圣观念是与独特的空间界限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界限的崇拜和对它神圣性的敬畏几乎在所有地方都以近似的手法表现出来。”[6](117)在罗马,有一位特定的神,即护界神,而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中,对庙宇界限的崇拜是十分普遍的。可以说,正是那种特定的界限,把神圣的区域从世俗的区域中划分出来了。
在《孟达明或印第安玉米的起源》中,文志的禁食是在森林中一个特定的地方进行的。在未被选定为禁食场所以前,这个地方是平淡无奇的,和它周围的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一旦被选定为禁食场所,这个地方就上升为一个神圣的存在圈了。在林中搭建的那个具有印第安风俗特点的小屋就是一个特定的界限,这个界限把这个地方与其周围的事物区分开来了。在这个划定的界限内,这个地方获得了它的特殊的意义。禁食的小屋,被视为神显灵的地方,被视为禁食者与神灵交往的地方,因而,作为禁食场所的这个特定的空间就具有了神圣的性质。海华沙的禁食与其原型文志的禁食是相似的,因而,海华沙禁食时在森林中搭建的那个小木屋,也是禁食者与神灵交往的场所,因而就与它周围的地方分离开来而具有了神圣的性质。因此,神圣性并不是客体固有的一种性质,而是客体在特定情势中获得的一种性质。人通过将某些价值区别引入平常性而赋予平常性特殊的意义,从而使其与世俗的东西区别开来了。可以说,任何平常的事物都有可能被人赋予有别于世俗性的意义而获得神圣性。事实上,在宗教思维那里,世界上的全部实在都被具体化为神圣的和世俗的两种类型了。在这种具体化的过程中,空间中的每一方向、每一位置都有可能在特定的情势下被赋予神圣的性质。而海华沙和文志禁食的所在地,就因为被确定为禁食的场所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从而与周围的其他地方区别开来了,这样,这个禁食场所就与其周围的地方之间形成了神圣与世俗的对立。而这种神圣与世俗的对立,恰恰体现了神话思维的空间意识的核心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海华沙之歌》忠实地再现了印第安神话传说所反映的神话思维特征。
三、《海华沙之歌》之神圣的时间
在神话思维那里,把空间划分为各个方向和区域与把时间划分为若干阶段的活动是平行进行的。神话情感并不把空间位置和方向看做单纯的关系的表现,而是把它们视为一个神或魔鬼。这种认识空间的方式也适用于对时间的认识。神话思维将一种特殊的神圣色彩赋予了时间总体和特定的时间片段,甚至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宗教中也保留着这种信念。例如,在波斯宗教中,从对光的普遍崇拜中,发展出了对时间的崇拜,包括对四季、十二月以及个别日子和时刻的崇拜。[6](122)“总的说来,神话的时间直观和空间直观一样,都是定性的和具体的,不是定量的和抽象的。”[6](122)正如一个个空间位置和方向被赋予了具体的内容一样,一个个时间片段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神话思维的上述时间意识,渗透到了较发达阶段的文化中。在那些文化中,一些重大的社会活动和宗教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时间里进行的。像战争这样的重大社会活动,往往是在某个特殊的时段里发起的,而其具体时间的确定可能与月相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凯撒的说法,阿里奥维斯杜斯直等到新月出现时才开战,而拉塞达莫尼斯则等到满月出现时才作战。而在宗教活动中,一些特定的活动被小心谨慎地安排在确定的时间和季节进行,如果错过了那个确定的时机,那些活动将丧失其神圣的力量。[6](122−123)例如,中国古代的高禖之祭就是在玄鸟至之日进行的。《毛传》在解释《诗经·大雅·生民》之“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时说:“禋,敬。弗,去也。去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7](1055)在这里,祭祀的时间被限定在“玄鸟至之日”,这个时间是不能更改的,这就是这个时间的神圣性的表征。而“支配所有这些事例的直觉是,如同空间一样,时间间隔和界限不只是思想的习惯区分,而是具有各自的固有性质,尤其是各自的本质和效力”。[6](123)每一个时间片段都有属于它们的内涵,甚至有它们的效力,因而这些时间片段被严格遵守,否则,活动将丧失效力。在中国的占卜之书中,例如,在《周易》中,每个时间间隔都有特定的本质或效力,因而时间选择与人的行动的得失利害之间有必然性的联系,每个时间片段、每个日子甚或时刻,都可能被赋予吉凶之意,人只有按照时间的进程展开或者约束自己的行为,才能逢凶化吉。由此观照神话思维的时间意识,其特质就不难理解了。
在神话思维那里,时间总体和时间片段都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一些时间片段具有不同于其他时间片段的神圣的性质,因而,神话思维中的时间和空间一样,也存在着神圣和世俗的分野。
在《海华沙之歌》中,海华沙禁食的时间是“七天”,这个时间和印第安神话传说《孟达明或印第安玉米的起源》中文志禁食的时间是一样的。在这里,“七天”是规定的禁食期限。禁食是一种仪式行为,所以,禁食期限是预先规定好的,而不是禁食者临时决定的。那么,为什么禁食的时限是“七天”,而不是更长或更短的时间呢?文志在成年仪式上禁食的期限被确定为“七天”,这说明“七天”这一时间片段在印第安神话思维中被赋予了神圣的性质。而这个时间片段的神圣性质很可能与神圣的数字“七”有密切的关系。
在理论知识体系中,数能够包容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内容,并将它们转变成概念的统一性。[6](158)但是,在神话思维那里,数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在神话思维中,数不是单纯的数字,它具有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独特的性质和力量。数的这种独特性能够渗透在那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实体中,使这些实体共享其独特性,从而使这些不同的实体具有了共性。[6](160−161)“在逻辑思维看来,数具有普遍的功能和意义,而在神话思维看来,数始终是作为一种原始的‘实体’,它把其本质和力量分给每一个隶属于它的事物。”[6](161)也就是说,所有被某一个数字所标识的事物,都享有了这个数字的独特性,从而获得与这个独特性相关联的全新的意义。在原始思维那里,数的整体甚至每一个特定的数都被一种魔力之光所环绕,而数的这种魔力会传递给与其相关的每个事物,使这些看上去完全相异的事物都具有数的这种魔力。可以说,数扮演着沟通世俗和神圣的调节者的角色。[6](162−163)
数的神圣化过程几乎是无法阐述的,因为每个数都可能成为神话解释和崇拜的对象。“不仅原始人的思维,就是一些庞大的文化宗教,也处处可见把一、二、三实体化的例子。”[6](163)数字“四”的普遍的宗教意义在北美一些宗教中得到了证实,数字“七”的尊贵性堪与之相比。数字“七”的神圣性从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化基地传播到了四面八方,不过,在没有或不可能有巴比伦−亚述人文化影响的地区,“七”也是一个圣数。在古希腊哲学中,“七”仍然带有这种神话−宗教特征,在基督教中世纪,教父们把“七”说成是完满之数。数字“九”与数字“七”分庭抗礼。在古希腊人和日耳曼人中九日间隔期与七日间隔期地位相当。[6](163−164)“由于简单数的这种神圣性扩展到复合数,由于不光三、七、九、十二等,就连这些数的积都具有特殊的神话−宗教力量,所以说到底几乎没有什么数字术语不能归入这种直觉领域、纳入这种神化过程。”[6](164)凡是与这些数字相关的东西都被打上了它们的神圣的印记。
印第安仪式中禁食的时间都是预定了的,因而几乎是不可更改的。罗伯特·H·罗伊指出:克劳印第安人从孩提时代起就被告知,要想成为伟大的人,要想在危难时刻确保成功,就必须赢得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保佑。但是,很少有人毫不费力地在梦中或者以其他方式获得幻象,大部分人要通过磨难才能获得神的青睐。寻求幻象的人,必须禁欲,其过程是十分确定的。一个想要得到幻象的人,必须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在那里,“他要禁止饮食四天”。[4](203)可见,禁食是一种仪式行为,因而,其时间规定是十分明确的。在印第安神话传说《孟达明或印第安玉米的起源》中,成年仪式的受礼者禁食的时间是“七天”,这个时限是预定的、不可更改的,禁食者的行为与这个时间片段之间有着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换言之,禁食是仪式行为,而仪式行为天然地包含着神圣性,因而“七天”这一禁食时限被赋予了神圣性。同时,由于“七天”这个时间片段与神圣的数字“七”相关,所以这个时间片段又被渗透进了数字“七”的神圣的性质。总之,“七天”在《孟达明或印第安玉米的起源》中是一个神圣的时间片段。而《海华沙之歌》移植了该印第安神话传说中的禁食过程,其主人公海华沙禁食的时限也是“七天”,因此,这个时间片段也具有神圣的性质。就此而言,《海华沙之歌》中的神圣的时间忠实地再现了印第安神话思维的特征。
神话的客体世界和经验的客体世界是不同的,而这种差异是由人类的认识方式导致的。人类对这两个世界的认识都离不开时间、空间和数等基本的形式,不过,在对经验世界的认识中,时间、空间和数是高度抽象化了的,它们不表现具体的内容,但在神话意识中,时间、空间和数都表示具体的内容,而且这三者都是在神圣的和世俗的对立中展现其具体内容的。通过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肯定,朗费罗把《孟达明或印第安玉米的起源》中的文志禁食的过程移植到了《海华沙之歌》中,自然,该神话传说中的神圣的空间和神圣的时间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就在《海华沙之歌》中得到了再现。可以说,朗费罗在对印第安神话传说进行创造性地重构时,敏锐地把握住了印第安神话思维中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的核心特征,即神圣与世俗的分野。就此而言,朗费罗对印第安神话传说的创造性重构,不仅体现了其以英语保存印第安文化的自觉意识,而且还赋予了《海华沙之歌》鲜明的印第安色彩,为构建有别于英国文学的美国民族文学探寻到了一个有效的路径。虽然朗费罗昔日的光彩已经黯然失色,但其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所作的重要贡献不应被遗忘。
[1][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M]. 李增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2]See Jay, Parini,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oetry[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3][法]E·杜尔干. 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M]. 林宗锦, 彭守义译.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4][意]马利亚苏塞·达瓦马尼. 宗教现象学[M]. 高秉江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5]Henry R. Schoolcraft. The Myth of Hiawatha and Other Oral Legends: Mythologic and Allegoric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Philadelphia: J.B.Lippincott & Co; London: Trubner &Co,1856.
[6][德]恩斯特·卡西尔. 神话思维[M]. 黄龙保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7][唐]孔颖达. 毛诗正义(下册)[M]. 十三经注疏[Z].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