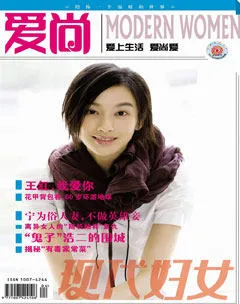避免校车事故当始于对每一个生命的敬畏
朋友与爱情
人为什么需要朋友?朋友的功能一是分享,二是分担。分享的是快乐,分担的是痛苦。而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其实并不需要朋友。他的快乐可以自己独享,他的痛苦可以独自承受。
说到底,人是孤独的。孤独地来到人世,孤独地离开人世。在肉体上也许可以不那么孤独,但是在精神上,人绝对是孤独的,除了有极个别精神上的朋友,而这种朋友不可强求,只能是各种因缘际会的自然结果。
爱情这个东西很奇妙,它的理想形态应当是肉体朋友和精神朋友合二而一的一个实体。这两种性质能恰好凑到一个人身上的几率真是太小了,可遇不可求。我相信,很多剩男剩女就是在等待这个人,等待自己生命中这个可遇不可求的奇迹。
总有人问我对剩男剩女有什么样的规劝,我的规劝是两句话:一,如果你很想结婚,那就不一定非要等到爱情不可,跟一个仅仅是肉体的朋友或者仅仅是精神上的朋友结婚也无不可;二,如果你并不是很想结婚,而且一定要等待爱情,那你内心要足够强大,要做好终生独身的准备,因为爱情发生的几率并不太高。
——李银河,学者、社会学家。
中国人的集体浮躁
那天,从温哥华回京,旁边是一个中年男子,看言谈举止还是一个有点层次的企业老板,但在飞机上基本没看到他安静过:看电影没超过五分钟,打游戏没超过两分钟,看报纸不超过一分钟……我在想,他如果懂得一点发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多好。
浮躁,真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吗?更深的原因不去分析,我们只看看现在人们的一些普遍行为。先说工作。据说在北京能在一个公司待上三年的人基本就是老员工。对财富的渴望更是浮躁,恨不得明天世界的财富全部跑到他那里去,没有一种适可而止的态度。爱情、家庭也是如此。爱情也是短平快,注重外在的东西;对家庭也是如此,对孩子,认为能拿钱去名校就是家长对孩子最大的贡献,不愿点点滴滴去做那些影响孩子一生和性格的事。
对于知识、学历之类的东西,更是五花八门,文凭可以买,学历可以造,头衔就靠权力;宗教信仰也想速成,不是信教,而是信效益,人家去教堂、庙宇都是想去向神忏悔、赎罪,用宗教寄托来净化心灵,我们去神庙就是想立竿见影,求神保佑发财。
中国人的集体浮躁就是那么回事,今天也是说说而已,下面该浮躁还是继续,至于继续到何时,连神仙都不清楚,我们又奈何?
——刘旗辉,商界传媒董事长、总编辑。
避免校车事故当始于对每一个生命的敬畏
校车事件一次又一次拨动着我们的神经,从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的校车事故到江苏丰县校车侧翻事故,校车再次成为时下最热的焦点之一。
一系列的校车事故带来的反思与措施铺天盖地,但仍未阻止这些生命的陨落,当我们溯本求源时,总会把矛头指向政府部门与学校的监管不力、投入不足与法制的不健全之上,然后各种亡羊补牢的举措竞出:“大力排查校车隐患”、“采购先进校车”、“出台相关法规”等等,络绎不绝。接下来是另一起事故的发生,另一群孩子的离去。
事后我们常看到因此落马的失意官员、被家长唾骂的校长,却不会在任何追悼会上看到他们的忏悔。保护生命倘若不是出于对生命最为直接的敬畏,那么任何举措都可能变成被篡改为徒有其表的“安全措施”,其下暗流涌动。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保护生命的经验,却仍可能学不会以生命去敬畏生命的姿态,这比灾难本身更为不幸。
——姜子健,自由媒体评论人。
“海派清口精英奖”何干“娱乐入侵”校园
2011年上半年,“海派清口精英奖”在复旦大学设立。有人质疑,海派清口在复旦设奖学金是娱乐文化又一次入侵校园。
“海派清口精英奖”设立之初的目的是“以培养精英人才为重点,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大学生和特殊人才,并鼓励他们参与慈善事业。”可见,并没有限定获奖者必须喜欢海派清口,或者是周立波的粉丝。因此,质疑海派清口乃是娱乐文化入侵校园的说法,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只是看到了冠名权,就指鹿为马。
周立波确实很火,是上海娱乐界的大腕,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让海派清口焕发新生,重新包装后赢得市场认可,每一场演出都是观者云集。他在自身事业有成之后,能够捐出资金来,在高校设立“海派清口精英奖”,乃是一种回馈社会、回馈教育的个人行动。
学生的个人爱好只能引导,却无法强制,有人就是喜欢周立波,喜欢海派清口,你又能怎样。因此,只要不将奖学金和爱好拉在一起,就是可以忍受的。
——江德斌,自由撰稿人。
(责编 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