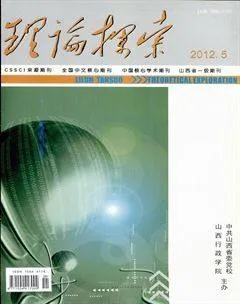社会怨忿情绪及其化解
〔摘要〕 社会转型期,部分群体中存在着怨忿情绪,并有明显向其他群体扩散的趋势,存在从浅层次向深层弥散型怨忿转变的危险,以极端和暴力方式表达怨忿的案例越来越多。社会怨忿情绪不利于政府政策执行、民众有序政治参与和政治体制改革环境的营造,破坏经济建设环境,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怨忿情绪的产生,既有经济根源,也有政治根源和社会根源。化解怨忿情绪,应加大治本力度,采取综合性措施:着力消除社会转型期诱发怨忿的结构性因素和物质诱因;通过提高公民的效能感,消减其“无能感”,消除怨忿情绪产生的主观诱因;构建有效的阻断机制,防止怨忿情绪的扩散;建立怨忿情绪的消融和理性释放机制,不断消解已形成的怨忿情绪。
〔关键词〕 怨忿情绪,特点,危害,主要根源,化解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5-0099-05
根据舍勒的定义,“怨恨是一种具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由此看来,怨忿产生的原因在于,由于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报复冲动,“既在内心猛烈翻腾,又感到无法发泄出来,‘只好咬牙强行隐忍’——这或是由于体力虚弱和精神懦弱,或是出于自己害怕和畏惧自己的情绪所针对的对象” 〔1 〕 (P10 )。从本质上讲,怨忿是一种潜藏在内心的不易2e98dc6db9d82aae6d3dd88f6a2018c6af97c5ff60dc665078876c55cedb5777化解的强烈仇恨感和憎恨感,是一种最可怕的愤怒。这种情绪虽然在平时隐于无形,但如果忽视化解和疏导,一旦产生,不仅不会自动熄灭,而且会愈燃愈烈,并产生极坏的影响:在对象上它会产生扩散和转移,由针对特定对象的怨忿演变成弥散性怨忿;在强度上会逐步加深,由一般的“怨”变成刻骨铭心的“忿”;在主体上会自动传染,由少数人的怨忿变成普遍的怨忿。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导致的利益分化、腐败和社会底层权利保障困难等原因,使怨忿情绪在部分群体,尤其是在弱势群体中滋生蔓延,已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破坏社会和谐、制约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通过改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现代化的目标,不仅需要妥善解决物质利益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同时必须及时化解心理和情感层面的无形矛盾和问题,塑造健康人格与和谐心理。为此,本文尝试在分析当前中国怨忿情绪的特点、危害和产生根源的基础上,探讨有效化解怨忿情绪的对策。
一、社会怨忿情绪的特点和危害
(一)社会怨忿情绪的特点。当前,社会怨忿情绪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主体看,主要集中在弱势群体,但有明显向其他群体扩散的趋势。当前怨忿情绪主要集中于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和老弱病残困等群体,但是,怨忿主体有向包括国有非垄断行业的普通职工、普通市民和普通知识分子扩散的苗头,值得高度注意和警惕。当前,我国虽然尚缺少关于怨忿主体分布的调查数据,但现有研究成果可以从侧面揭示其向其他群体扩散的趋势。有研究显示,在当代中国的大城市,“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比例达到了14.6%,比例之高是很罕见的” 〔2 〕。另据《领导科学》杂志社的调查,甚至“有45.1%的受访党政干部认为自己属于‘弱势群体’”(《约稿启示:“领导干部弱势心理”专题研究》,载于《领导科学》2011年第3期)。而这些人之所以自认为处于社会“下层”或“弱势地位”,主要是由于明显的效能感低下和面对挫折的无奈情绪所致,而根据舍勒的理解,这些既是怨忿情绪生成的关键中介因素,又是怨忿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上述自认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即使不是怨忿的主体,也往往是怨忿的易感人群。
2.从涉及的对象看,以浅层具体型怨忿为主,但存在向深层弥散型怨忿转变的危险。即虽然目前的怨忿主要针对具体的人或具体的政策,但却有深化为针对体制和制度的危险。这一方面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的不完善不合理,再加上快速的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对一些群体造成“体制性”伤害;另一方面,如果浅层的怨忿长期得不到化解,则会不断积累和加速,不仅会导致怨忿的对象发生扩展、改变和转移,而且也会使得怨忿向更深的层次发展。由于我国利益表达通道不够通畅,情绪合法宣泄渠道缺失,再加上疏于对民众心理的研究和疏导,导致怨忿情绪有传染和蔓延的危险。
3.从表达方式看,以口头怨忿批评为主,但以极端和暴力方式表达怨忿的案例越来越多。一方面,怨忿的最突出表达是民众以“仇官”和“仇富”为主的怨忿批评,这种怨忿批评既可见诸街头巷尾和茶余饭后的闲谈,也可寓于广泛流传的调侃式段子和顺口溜,同时还有网络论坛和微博上的宣泄式言论。另一方面,值得高度注意的是,近年来以极端和暴力方式表达怨忿的案例激增,突出表现为群体性事件的暴力燃点越来越低,尤其是大量“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群体性暴力破坏。另外,暴力抗法行为、自杀、自焚式维权、灭门式杀人等残忍行为,以及针对无辜者的暴力行为也越来越多。对于这些行为,政府往往将其归咎为法治观念淡薄或者人格变态,其实,这些行为背后的社会怨忿情绪更值得注意和深思。
(二)社会怨忿情绪的危害。当前怨忿情绪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怨忿情绪不利于政府政策执行、民众有序政治参与和政治体制改革环境的营造。具体而言:首先,破坏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和谐关系,提高了政策执行的成本,容易造成政策执行的梗阻。民众对政策的认同、配合和参与是政府政策顺畅执行的前提。但目前的情形是,在有些地方,怨忿情绪蔓延造成了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出现了抵触、对立情绪,民众对政府政策虽不选择暴力对抗形式,但采用“不服从、合法抗争、温顺的拒绝”等不合作态度,或者如斯科特所描述的运用“弱者的武器”,即采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纵火、暗中破坏” 〔3 〕 (P2 )等形式进行消极抵抗。所有这些行为,都会大大提高政府在执行中的成本,并使政策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阻碍民众有序政治参与的形成,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众有效而有序的政治参与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有序政治参与需要完备的参与知识和娴熟的参与技巧,更需要良好的心态。在怨忿情绪支配下,民众参与行为只会在“‘政治冷漠’和‘政治参与爆炸’之间游走极端”。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预防因情绪化参与而导致政治参与无序化和暴力化,已成为困扰许多基层政府的难题。而要解决此难题,必须先化解和疏导情绪化行为背后的怨忿情绪。
再次,怨忿情绪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考虑民众的承受力和接受程度,必须在和谐稳定的环境中进行。“文革”和苏联东欧的教训都警示我们,民众怨忿和政治动荡是互为表里的,在怨忿弥漫和政治动荡的环境中进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更是不可能的。当前,作为怨忿表达形式的怨忿批评的出现,极不利于和谐稳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环境的营造,因为这种“缺乏任何积极目标的不分皂白的批评”,“并非真想消除不良现象,只是以之为借口;而且,对于所抨击的状况的任何改善,不仅不能令人满意,反而只能导致不满,因为它们破坏了谩骂和否定所带来的不断高涨的快感” 〔4 〕。如果不能有效地化解怨忿情绪,政治体制改革将难以被认同,甚至会遭到一味地否定、贬低和责难,最终的结果是,一些改革会受到阻滞,有些改革甚至根本就无法推行。
2.社会怨忿情绪增加交易成本,破坏经济建设环境。首先,怨忿的存在会破坏和谐的劳资关系,增加管理成本。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管理者和员工、劳方和资方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之一,基于员工归属感的企业文化可以有效降低管理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但是,由于部分员工,尤其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中怨忿情绪的蔓延,助长了日趋高发的劳资冲突,如珠三角每年因劳资纠纷引发的农民工百人以上群体性事件有几十起,小的冲突更是层出不穷。尽管这些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员工的怨忿情绪不仅是主要原因之一,而且使得冲突更加难以解决。其次,由于“仇富”心理的蔓延,诱发越来越多的“穷”与“富”之间的冲突,不利于经济发展。毫无疑问,为富不仁、骄横狂妄的富人只是极个别现象,但由于“仇富”心理的作用,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隔阂和摩擦。甚至一句“富人欺负穷人”的谣言就可以引发一起恶性群体性事件,富人群体经常会成为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和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冲击对象,震惊全国的池州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同时,“仇富”心理也使企业的外部环境恶化,针对企业的恶意破坏、偷盗、讹诈等事件明显增多。在此背景之下,以企业家为代表的一些富人惮于“仇富”情绪造成的心理压力和恐慌,将大量资产和财富转移到国外。
3.社会怨忿情绪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首先,怨忿情绪导致“非直接利益冲突”频繁发生,对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近年来,大规模“非直接利益冲突”,诸如瓮安事件、池州事件,都曾卷入数万名普通群众,虽然他们参与事件的具体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怨忿无疑是他们共同的心理特点。其次,怨忿情绪不利于和谐阶层关系的构建。随着我国阶层的构成日趋多样化,阶层差距更加显性化,阶层矛盾更加复杂化,阶层冲突在某些方面和层面开始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和谐阶层关系,本来就是各级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考验。而由于怨忿情绪的蔓延和作用,放大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深了阶层间的隔阂和猜忌,制造了阶层之间的误解和仇恨,使得阶层整合更加困难。
二、怨忿情绪产生的主要根源
当前在部分群体中滋生和蔓延的怨忿情绪,既有结构性根源,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其生成过程是一个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一)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不公平因素,消费主义盛行背景下贫富差距显性化对弱势群体的巨大刺激,是怨忿情绪产生的经济根源。首先,从经济发展过程角度看,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成本分摊和成果分享不公平现象,导致部分群体的生存状况相对变差,这是怨忿情绪产生的主要经济根源。成本分担高而成果分享少的群体主要包括两类群体:一是人数庞大的农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有形的税收和无形的“剪刀差”,以及土地征收等各种形式,从农民中提取了巨额财富。但是,国家既没有给予他们合理的补偿,也没有给他们提供应有的社会保障,出现大批“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二是国有和集体非垄断行业的工人,尤其是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和失业工人,也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他们曾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过巨大牺牲和贡献,但最终被以廉价“买断”的形式逐出企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官员、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层的待遇有了巨大提升,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员的灰色收入甚至是黑色收入,少数企业管理层利用职权或者企业改制的机会,侵吞、私分公有资产行为的存在,无疑会使相对被剥夺阶层将自己的境遇归因于此,进而产生对官员、管理层的怨忿。
其次,消费主义盛行背景下贫富差距显性化对弱势群体的巨大刺激,是怨忿情绪产生的另一经济根源。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传入中国并开始流行,金钱和物质不但是经济上成功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些范围内甚至成为了社会评价的唯一标准。与此相反,知识、劳动、品德和精神价值相对贬值。不仅如此,在不少地方金钱攀附于权力,甚至与权力结盟,个别黑社会头子头顶人大代表的帽子,以及纳税多可以换取副镇长甚至副县长头衔的现象就是例证。在此背景之下,非正当致富者不仅没有负罪感,反而大肆炫富,生活奢靡,甚至个别暴富者叫嚣拿钱可以买穷人的命;相反,当普一些人不仅靠知识难以改变命运,靠勤劳难以致富,而且遭受鄙视和侵害的时候,所能够感受到的恐怕就只有恼怒和怨忿了。
(二)腐败和公民权利保障低效是怨忿情绪产生的政治原因。首先,腐败是怨忿情绪产生的最主要政治根源。虽然腐败在各国都存在,但在中国腐败造成的怨忿更加突出。这主要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作为公仆的官员应该是绝对清廉的,但现实与理论形成了强烈反差。在此背景之下,腐败所造成的危害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心理层面的。有研究显示,腐败和不公是民众感觉最不满意的两个问题。
其次,弱势群体权利保障和救济的困难是诱发怨忿的另一主要政治根源。与社会结构的断裂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权利上高度失衡”的现象。以农民、下岗工人等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既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也缺少利益表达的组织和能力,导致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权利贫困;同时,弱势群体也缺少救济自身权利的有效通道、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在此背景之下,权利受损而又救济无望的弱势群体,当然成为了最容易产生怨忿的群体。
(三)社会流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由于社会建设滞后导致的民生困难是怨忿情绪产生的社会根源。首先,以“官二代”和“富二代”为代表的一部分强势群体挤占了本来属于知识精英的机会,堵塞了一部分弱势群体的上升通道,不仅造成普通知识分子群体的怨忿,而且伤害了社会普遍的公平感。由于干部录用机制的不完善和不成熟,导致权力和金钱在社会流动中扮演了不应有的角色,造成社会流动中的大量腐败和不公平现象。尤其是随着大学的大规模扩招,一方面,付出巨大代价,因而也报有莫大期望的普通学子就业困难,向上流动无望,另一方面,少数不学无术的官员和富人子弟靠着权力和金钱,抢占了优越职位,造成了“官二代”、“富二代”对“农二代” 、“贫二代”在社会流动中的剥夺,当然也造成了后者对前者在心理上的怨忿。
其次,社会建设滞后造成的对弱势群体的伤害,是怨忿的另一社会根源。一方面,我国社会建设滞后的特点不仅不会影响强势群体的生活,反而会给其带来优越感;另一方面,广大弱势群体由于较少享有政府提供的福利,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各个方面面临巨大的压力,有些人甚至被逼入绝境。这种强烈的对比也会使部分弱势群体产生怨忿情绪。
三、社会怨忿情绪的化解
根据舍勒的观点,在客观方面,怨忿情绪一般以“伤害”或“价值攀比”为起点,部分群体因遭“伤害”而产生报复感、恼恨感、阴恶和恶意,或因“价值攀比”心生妒嫉和醋意;在主观方面,怨忿主体必然经历长期的“无能体验”的折磨。因伤害或攀比而产生的负面感受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得到发泄,经过“无能感”的发酵、沉淀而成怨忿。同时,怨忿情绪一旦形成,不仅不会自动消失,相反,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自我强化机制。基于对上述怨忿生成和传播特点的理解,笔者认为,要化解怨忿情绪,必须从多个方面和层次入手:既要消除怨忿滋生的结构性诱因和物质根源,又要通过增强效能感化解诱发怨忿的中介性因素即无能感,同时还必须尽快建立阻断机制以防怨忿情绪的扩散,最后还必须建立有效的消融和引导机制,逐步化解郁积于部分群体心中的怨忿情绪,防止其破坏性发泄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着力消除社会转型期诱发怨忿的结构性因素和物质诱因,这是化解怨忿情绪的前提。首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发展,消除城乡壁垒、行业垄断、所有制差别等各类“体制性歧视”对弱势群体的伤害,使发展成果由全社会更加公平地共享。为此,一方面,应在制度和体制层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制度设计的公平性,从而促进社会的包容性与增长的共享性。因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同样也是化解怨忿情绪的前提和基础;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同样也是构建健康社会心理的根本保证。当前,尤其应通过就业、收入分配、税收、财政和金融等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使农村、落后地区、非垄断行业和弱势群体能公平地享有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在政策层面,应通过加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转移支付和扶贫开发力度等方式,尽快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使包括各类弱势群体在内的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其次,加大对公共权力监督和约束的力度,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更加充分地保障人权,消除诱发怨忿情绪的政治方面的结构性诱因。政府的一些不当行为和公共权力既是怨忿的主要对象,也是怨忿情绪产生的主要根源。因此,要化解怨忿,一方面,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构建更加科学的公共权力结构体系,使公共权力的边界更加明晰;通过厉行法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等多种方式,加大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力度,使公共权力的运行方式更加规范;同时,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制,减少或杜绝公共权力不当作为对公民权利和尊严的伤害。另一方面,必须真正坚持以人为本,摒除权力本位,树立权利本位观,切身保障和实现公民各项人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权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民主的精髓在于保障民权。要消除怨忿情绪的政治根源,必须将民权保障放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更加重要的位置,创造全体公民平等而充分地享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政治环境。
再次,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也是消除怨忿结构性诱因的重要举措。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导致的民生困难,是底层社会民众产生怨忿情绪的直接和主要原因。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解决底层民众在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难题,可以有效预防底层社会群体因生存困难而诱发的怨忿情绪。同时,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维护民众权益,保持社会良好秩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权益受到保障、心情更加舒畅,也是化解怨忿亟需采取的措施。
(二)通过提高公民政治效能感,消除怨忿情绪产生的主观诱因。政治效能感是个人对自身参与和影响政治的能力,以及外部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的认知,包括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两部分,前者是指个人对政治系统和政治决策施加影响的能力的认知和信念,后者指个人对所处的政治体系的公正、效率等方面的认知,包括政府公平程度、是否对公民具有责任感以及政府的绩效等等。作为民众评价政府与个人本身政治能力的重要依据,政治效能感的提高有利于培养政治信任和信心,因而是消除民众政治“无能感”,进而化解怨忿情绪的重要途径。就我国目前现状而言,提升公民政治效能感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增强公民的政治自信和信任,克服政治“无能感”。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公民既可以保障和实现自身合法权益,体验自身的政治价值,从而增强政治自信,克服政治无能感和政治疏离感;同时,有序政治参与的过程本身又是有效的政治教育过程,公民通过自身的政治参与,将其政治理想付诸实践,对公共权力构成有效监督和制约,提升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可以有效增强公民对政治系统和政治决策的认同感,增强其外部政治效能感,克服政治偏见和怨忿情绪。就我国当前现状而言,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仅需要尽快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创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方式,增强政府主动吸纳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必须大力培育成熟而理性的“政治人”,解决当前我国公民宏观政治知识有余而政治参与知识不足,参与激情有余而参与技能缺失,参与行为激增与理性程度及法治观念不足的问题。
其次,建设责任政府和回应型政府,增加政府与公民的互动,重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合理诉求长期被公共部门漠视、敷衍、推诿甚至野蛮拒绝,是公民产生无能感的重要来源,也是其怨忿政府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消除公众的无能感,必须同时进行体制改革,构建责任政府和回应型政府。通过构建对政府的内外控制机制,保证其承担应有的“道德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上的责任”,并“积极地回应、满足和实现公民的正当要求” 〔5〕。同时,通过建设回应型政府,构建回应机制,增强其回应能力,畅通官民互动与协商通道,实现从单向度的政府管理向官民合作的公共治理转变。通过上述途径,转变政府形象,冰释怨忿群体的政治冷漠和无能感,消融其心中的怨忿情绪。
(三)构建有效阻断机制,防止怨忿情绪的扩散。怨忿的传播是怨忿之毒再生的重要方式,因此,要化解怨忿情绪,必须净化舆论环境,消除怨忿传播的土壤,同时切断怨忿传播的主要途径。首先,营造理性宽容的政治文化氛围,消除怨忿情绪传播的土壤。“宽容使得差异性存在,差异性使得宽容成为必要” 〔6 〕 (P2 ),“‘差异性社会’是贯穿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的基本国情” 〔7 〕。面对经济社会日益分化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基本国情,我们不但需要在制度层面构建协商、谈判和妥协的政治机制,而且亟需在观念和心理层面营造理性宽容的氛围,避免怨忿情绪的蔓延破坏阶层和谐的基础。通过营造理性的氛围,使民众理性地追求利益、看待差异和处理矛盾,防止嫉妒心理、阴恶情绪、报复冲动等非理性情绪的散播蔓延;通过培育宽容的政治文化,使民众胸怀宽广,能够容忍差异、宽恕对手,避免摩擦、误会和仇恨的扩散。
其次,加强对舆论和媒体的管理,尤其要加强对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切断怨忿情绪扩散的主要渠道。负面舆论,尤其是其中的怨忿批评,既是怨忿的主要表达方式之一,又是怨忿的主要传播形式,而媒体,尤其是网络论坛、微博、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则是其传播的主要载体。因此,要防止怨忿情绪的扩散,必须加大对舆论和媒体的引导、管理力度。一方面,“加强舆情分析研判,加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引导,从群众关注点入手,科学解疑释惑,有效凝聚共识”,增强主流政治文化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针对舆论中的各类怨忿批评,以事实真相为基础,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和喜闻乐见的语言,给予有力的批驳,占领和巩固舆论阵地,阻止怨忿批评的扩散及其对民众的毒害。同时,贯彻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阻止怨忿情绪在网络等新兴媒体中传播和蔓延。
(四)建立怨忿情绪的消融和理性释放机制,不断化解已形成的怨忿情绪。化解怨忿不仅要防止增量,更要消除存量。怨忿作为一种心灵的自我毒害,一旦形成则不会自行消失,必须借助外界的干预方可清除。要消除现有怨忿情绪,首先,应该通过加强社会心理的疏导和服务,建立怨忿消融机制。为此,需要改善对底层群体的心理服务,增进对他们的心理关怀,及时发现并疏解包括怨忿情绪在内的各类不良心理和情绪。通过大力发展专业化的、规范的心理服务机构,提供社会化心理咨询和心理救助服务,建立个人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对因各类挫折而产生嫉妒、报复感、阴恶、恼恨感等不良情绪的人群进行疏导和救助,帮助其主动进行心理疾患的治疗和康复。
其次,建立有效的社会情绪“减压阀”,引导怨忿情绪通过理性释放走向化解。对于怨忿情绪,压制的办法和放任自流的处置方式都是错误的,前者虽可换一时平安,但会使其走向更深的怨忿,后者则容易造成严重的社会破坏。正确的方法是通过社会情绪的减压阀机制,引导其理性地和平地进行释放,从而最终走向化解。而要建立社会情绪减压阀,不仅需要政府转变畏惧和拒绝民众批评的观念,而且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引导公民理性地行使其批评、建议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等权利,通过充分的表达、和平的对话和有效的协商,这样既能使部分群体胸中的怨忿得到理性和平地发泄,又能使政府在更好地掌握舆情的基础上提升治理水平。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M〕.罗悌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2〕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J〕.社会,2005,(1).
〔3〕〔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4〕成伯清.“体制性迟钝”催生“怨恨式批评”〔J〕.人民论坛,2011,(18).
〔5〕张成福.责任政府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
〔6〕〔美〕迈克尔沃尔泽.论宽容〔M〕.袁建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任 平,王建明.论差异性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未来〔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5).
责任编辑 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