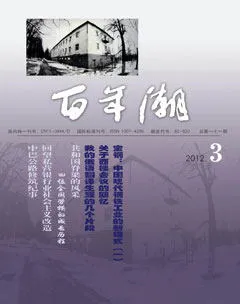我的俄语翻译生涯的几个片段
新中国成立前夕乃至20世纪60年代,我作为一名俄语翻译人员,参与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国内活动,见证了一些颇具影响和教育意义的事件。这里,仅择取几个片段,做一追述,以飨读者。
参加第二届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
1949年6月30日,正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际,我党派出一个由肖华将军率领的各民族青年、各个解放区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文艺工作者上百人组成的青年代表团前往欧洲,参加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这个联欢节,象征着世界民主青年的大团结,也是青年艺术展示的盛会。作为华北大学的一名俄语教员,我被选派为新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俄语翻译。
临行前,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兴高采烈的青年代表们来到中南海的会场,会场由一座大四合院改建而成,上面是用拱木制做的屋顶,悬灯结彩,下面是摆放整齐的桌椅,大厅四周是雕梁画栋的走廊,悬挂着大红灯笼,有台阶通往正殿和东西厢房,给人以厅外厅的感觉。这个做会场的大四合院属于怀仁堂。大家依次落座,屏息静候接见时刻的到来。
适值盛暑子夜时分,万籁俱寂。忽然,大厅里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毛泽东主席来到大厅,他体态魁梧,满面红光,目光炯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心情万分激动,沉湎于喜悦之中。毛主席向大家招手致意,显示出举国同庆解放的豪迈气势。
周恩来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讲了话。他说,你们这次出访欧洲,责任重大,在那里,可以说有“一红、一白”两头狮子在对峙。你们的任务是:协助红狮子(苏维埃政权)打败白狮子(帝国主义)。不要辜负祖国人民的嘱托和期望。你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勤奋工作,争取更大的胜利。欢欣鼓舞的各民族青年以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回报了周恩来的殷切期望和嘱托。
当年,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提出的口号是“保卫和平,打倒战争贩子,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主和平”。这些口号的提出,尽管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如今在我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
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开幕的那一天,在布达佩斯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开幕仪式。雄壮的《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响彻云霄,上千只和平鸽放飞碧空。身着鲜艳民族服装,演奏着优美民间乐曲的各国青年,在鲜花锦簇、彩旗招展中,欢天喜地地进入会场。
这里我要讲一个小插曲:由于第二届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是在1949年夏天举行,那时我国国旗方案尚未最后确定,因此在联欢节开幕前夕,我代表团曾多次与国内联系询问此事,当得知国旗方案仍然没有确定时,才决定按原计划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入场。军旗是在匈牙利加工制作的,上面的“八一”汉字原本应该是“八”在上,“一”在下,呈纵行排列,但呈现在我眼前的军旗上的“八一”两字竟然颠倒成了“一八”,变成“一”在上,“八”在下,其中的“八”字还钉倒了,“八”字的两撇冲着上面的“一”字。当年我做翻译的责任之一,就是事先检查所有工作的细节,当我看到这面制作失误的军旗时,心中不免大吃一惊,在惊诧之余又发现“八一”两字是布制的,并且是用线缝上去的,于是赶紧请人把下面的“八”字拆下来,用大头针别到“一”字的上方,这样看起来整个军旗的布局虽然在比例上不太完美,但起码是一面正确的“八一”军旗了,而此时离入场式只有半小时了。就这样,我青年代表团高举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锦绣肖像,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在万众欢腾、引吭高歌中,雄赳赳、气昂昂地绕场一周进入会场。当年回国后我曾见到过那张打着“八一”军旗入场式的照片,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在这次盛会上,我青年代表团比起其他一些国家上千人的代表团来说,是一个很小的团体,衣着也很简朴单调。我记得无论男女青年全是清一色的蓝色制服,唯一的区别是,女同志下着裙装。代表们手中也没有花束和彩旗,显得有些逊色。然而,她所代表的却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向世人明示了以“小米加步枪”可以最终赢得彻底解放的哲理。在近一个月的友好访问中,中国青年代表们向各国青年昭示了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中国人民新生活的开始。
随西蒙诺夫采访两位司令员
1949年深秋,著名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在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后,以苏联《真理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随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南下两广,进行实况采访。采访组一行四人,有作家西蒙诺夫和速记员克拉娃,翻译梁楠,我作为陪同翻译兼联络员随行。
在湖南长沙,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会晤了西蒙诺夫。他们一道参加了部队的庆功表彰大会,观看了战士们自编自演的节目。
在采访中,刘伯承司令员详尽介绍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进军大西南——川、云、贵等省以及解放重庆的战略部署。在叙谈进行了几个小时之后,刘司令员问道:“还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请刘将军谈谈自己个人的经历和生活。”由此引发出刘伯承司令员一段勉为其难的自述,只是寥寥数语没说几句就结束了访谈。
对此,西蒙诺夫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将军同志谈起打仗、战略策略、克敌制胜,谈笑风声近五个小时。”“谈起个人,无动于衷,吞吞吐吐,不知从何谈起,总共不到五分钟。”西蒙诺夫还私下打趣说:“关于他的履历,我所知道的要比他讲给我听的多得多。”对中国将领的忘我革命精神,西蒙诺夫深表敬佩和尊崇,接着还补充说:“与其说他是一位将军,还不如说他更像一位教授。刘伯承将军翻译了许多苏联军事著作,从大部头的军事理论著述,到一般的报刊军事短评,都是他翻译的,而且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期间翻译的。”然而,刘伯承将军在积极借鉴外军的先进经验的同时,还强调推陈出新,“一面翻译苏联的军事著述,一面整编出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这也正是他后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时发出的英明指示,为我军的教学与训练开辟了新路子。
在湖南衡阳市郊区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的大四合院内,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会见了西蒙诺夫。会晤时,正值林彪身患感冒,发高烧近40度,面红耳赤,捂着军棉大衣,戴着一顶军帽,坐在一部战地指挥报话机旁,手中拿着各色的小标旗,在一幅军事挂图前指挥战斗。他向西蒙诺夫介绍了毛主席关于“是远距离包围迂回,不是近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思想。克拉娃速记员不甚理解“远距离包围迂回”的含义,西蒙诺夫欠起身来,展开双臂,做了一个大拥抱(围剿)的姿态,解决了疑问。座谈进行过半,到了中午,不得不留下客人吃午饭,吃的是白米干饭、豆类菜肴,还专门为客人打开了一听“洋罐头”,饮料就是热白开水。午饭期间,林彪与其说是吃饭,不如说是双手捧着一个热搪瓷缸子取暖。
那天在采访离开之后,西蒙诺夫突然对我说:“我真想把你的手表摘下来扔在地上用脚把它碾碎。”这一误解,我想是因为我们的想法不一致造成的,他的想法是在被采访者面前频频看手表是不礼貌的,有不尊重被采访者之嫌。而我的想法是已经采访近3个小时了,而且林彪又患病发高烧,应当适可而止。
在湖南黄土铺,第四十五军军长陈伯钧热忱会晤了西蒙诺夫,并且专门为他召开了衡宝战役座谈会,详尽地介绍了震撼中外的同国民党桂系5个兵团决战的全过程。参加座谈的第一三五师师长讲述了关于该师在没有接到停止前进命令的情况下,如何一举插入敌后,切断敌军退路,牵动整个战役全局,这次战役取得歼灭桂军残余主力近4个师的辉煌胜利的详尽过程。
采访组还广泛采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普通战士。他们崇高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不时被刊登在苏联《真理报》上,并经塔斯社传遍世界。
在前线,几位解放军战士向西蒙诺夫讲述了一段感人事迹。他们的班长在一次冲锋陷阵中英勇牺牲,残暴的敌人将他肢解后悬挂在树上示众。复仇心切的战士们奋力夺回了阵地,擒获了残害他们班长的敌人,本想用机枪将这伙歹徒扫射成肉泥。但“缴枪不杀”的俘虏政策萦绕脑际,还是安置了这批战俘:愿留下者,予以学习改造的机会,跟随部队走;愿回家者,发给路费遣返家乡。战士们对此做法有些想不通,内心矛盾,但毅然执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政策。西蒙诺夫对战士们的严明纪律和崇高品德,深感尊崇、仰慕与敬佩。
西蒙诺夫返回苏联后,撰写出版了《战斗着的新中国》一书(1950年),歌颂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世界历史性的胜利,赢得广大读者的好评。
伏罗希洛夫赴杭州访问趣闻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代表团成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拉希多夫、高教部部长叶留金、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驻华大使尤金等。中国对伏罗希洛夫一行来访,给予了高规格接待。苏联代表团除在北京活动外,还到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进行了访问。
当年4月,伏罗希洛夫是在中国元帅贺龙陪同下,由上海飞往杭州参观访问的。我作为翻译一同前往。
专机起飞后,机长向两位元帅报告了飞行状况和有关数据,接着是瓦西里同志(克里姆林宫御苑厨师)求见,他向元帅们致意后说,我们正在飞往中国旅游圣地杭州市。那里的西湖龙井堪称名品,声震遐迩,作为早茶,元帅们不妨品尝一番。说罢,他开始忙碌料理起来。大半晌,终于端上几杯深褐色热饮置于桌前。贺龙元帅看了,赶忙婉辞道:“多谢,我不渴。”伏罗希洛夫元帅端起杯子,咂了一口,连声赞许说:“味道好极了,我从来没有喝过这般好茶,真是名不虚传!”这种深褐色的酸中带甜、甜中有酸、散发着奶酪味的龙井茶,乃是瓦西里按照俄罗斯传统方式泡沏出来的。他先将龙井茶叶煮沸,然后加进牛奶、砂糖和大片柠檬,这样就成了他的“龙井茶”了。既然伏罗希洛夫肯定“味道好极了”,随从人员也就跟着品茗,而且赞不绝口。
连日来,一直陪同伏老的贺龙元帅开始继续讲述中国革命战争史略。伏老凑近舷窗,俯望大地问道:“下面是否是井冈山一带,长征的起点?”“不是,长征的起点在江西的瑞金,这一带,确切地说,应是北伐军北上挺进的路线。”贺龙元帅答道。贺龙元帅还谈及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接着两位元帅凑近舷窗,俯望华夏大地,触景生情地畅谈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伟大历史意义。
在杭州,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一行,他们受到20多万人的夹道欢迎。人们高呼口号,挥动中苏国旗,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弄龙舞狮,遍地撒花,迎接国际友人。一位老工人吟诗道:“伏老可真不服老,将军总是爱将军。杭州刺史今如在,料当含笑接知音。”这充分表达了当年中国人民对中苏传统友谊的心声。
在参观杭州著名茶乡梅花坞茶叶生产合作社时,周总理和伏老来到园圃间,同茶农叙谈起来。不一会儿午餐时间到了,只见一位茶农从瓦罐中盛出几碗米饭,又在上面撒了点咸菜,手里拿着筷子招呼在场的人就餐。伏老不大习惯用筷子,哆哆嗦嗦地用筷子往嘴里扒拉饭,就着咸菜倒是吃得津津有味。负责元帅安全的苏联保安人员站在一旁,面面相觑,心余力绌,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周总理问道:“我们吃了你们的饭,不够了怎么办?”“够了,够了。不够了再回去取就是了。”茶农们欣然回答。吃过午餐后,贵宾们参观了绿油油的山茶园,合作社社长代表全体社员向苏联贵宾赠送了明前特级龙井茶3斤,并展示了中国茶道。至此,苏联元帅才真正品尝到清泉水沏泡的正宗龙井茶。
参与《和平与社会主义》杂志工作
1958年9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合办的理论性和报道性刊物《和平与社会主义》杂志创刊于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它曾以34种文字向全世界145个国家出版发行。该杂志于1990年6月停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作为编辑部中方翻译,曾在布拉格工作了一段时间。
《和平与社会主义》杂志编辑部原址是一幢三层楼的神学院。经过整修改建、扩展厅室、疏通管道、安装通讯设施,成为一幢外貌古朴、内部崭新、全盘电气化的现代化建筑。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委派代表组成编辑部,指导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一位捷克老工人说:“原本是一座闻名遐迩的神职学府,如今是宣传马列主义的阵地。”对此变迁,他深感困惑和不解。
《和平与社会主义》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开宗明义指出:本刊以“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同时,对教条主义也采取不调和态度”。
1958年以后,中苏之间矛盾渐起。在整个编辑部内,也经常围绕右倾机会主义亦或“左”倾教条主义争论不休。各国编委各持己见,慷慨陈词,情绪激昂。在一次编委会议上,苏联主编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诘问中国编委说:“您读过列宁有关‘左派幼稚病’,的著述吗?!”得到的答复是针锋相对的:“您读过列宁关于‘叛徒考茨基’的著述吗?!”带有人身攻击的理论观点上的对立可见一斑。
为了增进理解,缓解分歧,了解“大跃进”的经济形势,整个编辑部全体成员应中共中央联络部的邀请,先后分两批参观访问了中国。编委们返回编辑部后都缄默不语、隐约其辞、不加可否、不予评论。唯独法国编委卡纳巴抱怨说,他听到的与看到的不一样。在编辑部他听到的是:“中国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等美好的共产风。”到中国看到的却是:“午餐时在尘土飞扬的场院里,发给每个农民几个馒头,用筷子串起,就一点咸菜,一碗菜汤或稀饭,蹲在地上进食。”他摇着头说:“这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但是说实在的,当年饥寒交迫的中国农民能吃上大米白面,填饱肚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只是无须吹嘘为“共产主义”就是了。
参加毛主席著作翻译工作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以后,我参与了该书俄文版的翻译工作。
翻译工作是将一种语言文字,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中国的汉字不同于西方的文字,这就使中文翻译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繁复性与艰巨性。
“扔掉洋拐棍”的提法来自周恩来总理,具体指的是,不依赖外国专家,由中国同志自行承担中译外的翻译、改稿、定稿和审稿的全过程。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俄文翻译组最初只有一位俄侨专家易国尼科夫。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离开了中国迁往澳大利亚定居。失去了专家后,我作为《毛泽东选集》翻译组的负责人向上级提出另行聘请专家的问题。但由于当年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向苏方敦聘已不可能,周总理的答复是:“你们能否丢掉洋拐棍?”
《毛泽东选集》翻译组领导人、翻译界老前辈姜椿芳同志随即开始物色、聘任、培养“中国人的俄语定稿员”。在各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下,集聚了几位精通俄语的翻译专家,经过不懈的努力、培训和实践,终于形成了由中国人自己组成的“中译俄的定稿班子”。在此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内,这个班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完成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述以及中央重要文献的中译俄的大量翻译、定稿和出版任务。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国以多种外文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其他外文版本的书名都是《毛泽东主席语录》,唯独俄文版本没有“主席”二字,只是《毛泽东语录》。
略去“主席”二字,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这被认为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是反革命的有意破坏。
然而,俄文版所做的“省略”是有其依据的:(1)当年苏联拥有数十万个集体农庄,每个农庄都有一位主席,再加上政府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主席实在是太多了,真是成千上万,多如牛毛,已失去了应有的亲切感,不再是一种令人景仰的尊称,倒有点儿像在中国称“科长”、“处长”的感觉。(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经典著作的书名从来没有“官职”之类的称呼。
在即将发稿前,就“主席”一词的取舍问题仍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毛著室的红卫兵小将们反对得最厉害,作为毛著室俄文组的负责人,我曾被带到中南海接受“革命造反派”近4个小时的批斗审讯。最后请示到中央宣传口的领导同志,幸好他通晓俄语,得以圆满解决。这位领导下令放人,并肯定了俄文版的“省略”方案。
(责任编辑 刘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