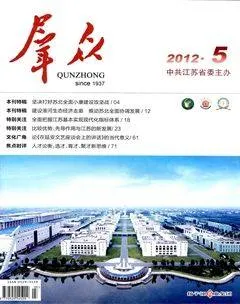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意义
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内容
1942年5月在延安举办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文艺座谈会共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除文艺工作者外,还有中央和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共100余人。5月2号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是为“引言”,5月16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主要由与会者发言,毛泽东认真听取会议发言并有所记录,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做总结发言——是为“结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这两次讲话(“引言”和“结论”),经过整理,一年后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名,发表在1943年10月19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着重强调了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为此,毛泽东提出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就是文艺工作者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态度问题”,就是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群众、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应该赞扬、歌颂而不是暴露;“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应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工作问题”,就是要熟悉工农兵及其干部并懂得“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学习问题”,就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
在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毛泽东在“结论”部分首先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为着人民大众”。在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之后,接下来的是“如何去服务”的问题,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对此,毛泽东首先回答了文学艺术的来源问题,认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只有“人民生活”才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而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由于文学艺术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因此“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虽然毛泽东是以一种辩证的态度看待“普及”和“提高”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他更注重“普及”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
毛泽东在“结论”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首先从文学艺术的性质上,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由此,在文艺批评的标准上,就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而在“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依照这样的性质认定和标准设置,文艺工作者在处理光明和黑暗、歌颂与暴露等问题时,就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歌颂人民,暴露危害人民的黑暗势力。
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之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处在最为艰困之际,其时苏德战争激战正酣,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正处于全面攻势阶段,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滇缅路战役和浙赣战役正在惨烈地进行,华北、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则面临着日军“大扫荡”的巨大压力。在革命圣地延安,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党自遵义会议以来未能解决的思想路线问题,使党在思想上更加强大和统一,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号召在全党开展一次思想教育运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进行了动员。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这被认为是整风运动高潮来临的标志。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当时延安的文艺界,一大批从各地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在长期形成的文艺观念的惯性作用下,仍希望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人性”,表现“人类之爱”,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揭露黑暗”,“还要鲁迅笔法”,并希望通过文艺作品提升读者的艺术鉴赏水平等。其中,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间,丁玲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丁玲);《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论同志之“爱”与“耐”》(萧军);《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王实味);《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坪上散步》(艾青)、《嚣张录》、《还是杂文时代》(罗烽)等众多杂文,1941年11月,丁玲还发表了小说《在医院中时》,这些作品,都对延安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大背景)和文学艺术风潮(小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其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在《讲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召开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是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也就是说,毛泽东是要从政治的角度,来摆正文艺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关系,而当时最大的“革命工作”(政治),就是要“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因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围绕着如何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展开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引言”所着重阐述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解决的”五个问题,就有了统一的内在逻辑: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因此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就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边;态度就要歌颂人民暴露敌人;文艺作品的阅读对象就只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具体而言就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文艺要表现工农兵并使他们能够接受,就要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语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文艺工作者就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与群众结合。
“结论”部分所涉及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去服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以及文艺的批评标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对“引言”部分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其逻辑是一致的,其核心仍然是:文艺要为大众、以大众生活为创作的源泉、以大众为普及和提高的出发点、文艺要服从于抗日的政治、文艺批评的标准首先要看是否“政治正确”——也即是否“利于抗日和团结”,是否能“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促成进步”。
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特殊历史时期(抗日)和特殊环境(延安)下,针对延安当时文艺界的特殊情况,对于文艺工作和革命工作关系的论述,因此并不能将之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文艺认识的一般准则。1943年《讲话》发表后不久,郭沫若就曾评价“凡事有经有权”,即是指“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的”,而多少年后,胡乔木在谈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也明确地表示“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问题,讲话有它的局限性”——依此延伸,《讲话》中关于文艺评价的标准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也只能看作是“权宜之计”。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意义
对于《讲话》中包含的“经常的道理”(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胡乔木认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问题上,《讲话》的观点是不可动摇的”。“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其他都是流,所以作家要深入生活。文艺要诉之于读者,读者基本上是人民。文艺如果没有读者,就是没有对象。……这些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胡乔木的论断非常精辟,深刻地阐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并对当代文艺创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如果在胡乔木的观点上再稍加发挥,我觉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意义,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强调。
(1)以人民大众为本的文艺方向。将大众(工农兵)放在文艺的中心位置,强调文艺为大众服务,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内容,在《讲话》中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我们的文艺”是“为着人民大众”的,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今天,作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文艺创作,工农兵的文化水平也与当年延安时期工农兵的文化水平不可同日而语,而文艺的存在方式也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文字形态,还有影响更为广泛的影视、网络形态),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形态可以多种多样,但书写并歌颂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仍然应当成为当代作家的书写重点和努力方向。当前文艺界私人写作、商业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乃至各种怪异的行为艺术层出不穷,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底层民众无论是作为被描写的群体,还是作为必须被考虑的接受对象,都被一些文艺工作者视若无睹或置之脑后。事实上,无论在任何时期,也无论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人民,以文艺作品服务人民,以人民为本位,都应该成为文艺工作者永远牢记的创作原则。就此而言,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当今的文艺创作,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以民族特色为旨归的文艺追求。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今天,文艺作品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日趋明显,在追求“现代”、努力“先锋”、不断“西化”的“时尚”面前,对民族特色的追求似乎已被一些文艺工作者遗忘。事实上,无论世界如何全球化和“一体化”,各民族的文化(文艺)都应在融合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并以融合了外来文化的民族文化参与世界文化的共同创造从而达到全球化。对于文艺的民族化追求,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通过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定义,强调了这种“新文化”的民族特性:“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并明确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对于什么是民族形式,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有过阐述,那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种“民族形式”则具体化为要熟悉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并“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要有充分的知识,改变“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的状况。对照今天我们的当代文学创作,在追求“现代”、“先锋”的过程中,是否对民族特色的坚持和创新,有所轻慢呢?在全球化浪潮和“西化”浪潮成为文艺创作“主潮”的今天,重温毛泽东70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或许对当今热衷全球化的文艺“时尚”,会有一定的警醒作用。
(3)以批判继承为前提的文艺创造。在改革开放和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学(艺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融入世界文学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学(艺术)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吸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个能立足于世界文艺之林的当代中国新文艺的问题。在当今文坛,我们有的是对西方文艺照搬式的“模仿”,缺乏的是对传统文艺融会贯通式的借鉴,鲜见的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机结合并创造出新型当代文艺的典范。7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说道:“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在更早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的这一思想曾以另一种方式表述过:“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对照今天文坛上大量存在着的“全盘西化”、“食洋不化”、“薄古厚外”现象,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在70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们引以为鉴。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有70年了,《讲话》中对于文艺认识的一些理论观点和科学论断,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