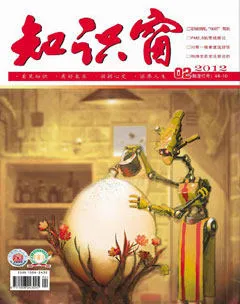滋味人
冬季腌菜,是家家少不了的一件寻常事情。腌菜历史久远,但有文字记载的还是宋《警世通言》里提到的:“刘妪便在厨柜内取了些腌菜,和那冷饭,付与宋金道:‘宋小官,胡乱用些罢!’”
对腌菜,我有着深厚的情结。
小时候,外婆是腌菜好手。一到冬季,家里的卷心坛、小龙缸、大釉缸,都被外婆像变戏法一样,腌满了白菜、豇豆、萝卜甚至山芋藤。这些大坛小罐,放置厨房一角,看着就温暖,有滋有味。
一到雪天,窗外寒风呼呼,雪花飞扬,外婆总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取出几棵腌白菜,洗净切好,放置炭炉上,和大肠或肉什么的一起炖着,突突冒着热气,香气慢慢弥漫。这时,外公总会温壶烧酒,一家人围拥在一起,享受着快乐的晚餐。这些,成了我童年难忘的幸福。
如今,外婆和外公都走了,但外婆腌菜的手艺没有消失。不论在北京姐姐、妹妹家,还是在我家,都能吃到和外婆做的一样味道的腌菜。外婆教会了我们腌菜,也教会了我们平淡、真实而有滋味的生活。
双休日,我买了30斤白菜。晒好洗净后,喊来女儿,一起将白菜一棵棵放好盐,整齐码好放进缸里,再压上石头,封好缸口。女儿高兴地说,她也学会了。
姐姐更是腌菜的专家。每到北京姐姐家,我都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腌菜。雪里蕻、白菜或是萝卜菜,爽口下饭。姐姐说,有这手艺,到哪都能吃到家乡的口味。是呀,只要有这个手艺,到哪都是家,到哪都是家的味道。
过去,生活比较艰苦,腌菜是那时人家餐桌的主打;如今吃腌菜,却是迎合人们刁钻的口味了。
记得高中时,我有一位好友赵勇,家境贫苦。每周回校,他总带来一大瓶母亲腌制的腌菜,这就是他一周的菜。后来,赵勇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武汉打拼,如今有了自己的公司。年前我出差湖南,绕道看他。席间,我们都喝了不少酒,说到过去,他说,高中后很长时间他都不敢吃腌菜了,看到腌菜嘴里就酸酸的,肠胃不舒服。如今生活好了,大鱼大肉,却都没有腌菜好吃下饭。吃来吃去,就想母亲的腌菜,就想家乡的母亲……
一碗腌白菜或一盘腌豇豆,在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旁,不卑不亢,一点都不怯弱。在都市,哪家酒店没有预备几样可口的腌菜?这些腌菜大大方方地登入大堂,凭的就是一种淡定,一种质朴,一种独有的滋味。
再过两周,我自家的腌菜就可以开坛了。我想,找几个朋友,小聚一下,尝尝我的腌菜,再谈谈和腌莱有关的故事,呵呵,想想,都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