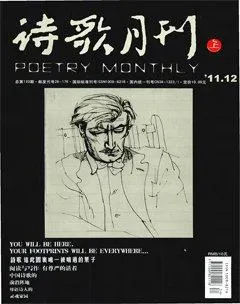舞在敖德萨(节选)
作者的祷告如果我为亡者说话,我必须离开我身体里这只野兽,我必须反复写同一首诗,因为空白纸页是他们投降的白旗。如果我为他们说话,我必须行走于我自己的边缘,我必须像盲人一样活着,穿走于房间而不碰倒家具。是的,我活着。我可以过街,问:“现在是哪一年?”我可以在睡眠中跳舞,在镜子前笑。甚至睡眠也是一种祷告,上帝我将赞美你的疯狂,以一种不属于我的语言,谈论那唤醒我们的音乐,那我们游动于其中的乐曲。因为无论我说什么都是一种请愿,我必须赞美最黑暗的日子。舞在敖德萨(一)
在一座被鸽子和乌鸦联台统治的城市,鸽子盖满了主要地区,乌鸦占据了市场。一个耳聋的男孩数着邻居后院里有多少只鸟,然后造出一个四位数号码。他拨打这个号码,在线路上对着声音表白他的爱。
我的秘密:四岁时我耳聋了。当我失去听力,我便看见声音。在一个拥挤的电车上,一个独臂男人说我的生命会与我祖国的历史神秘地联在一起。但我的祖国不见了,它的公民在梦中相遇,选举。他没有描绘他们的面孔,只有几个名字:罗兰,阿拉丁,辛巴达。舞在敖德萨(二)我们生活在未来的北面,日予以孩子的签名打开信笺,一枚桑果,一页天空。我祖母从凉台上扔西红柿,她掀动想象,如同从我头顶扯起一床被毯。我画我母亲的脸,她知道什么是孤独,她把死者同党派一样藏于土地里。夜晚为我们解衣{我数它的脉搏),我母亲跳起舞来,她用桃子,烤制的食物,填满过去。对此,我的医生笑了起来,他孙女抚摸我的眼睛——我吻她膝盖的背后。城市在颤抖,一只鬼船出航了。我的同学为犹太人取了二十个名字。他是天使,他没有名字,我们摔跤,当然哕。我祖父坐在拖拉机上与德国坦克对仗,我提一满箱布罗茨基的诗。城市在颤抖,一只鬼船出航了。夜里,我醒来小声说,是的,我们曾经活着。我们曾经活着,是的,别说那是一场梦。在当地工厂,我父亲抓起一大把雪,塞进我嘴里。太阳开始了日常叙述,染自他们的身体母亲,父亲,舞着,移动着黑暗在他们身后述说。这是四月,太阳洗刷着凉台,四月。我复述我的故事,光线浸蚀我的手:小书本,去那个城市吧,不要带着我。
音乐疗法——致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哀歌[一位现代奥菲斯:他被送往地狱,再也没有返回,他的遗孀搜遍了地球六分之一,她紧紧抱住装满他诗歌的碟子,夜里背诵,以防止愤怒女神带着搜查令发现了它们。]当这页纸上仍然还有一些光线时,他带着妻子穿着陌生人的外衣逃跑了。衣服上有些汗味;一只狗在追踪,舔他们走过和坐过的地面。在厨房,在楼梯,在马桶上,他将向她展示通往沉默的路,让收音机自言自语。他们关掉灯,做爱。但邻居有望远镜,而他也看,灰尘落在眼皮上。这是1930年:圣彼得堡是一只冰冻的船。大教堂,咖啡馆,他们搬迁到涅夫斯基大道,因新政权找他们的茬。[在克里米亚,他召集富有的“自由派”,对他们严厉地说:在审判日,如果他们问你是否理解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就说“不”。是否喂养了他?——你必须回答“是”。]我大声朗读我在地球上的生命之书,然后坦白,我爱柚子。厨房里:人们举杯,品尝伏特加;香肠。我,一个穿白衬衣的男孩,用手指蘸甜蜜。母亲为我擦洗耳根。我们说了许多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也就是说这是八月,八月!树上的光影,充满愤怒。八月将语言填满我们的手心,闻起来像烟熏。此刻,记忆,倒啤酒,把盐撒在杯口,给我写信的人,拿去你想要的吧:一枚金色的硬币,置于我舌头之上。(云彩的弟弟走来,他穿深绿色的裤子,未刮胡子。大教堂里:他双膝跪下,祈求“幸福”他的话语在地板上,死乌的骨骸。)我爱过。是的。我洗手。述说我对大地的忠贞。而此刻死亡这美男子,正数我的手指。我逃亡,被捕,再一次逃亡被捕,再逃再被捕:在这首歌里唱歌的是一个瓷娃娃。诗歌就是自我,而我抗拒这个自我。在别处:圣彼得堡像一个迷失的青年站立在那里,它的教堂,船只,绞刑架加快我们的生命。[1924年夏天,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带着年轻的妻子来到圣彼得堡。娜杰日迟正像法国人所说的“可爱而迷人”。一个偏执狂?他当然是。他把一个抱怨他没有发表作品的学生掀倒在楼梯上,吼道:萨福发表过?耶稣基督发表过?]诗人是一种声音,我说,就像伊卡洛斯坠落时自言自语。是的,我的生命如风中的碎枝击打北方的大地。此刻我写一部雪的历史,灯光沐浴着划过纸面的船只。但在某些下午,诗共和国开启,我害怕没有生活过,死了,没有活够以将这狂欢化为元音,倾听清晰的圣经般的演说拍打出浪花。我读柏拉图,奥古斯丁。读他们音节中的孤独而伊卡洛斯不停地坠落。我读阿赫玛托娃,她丰韵的重量将我绑在大地山坡上的坚果树呼吸着干燥的空气,日光。是的,我活过。国家把我的脚吊起来,我看见圣彼得堡的女儿,天鹅,我学会飞鸟阵列的语法,永远落在普希金大道,而记忆坐在角落里,用海绵将我擦掉。我犯过错,是的,我在床上将政权与我的女友相比较。政权!一只傲慢理发师的手在肌肤上剃干净。我们大家围着他欢快地跳舞。[他坐在椅子的边缘,大声梦想美妙的晚餐。他不在办公桌上,而在圣彼得堡街头,写诗;他热爱这样的意象:公鸡用他的诗撕开雅典卫城墙下的夜晚。关在牢里时,他拼命在门上敲打:
“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坐牢的。”]生命中有那么一两次,一个男人像苹果一样被掰开。剩下的是声音撕开他的身体一直撕到中间。我们看见:淫秽,惊骇,泥土但有种形式的快乐总是多于一种沉默。——在此地与涅夫斯基大道之间岁月,鸟儿一般地,伸展,——为他祈祷吧,那为面包和土豆而活着的人一群狗在每一条街上背诵他的诗。是的,数一下”三月”,“七月”用一根线把他们织在一起——是时候了,上帝,用这些词语紧紧压住你的沉默。——故事是这样说的,一个人逃亡又被抓进夜晚的书写里:做爱之后,他坐在厨房地板上,睁大眼睛讲述上帝的空虚,而我们就是由这样的意象构成的。——他失业了——在银餐具和灰尘中,亲吻妻子的脖子,直到她肚子抽筋。人们会想到一个小男孩用舌头将音节铺展在女人的皮肤上:这些诗句完全由哑音缝起。[娜杰日迭从书上抬起头来说:奥西普、阿赫玛托娃和我站在一起时,曼德尔施塔姆突然欣喜地融化了:几个小女孩从我们身边跑过去,想象她们自己是马。第一个停下来,不耐烦地问:“最后那匹马在哪里?”我抓住曼德尔施塔姆的手,不让他走过去;阿赫玛托娃也是,感觉到危险,低声说:“不要跑开了,你是我们最后的马。”]——我死去时,赤脚走遍我的祖国在这里冬天筑起最强大的孤独,拖拉机闯进半人半马王国,驰骋于白话语言:我二十三岁,我们生活在茧中,而蝴蝶交配。奥西普把手指伸进火里,他早起,穿着拖鞋四处走。他写诗很慢。祈祷者们在屋里倒下。飞蛾在窗外看他。当他的舌头划过我的皮肉,我看见他的脸在下面,我看见痛的清晰——娜杰日达如是说,她站在橙色的光线里。双手安详,自言自语亚伯拉罕、伊萨克、雅格布的神啊在你的善恶尺度上,放一盘温暖的食物。我丈夫从沃罗涅日回来时,嘴里藏着一只银勺——他梦到,独裁者沿着涅夫斯基大道跑像狼~样追踪他的过去,一只睁眼睡觉的狼。他相信人性。他无法将自己从圣彼得堡中拉回,治愈。他在心里默诵死者的电话号码。哦他低声说!——未说出的话语变成岛屿的痕迹。他煽了托尔斯泰一耳光,好啊。他们抓走我丈夫时,每一个字都消失在书本里。他们看着他说话,元音上有牙齿的印记。他们说:你,必须让他独处因为他背后已有石砖囤积,落下。[奥西普有着浓密的睫毛,直到他面颊的中央。我们走在普利西斯坦卡大街上,谈论什么我已记不清。我们转到果戈理大道,奥西普说:“我已为死亡做好准备。”他被逮铺时,他们搜索诗,弄得满地都是。我们坐在一个房间里。墙的另一边是一个邻居家里,有人在弹夏威夷吉他。我亲眼看见搜查者发现了《狼》,拿到奥西普跟前。他微微点头。离开时他亲吻了我。他是在早上七点钟被带走的。]在视野的每一个尽头,曼德尔施塔姆站立着,手里捏着土块,扔向路过的行人。你会认出他的,主说:——他讨厌沙皇村,马雅可夫斯基说:“别念你的诗了,你不是罗马尼亚交响团。”和谐是什么?它纠结又被解开;娜杰日达说。雪落进她身体里,她听到全身都是小鸡的声音。娜杰日达,她的是与否总是难以分辨。她跳舞,裙子卷在大腿间,光线加强。在每个房间的四个角落里:他与她做爱,耳垂,眉毛,日子编织成结。他穿过她的厨房,抚摸家具,头上有一个小螺旋桨随着他说话而转动。室外,一个小男孩对着树撒尿,一个乞丐训斥他的猫——那个1938年夏天——墙壁热烘烘,日头打在城市的砖墙上,“这个爱屈服于威权的城市。”在每一个视野的尽头,他用牛奶擦她的脚。她敞开身体,躺在他腹部。我们将在圣彼得堡相见,他说,我们已把太阳埋葬在那里。
旅行音乐家玛丽娜·茨瓦塔耶娃㈠在每一行的奇怪音节中:她醒来如同一只海鸥,撕裂于天地之间。我接受她,与她站在一起,面对面。——在这个梦里,她穿着裙子,像一只帆,在我身后跑,我停她也停。她笑着,孩子一般自言自语:“灵魂=痛苦+其它所有一切。”我笨拙地双膝跪下,不再争吵,我需要的只是一扇人间的窗户在以我生命为屋顶的房间里。玛丽娜·茨瓦塔耶娃㈢
在我耳聋的第一年,我看见她与一个男人在一起。她戴着紫色围巾,半跳着舞,把他的头抱在手中,放在胸前。然后她开始唱歌。我聚精会神地观察她。我想象她的声音有橘子的味道:我爱上她的声音。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像个共谋犯一样发出矛盾的讯号。“别吃苹果核,”她威胁我,“吃了苹果核,树枝会长在你肚子里!”她摸我的耳朵,用手指抚摸。
我对她丈夫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在一辆开动的汽车上死TULm9ECFg4/CgW5FOYAIkb1JTit9cHJxfg4vHfOzyho=于致命的心肌梗塞。她脸上没有抽搐,看着她的脸,我明白了悲痛的尊严。从葬礼上回来后,她脱下鞋子,赤脚走在雪地里。赞美……而有一天会有一些黄柠檬透过半开的大门朝我们闪烁这些金色的阳光号角在我们空旷的胸部倾吐他们的歌声。赞美我们匆忙地离开敖德萨,忘了公寓前那只装满英语词典
的箱子。我来到美国,没有带字典,但有几个词语存
留下来:忘记:光的动物。一只船抓住了风和船帆。过去:手指来到水的边缘,举着灯盏。水可疑地冷。许
多人站在岸上,最年轻的把帽子抛向空中。理性:将我与疯狂隔绝的不是隔绝,真的不是。一个巨
大的水族馆,装满了水草,乌龟,和金鱼。我看见闪
光:移动,刻在额头上的名字。快速的笑她倾身过来,受骗了。我喝得太快。死:进入我们的梦中,死者变成没有生命的物体:树枝,茶杯,门把。我醒来,渴望我也带着这般的清晰。时间,我的孪生,拿去我的手穿过你城市的街道:我的日子,你的鸽子,在抢面包屑——一个女人在夜晚要我讲一个结局圆满的故事。我没有。一个难民,回到家变成鬼寻找曾经住过的房子。他们说——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是一个王子同一个犹太女孩结婚违背了教会的意愿和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意愿。失去了一切渴望失去:地产,船舶隐藏这个戒指《他的婚戒),这个戒指我父亲交给我哥哥,然后拿走。又给他然后拿走,匆忙地。在家庭相册里我们端坐着如同学生服模特而破坏,像一堂讲座,被推迟。然后母亲开始跳舞,重新排列这个梦。她的爱很艰难;爱她却简单,如同把桑葚放入嘴里。哥哥的头上:没有一丝白发,他唱歌,唱给他1 2个月大的儿子听。而父亲唱歌,唱给6岁的哑默。这就是我们如何生活在地球上,一群麻雀。黑暗,一个魔术师,在我们耳朵后面找到栖身处。我们不知道生活是什么谁给的,现实覆盖着厚厚的渴望。我们放在嘴唇上,饮下。我相信童年,一个数学试题的故土归与不归,我看见——岸边,绿树。一个男孩从街上跑过,像一个迷路的神光线落下,触到他的肩。记忆,一支古老的长笛,在雨中吹晌,狗睡去,舌头半悬在外面;生死之间二十年我在哑默中穿行:1993年来到美利坚。美利坚!我把这个字放在一张纸上,这是我的锁孔。我看见街道,商店,骑自行车的人,夹竹桃。我打开一个公寓的窗户说,我曾经有过主人,他们在我之上呼啸我们是谁7为什么在这里?他们提的一盏灯笼仍然在我的睡眠中闪耀——在这个梦里我父亲呼吸仿佛一次又一次点灯。记忆启动旧引擎,开始移动而我以为树木在移动。沾了土的纸角上我的老师在行走,走出一个声音他在手掌上磨擦每个字:“手向泥土和碎玻璃学习你不能想出一首诗来,”他说“要看光线硬化成字句。”我出生在一个以奥德修斯的名字命名的地方我不赞美任何国家——伴随着雪的节奏,一个移民的笨拙单词坠落成语言。而你要一个结局圆满的故事。你的孤独拉响了琴音,我坐在地板上,看你的嘴唇。爱,一只腿的鸟,我幼时用四毛钱买回,然后放飞现在又回来了,我的灵魂在恣意煽动的羽毛中。哦乌的语言没有诉苦的词汇!——阳台,风。这就是黑暗怎样用小指头画我的肖像,我已学会像蒙塔莱那样看待过去神的隐秘念头降落在一个孩子的鼓点中穿过你,穿过我,穿过柠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