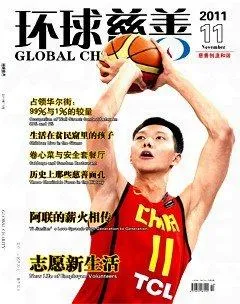饥馑中的官与商(下)
这次赈灾,不仅使义赈的触角延伸到海外,还让西方人意识到,在竭力迈向近代化的中国,存在着一个具有巨大活动能量的民间救灾机制。
公元1906年,即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的丙午年。这年农历七月十九日,盛宣怀突然收到两江总督周馥自南京发来的急电。电报称,苏北的徐州、淮安、海州一带深被水灾,“哀鸿遍野”,而官赈“苦无款可拨”,因此恳请盛宣怀联合沪上绅商急办义赈,“以助官力之不足”。
当周馥向盛宣怀求援的时候,苏北的灾情正在逐步加剧。春夏之交,强降雨造访了苏北一带,而且徘徊良久。如海州的沭阳县,从闰四月开始到七月上旬的90天中,有45天都遭受露雨侵袭。连绵的降雨酿成洪灾,使徐州府、淮安府和海州的13个州县化为一片汪洋。
尚未收获的大麦小麦不是被水冲走,就是因为阴雨而腐烂;甘薯、花生也大半付之流水。农作物绝收,饥饿开始蔓延。接替周馥出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在农历十月向朝廷奏称:“灾民无可糊口,纷纷变售牛具,四散觅食,甚至卖儿鬻女者,日有所闻。”
但官方主持的赈灾和救荒却显得无力。由于财政不足,各州县既没有用于赈济的存粮,也没有钱。不少州县发放的赈款,每个成年人只有40文铜钱,小孩只有20文。灾荒过境,粮价腾贵,小麦一斗1000文,米一斗3000文。区区40文,连一根萝卜都买不起。洪水退后,地方政府组织灾民补种。但种子价格飞涨,灾民糊口尚且没有着落,遑论补种救荒?
饥饿的灾民蜂拥外逃,流向富庶的江南地区。在江北的交通要冲清江浦,到10月中旬,聚集的饥民多达62万人。地方政府不得不一方面设置饥民厂收容这些流民,一方面给付路费遣送回乡。镇江设有三个饥民厂,从10月到11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总共动用了近800口大锅,投入400石米谷,为12万多饥民煮粥施赈。
一些赈灾不力的地方官员受到严厉处分。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将10名没有切实实施赈济的府州县官员予以革职。但随着流民越聚越多,安抚饥民和维持社会治安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如果官赈继续软弱乏力,事态必会进一步恶化。两江总督端方决定,在冬季的赈济结束之前,停止发放自己和江苏巡抚、安徽巡抚的养廉银,充作救灾资金。他甚至批准江南彩票局,自12月起发售赈捐公益彩票。同时,他一再催促盛宣怀迅速发动沪上绅商,组织义赈。
在上海,盛宣怀和吕海寰正马不停蹄地联络金融界、商贸界和实业界,四处筹措赈灾资金。到11月,他们已筹得6万两白银的赈款。至于放赈的人选,盛宣怀首先想到的是唐锡晋。唐锡晋自光绪初年就参与了义赈活动,庚子年间又随严作霖一道赴陕西赈灾,是公认的“义赈熟手”。盛宣怀将筹集的6万两白银兑换成十万二千串铜钱,交由唐锡晋等人,让他们分赴苏北放赈。紧接着,盛宣怀和吕海寰又捐出10万两白银,陆续解送灾区。
随着义赈的开展,盛宣怀向端方建议,将官赈和义赈统一起来。他认为,依照官赈的程序,需要查齐户口、核定数目后才能放赈,不但费时过长,而且容易造成胥吏从中克扣,只能出现新的饿死者和流亡者;而义赈先确定发放的钱数,然后“随查随放”,不但能“救活人命”,还能“遏止流亡”。当时,端方面临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遣返聚集在清江浦、镇江一带的几十万流民。但只有快速有效地实施赈济,才能促使流民返乡。农历十一月上旬,端方向流民许诺,将在他们的原籍所在地进行冬赈和来年的春赈,劝他们不要再滞留外地。
在这样的情势下,端方接受了盛宣怀的建议。随即,两人达成《官义两赈合办章程》。《章程》规定,选派总董和委员各11人前往受灾的11个州县,总董“专司查户发票”,委员“专司收票发钱”;对赈济的饥民,每位成年人给付铜钱1000文,小孩500文,返乡的流民每人也是1000文;放赈的铜钱直接运到各乡村,“随查随放”;从年内的冬季到来年的春季,每两个月放钱一次,拟总共放赈3次。
官赈与义赈合办后,赈务由于义绅们的参与很快就变得活跃起来。1906年的冬天,阴雨绵绵,寒冷不堪,在上海却掀起了赈灾募捐的热潮。《申报》前后发布的募捐广告多达155件,内容多为捐款者一览表及捐款金额。发布义捐广告的客户包括上海总商会、华洋义赈会、沪北仁济堂和《申报》报馆协赈所,这些机构为义赈募捐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华洋义赈会总共募集了125万两白银的赈灾款。它是一个由华人和在沪外国人构成的苏北赈灾支援团体,也是日后著名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前身之一。
精通洋务的盛宣怀一直寻求国际上的赈灾援助,这其中,吕海寰起了很大作用。他不但出任过驻德国、荷兰两国公使,而且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发起人之一,与洋人有比较深的联系。大约在11月,盛宣怀、吕海寰和英国人Edward Selby Little协商,设立了华洋义赈会,由在沪的外国人通过各国领事向本国募集捐款。在华洋义赈会的努力下,一些国家对苏北赈灾给予了热情援助。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亲自向国会呼吁,促使国会批准拨给救助清国灾民的救济款。华洋义赈会先后接收海外捐款合计白银近80万两,其中来自美国的捐款占到了一多半,将近48万两。
赈灾的深入推行,促使流民陆续返乡。到翌年年初,流民遣返工作基本结束,仅清江浦遣送的流民就达41万多人。放赈一直持续到1907年的5月,与之相伴随的,还有赈灾粮的采买以及以工代赈工程。直到当年9月,盛宣怀、吕海寰还继续筹银十几万两,派人“分赴奉天、山东等省,采办杂粮,由海道运至海州进口,分拨平粜”。
光绪三十二年的苏北赈灾,总支出高达白银800万两,前后发放铜钱740万人次,规模之大,可谓空前。这次赈灾,不仅使义赈的触角延伸到海外,还让西方人意识到,在竭力迈向近代化的中国,存在着一个具有巨大活动能量的民间救灾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