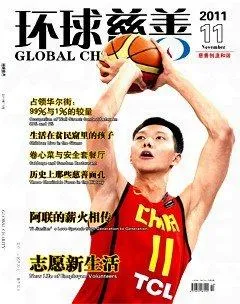企业志愿者的崛起
企业组织员工志愿服务最大的驱动力来自品牌意识的认同。企业直接以组织志愿服务的形式来介入社会课题的解决,更能彰显自己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态度,也更能确保所投入的资源与自己确定的社会责任战略方向匹配。
大巴车奋力冲出北京市区重重的车流,摇摇晃晃地穿梭在五环外的小巷子里。
黑桥村,一个被铁路环线包围着的村子,到处散落着灰色低矮的楼房和简易板房,有约4万名流动人口聚集在这里。打工子弟爱心会(CMC)的黑桥社区中心就建在村子的边缘,远离了喧闹的露天市场,是村子里唯一的亮色。
黑桥社区中心大约有2700平方米,中心设施全部由集装箱改造而成,便于迁徙。每当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4点半以后及周末,这里都会被拖着书包的孩子和各色面孔的志愿者填满。正待醒来的EVP
CMC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国际性公益组织,致力于通过在打工人群聚居的社区里建立社区活动中心,为贫困的流动儿童、青少年和打工人群提供免费的教育、社会、健康培训及咨询服务。
2006年创办之初,CMC只有美国小伙子何乐和两个志愿者。“现在我们有8个部门,但只有35名员工。”CMC外联及筹款经理谢颖芝称,有的部门只有一两个人。
在中国,整个公民社会第三部门能力很弱,瓶颈在于人才的极度匮乏。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现在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都不去NGO工作,因为待遇不高,没有福利,也没有保障。很多的制约,让中国本土NGO很难一下子雇佣那么多的一流人才。“最重要的办法是,要企业更多地参与、更多地投入于公民社会领域,企业的志愿者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表示。
企业员工志愿服务(Emp loyeeVolunteering Program,EVP)作为企业社会责任(CSR)的一种较晚出现的形式,在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界已经得到广泛发展。比如英国天然气公司,针对英国服刑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的问题,员工们会志愿教他们开卡车的技能,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减少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公司的思路是:我们在这个社区里就要帮助这个社区。
为鼓励企业员工参与志愿服务,欧盟把201 1年确定为“志愿服务年”,并将在欧盟企业中组织员工志愿服务奖的评选活动。在这一趋势影响下,企业员工志愿服务从一种员工在工作之余主动为慈善组织提供服务的个人化行为,转变为企业主动策划、组织和监督执行的官方行为。90%以上的美国企业已有支持员工志愿服务的措施安排,其中2/3以上的企业为员工安排相应的“志愿活动假期”。
与发达国家企业热衷实践的情形相比,企业员工志愿服务在中国本土企业中并没有那么踊跃。北京富平学校企业公益伙伴网络的研究发现,相比国外成熟的企业志愿者文化,目前国内开展员工志愿服务的企业总体比例不高;开展员工志愿服务的企业以外企为主,中国本土的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比例不高;很多有愿望开展员工志愿服务的企业得不到有效的支持。
被束缚的力量
中国志愿服务活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是出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本土志愿者出现在社区服务层面上。1993年12月19日,两万余名铁路青年率先打起了“青年志愿者”的旗帜,在京广铁路沿线开展为旅客送温暖志愿服务。之后,40余万名大中学生利用寒假在全国主要铁路沿线和车站开展志愿者新春热心行动。
随着志愿服务热潮的掀起,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成立促使志愿者招募、注册、培训、管理和激励机制逐步完善,并形成了由民政部门指导的社区志愿者、由共青团系统指导的青年志愿者和各类NGO志愿者三支队伍,另外还有一些由不同党政部门或人民团体领导的志愿者队伍。
但中国志愿者的活动始终突显一个主要特点:大多与政府的活动和政府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多或少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考虑到我国社会组织较为幼稚,自治权利孱弱,自律程度较低,志愿服务事业发展较慢,若脱离政府推动,则很难发展。
其中资金的缺乏是国内志愿者活动的主要障碍之一。黄伟辉是广东省惠州市志愿者联合会一窗灯火暖人心分会会长。“志愿者每次来接热线都要自己出交通费,有时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黄伟辉说,志愿者们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从事这些工作,本来就很累了,再要他们出交通费等费用,就给他们增加了更多负担。长期这样,部分人就有些疲惫,因此离开了志愿者组织。
目前中国本土的志愿活动或多或少带有组织色彩和运动色彩。黄伟辉从1998年开始做志愿者,对于社会对志愿者服务认识的不足,他很有感触:“部分单位、企业和市民现在仍认为,志愿者等于免费廉价劳动力,需要的时候就叫上。”
由于缺乏对志愿者活动的认可制度和有效支持,因而不能行之有效地激励全社会的参与。
CSR战略方向的匹配
2011年6月16日是IBM成立百年纪念日,世界各地40多万名IBM员工以志愿服务的形式纪念这一特殊时刻。IBM中国的4万多名员工以每人至少为社会志愿服务8小时方式进行“服务庆百年”活动。IBM中国公众事业合作部经理耿晨指出,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在IBM的员工志愿者服务体系中,全员参与的活动属于ODC(OilDemandcommunity,慈善志愿服务)层级。在ODC层级之上,还有CSC(CorporateServiceCorps,专业志愿服务)和ESC(Elite ServiceCorps,精英志愿服务)两个级别,这三个层面的活动因人员参与级别和人数差别而呈金字塔状分布。而公司对三个层面的志愿服务也提供不同的支持和管理方式。在CSC层面,员工通过自愿报名及选拔之后,来自IBM全球各地公司的815名员工组成多元跨国团队,到尼日利亚、南非等地区帮助NPO使用数据和财务管理系统,在当地大学建立企业孵化中心等。
作为中国关注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支持性民间组织,惠泽人认为志愿服务的市场应该细化,横向是教育、扶贫、环保等不同领域,纵向则分做好人、做好事、做好社会三个层次。
对公司而言,虽然在开展志愿者活动中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它需要提供很大的支持。“很多员工因为企业无法提供足够的时间参与志愿服务而退缩。”
惠泽人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创始人翟燕表示。
2004年微软公司开始实施员工带薪志愿服务项目,每一个正式的员工每年有三天带薪假期,可以到各地去开展志愿服务。壳牌中国集团公共事务部社会业绩经理毕蕾称,除经费、时间支持外,还要设立激励机制。如果员工贡献了个人时间,比如周末去参加志愿者活动,贡献一个小时的话,公司会支持30元。“另外,我们也会在公司年会上,由高管层给志愿者代表颁发证书,这是精神层面的认可。”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临终前认为,自我实现应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企业组织员工志愿服务最大的驱动力来自品牌意识的认同。企业直接以组织志愿服务的形式来介入社会课题的解决,更能彰显自己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态度,也更能确保所投入的资源与自己确定的社会责任战略方向匹配。
从“一”到“三”的合作
近年,国际上掀起新的潮流和趋势,即第三代企业和第三代NGO合作的模式。这种模式需要企业,特别是员工,更多地参与到NGO中来。
企业拥有人力资源、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他们参与可能是加入到NGO的理事会;可能是专业性服务,这也是对目前NGO来说急需的;第三个层面的参与是最基础的参与,企业的志愿者参与到NGO的活动和项目之中去奉献爱心。
2011年以来,普华永道有超过100名北京和上海的志愿者加入到CMC的各种项目中。除了超级星期六和欢畅周末活动之外,还有带领打工子弟参观博物馆或者开展环保工作室的活动。
此外,在CMC的合作伙伴中,还有西门子公司的法律部门每周三派出志愿者为“青少年职业技能”项目中的青少年普及法律知识,有万博宣伟公关顾问志愿投入的免费顾问咨询……
“企业员工志愿者虽然只占CMC志愿者群体的5%左右,但他们的技能和阅历大大填补了大学生志愿者能力的空白。”
谢颖芝的脸上始终挂着浅浅的笑容,“常有企业问CMC,我可以怎么帮你们?我说,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CMC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只要你有那颗爱心,我们就为你提供给孩子服务的机会。”
所有NGO的使命,是基于社会的需求,整合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解决社会问题和创新中。第一代的NGO跟第一代企业形成各自为政的合作模式,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合作和沟通。到了2000年以后,第二代企业和第二代的NGO合作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很多企业开始承担社会责任,更多的是给NGO钱。随着志愿者所代表的社会人力资源进入NGO,他们不但给服务机构提供人力帮助,而且还贡献各方面的人才。但我国现阶段大多数NGO的接待能力还有待提升,无法与企业志愿者达到良好的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