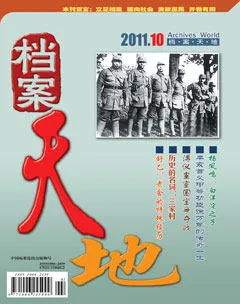盖有“木供”二字的结婚证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打开我的家庭档案,一眼就看见了一张红色的结婚证,它是一个家庭诞生的历史见证。我结婚在20世纪70年代,仔细端详着证书,封尘了三十多年的回忆,像一股绵长的细流,在心的深处缓缓流淌,它在我年轻时滋润着爱情,在中年时提醒我努力工作,担当起家庭的重任,在老年时,将见到我俩手牵手的夕阳红。
想起结婚证上的“木供”二字,真为我们国家现在的富强而惊叹!那时候,结婚要有一二件家具,能叫别人羡慕许久,即使是一对木箱,也需要结婚证才能供应。当我领到结婚证后,家里为把女儿风风光光地嫁出去,就马上到第八木制品厂的商店花了48 元,买到了一对木箱,商店在结婚证上盖上了印戳。
我是196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来到了辽宁省的最北端西丰县天德公社,在那里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农民的淳朴、勤劳,踏上了人生的漫漫长路,悠悠岁月。当我20岁的时候,亲属经常在我面前不经意地提到他,然而他还在数千里外的福建当兵,当看到照片的时候,浓眉大眼,带着憨厚的表情,穿着军装,当时就认定了我和他将有着不解之缘,心中也启盼着见面的那一天早些到来。
1971年的春天,他退伍回来的时候,介绍人让我们见了第一面,彼此竟有恍如前世就相识的感觉,谈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情,然而我第二天就回到了西丰,继续在广阔的天地炼红心。从此,邮递员成了我们红娘,频繁的书信,牵牢两颗相爱的心。
他退伍后分配到了变压器厂,在我们那个时代,进工厂是最令人羡慕的工作。一两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对我的感情没有变,然而他的亲属们却都来做工作,说一个在大工厂,一个在农村,根本不般配,也有的登门说媒,想阻止这段尚不成熟的狂恋,可他却请了2天假到400里之外的西丰来看我,叙说那不尽的相思情。
1973年的秋季,我从农村抽调回城,也为我们的爱情开启了通行之门,我是独生女,父母就盼多一个儿子,他家六个孩子,生活困难,就求减轻些负担,所以两家老人各求所需,理所当然地同意我们的结合。
1975年初,我们谈到男婚女嫁的时候,先到公社领到了一张鲜红的结婚证,由恋人成了爱人。
光阴如梭,弹指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一双儿女都已成家立业,我们都在国家机关工作,相濡以沫,从青丝缕缕到两鬓斑白,携手度过每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烈日炎炎的夏天、硕果累累的秋天、银装素裹的冬天。
如今对着结婚证,我非常坦然:我的家庭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