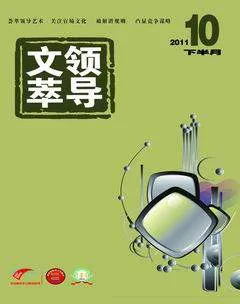后美国时代真的来临了吗?
美国到了“斯普特尼克时刻”吗?
美国官员对于美国衰落的结论不甚认同。“对于美国衰落的语言,历史有过,一次是50年代,一次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但是亚洲国家一个正在统一的共识是:美国将在未来30到50年还会在亚太地区拥有绝对控制权。”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一次半公开的会议中说,“事实上,因为我们的真诚,因为我们的市场的开放性,如果你低估美国的实力那是你自己自讨苦吃。亚洲国家普遍对我们看法乐观。当然亚洲的竞争性越来越强,我们的目标是对竞争遏制在建设性的积极方面。”
然而,支持“美国衰退论”的一派更喜欢用数字和事实说话。
美国自经济衰退之后,失业率一直停留在10%左右,而因为如果失业时间过长的人不再被统计在失业人群中,美国的真实失业率保持在15%左右。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字,美国有超过17%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十年前,在成年人平均财富方面,美国是世界第一,到2010年,则跌至第七位。根据衡量物质财富以及民主和治理的质量的列格坦繁荣指数显示,在全球最繁荣国家排行榜上,美国名列第九,落后于芬兰、瑞士以及其他北欧国家。
在过去25年中,美国在拥有大学学位方面居于领先地位,而现在美国只是在第12位。世界经济论坛的2010年排名中,在大学的数学和科学的教学质量方面,美国在139个国家中只排名第52位。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在数学和科学成绩方面,美国15岁的青少年逊于一般发达国家的同龄人。美国15岁的青少年在科学方面的成绩排名仅为第17位,在数学方面为第25位。在美国,近乎一半的科学领域的研究生是外国人。
十年前,美国在人均宽带互联网的使用方面排在世界第4位,而今天,排名落至第15位。2008年美国在世界专利申请上超过日本,到了2009年中国在全球创新专利申请方面很快超过了美日两国。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母亲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为1/4800。和其它许多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在产假政策上也略逊一筹。2010年,美国在43个发达国家中排名第28,比2009年的名次下降了1名。列格坦的研究也显示,美国在其人民的健康指标这一栏仅排名第27位。根据OECD的研究,美国人的人均寿命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指数要低,然而人均花在医疗方面的钱却是居于首位。这难怪OECD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在幸福指标方面,美国仅排名世界第13位。
自从2008年开始,美国堕入二战后持续最长、打击最惨重的经济危机。自此,“美国衰落论”更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帝国分崩瓦解的速度经常快得惊人:葡萄牙帝国仅仅花了一年;苏联花了两年;法国花了八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花了11年;英国花了17年。美国历史学家麦考伊称,如果从2003年这一关键的年份算起,美国从权力巅峰到衰落很可能要花22年。这使得奥巴马总统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也提及苏联于1957年10月4日发射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引起美国警醒的往事,称美国现在到了“斯普特尼克时刻”。
“相对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国的生活标准将会下降。由此美国将失去权力和影响力。”加州大学两位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隆和斯蒂芬·科恩在他们新出版的《影响力的终结》一书中写道,“这一影响力一旦消失,就不太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返回。”
美国放弃台湾?
如果说更高涨的“中国威胁”论是美国保守派对于美国国力衰落的一个本能反应,那么,乔治·华盛顿大学格拉瑟教授公开呼吁美国重新思考对台湾的“安保承诺”则是温和派的自然结论。
“大多数国家不会冒着大规模战争的风险来保护其他地区,美国最为特别的是,它不但一直这么做并且还在这么做。不过美国必须思考,在局势改变的情形下,这么做是否符合它的利益。我只是诚实且诚恳的提出这个问题,认为它应该被重新分析。”格拉瑟教授说,“如果你认为中国有无止尽的目的,任何在台湾议题上的让步只会养大中国对外扩张的胃口,那么就有理由说美国应该加强对台湾以及其他区域国家的承诺。我提出的论点是说,如果你不认为中国大陆像前述这样,它的目标并非无止尽而是有限度的,那么就有理由相信,美国减少对台湾的承诺可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可能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学院派人士像格拉瑟教授一样遭到台湾在美国的利益集团的强烈攻击,他关于美国对于台湾保护应该重审的提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弹。
“美国放弃台湾?这不会发生。”顾石盟对《看世界》杂志说,“美国向台湾作出的承诺是法律性的、政治性的,也是道义上的。后者尤其对(美台)关系发挥着实际重量。只要台湾的行为负责任,美国将站在它的左右。”
对于中国,在全球力量转变的大时代里最为关键的问题并非美国何时衰落,而是中国是否准备好行使全球领导权。毕竟,中国从全球战略、政府的决策以及执行政策能力、驾驭外交事务、政治体系的吸引力以及大众的成熟和开放度等方面仍然还在“成长”过程中。而中国需要自己讨论、决定以及形成共识的问题是: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一个世界?中国未来需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最终,中国面对的真正的评审员并非世界,而是自身。
(摘自《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