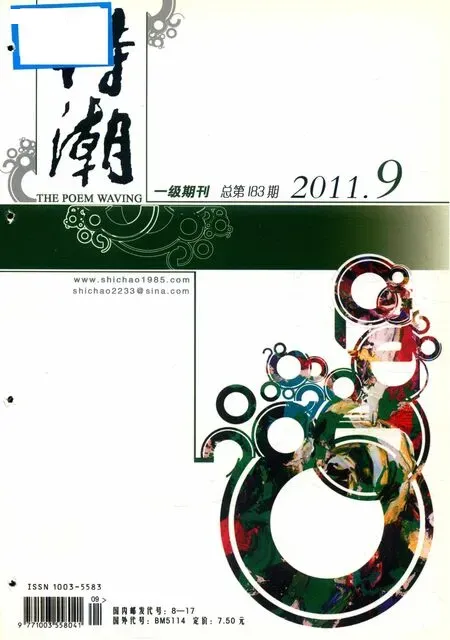词的言说
而什么样的词被雪裹着形成,/根据风,使你前趋的风。
——[德]策兰
19、20世纪之交大动荡的年代里,“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传承者,他们能够做到不为一时的现实功利所动,甚至不怕被流放,而执著于对俄罗斯正义灵魂的获救等问题进行探索,这与他们19世纪前辈知识分了的精神传统息息相关,却闪烁永远的光芒……
英娜·丽斯年斯卡娅写于1996年的《哦,那些词语多么令我痛苦……》是在回洲那个时代不能自由表达的全部痛苦,而诗中的“寒霜被称作白银”,是对“白银时代”最传神的诠释——白色、寒冷、凌厉、严酷、死亡。“没有这样的火焰,可以用它来温暖/红色的血球”,词语的孤独一如诗人的孤独;女诗人与词语一起承受极度的寒冷,却愈显出诗人的沉潜,以及高莽先生所说的“苦难的高贵”;“主流的词语/隐匿了次要的含义”“生活曾在我的眼前/而一切隐藏在字句里”,是那个时代诗人对表达的恐惧,“就像书页之间/夹起一枚槭树的叶片。”诗内的暗示,像一行先生在《词的伦理》中所说,暗示出物自身幽暗而隐秘的部分是对遮蔽和无名之物的保护或看护,气氛构成的……以及关联的至离的启示性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对可见物或不可见部分的言说。而事实上英娜·丽斯年斯卡娅在诗中的“只有在死神面前/一切事物才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钉子成为钉子插在自己的孔中,/而高处成为天空”,“钉子”这个醒目的意象作为词语的隐喻,它的决绝、忧伤在于直面死亡,灵魂才能获得自由“幸福”,才能获得一种自山表达的悲剧性的悖论而令人伤感。怀抱的只有词语——她说“我用微薄的食物和有罪的思想/喂养着词语”,就像喂养自己孱弱的孩子并和他形影相依,执著于与那个时代抵牾的一种精神的纯粹和勇敢,对于词语生死相依的挚爱,甚至可以为词语而先去赴死——“请先杀死我吧,然后再杀死它”——这正是真正的诗人的一种宿命。
诗人洛夫说,“字如钉拔出可以见血,诗是语言的最高艺术,对强调语言的先锋性更为决绝,‘飞’起来时必须死而复生,如‘蝶从千冢中翩跹而出”’。王家新在他的《尤今,雪》一诗中写道:“一个深夜写作的人/他必须在大雪充满世界之前/找到他的词根”,“火雪充满世界与一个诗人对‘词根’的寻找,这构成了一种宿命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也许永远难以消除。”如策兰“他作为一个幸存者只能与他的母语相依为命,纵然那同时又是一种枪杀他母亲的德国士兵所使用的语言” (《王家新:雪的款待——读策兰诗功)。
英娜·丽斯年斯卡娅1928年生于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巴库市,1978年参加地下文学丛刊《大都会》。她与利普金、阿克肖洛夫自愿退出苏联作家协会,以示对苏联作协开除维克多·叶罗洛菲耶夫和叶市盖尼波波夫的抗议。1994年由普希金基金会出版了她的诗集《历尽劫波之后》,索尔仁尼琴的信作为序言,获《旗手》杂志奖;1998年获俄罗斯国家奖;2009年“因其俄罗斯诗歌语言的透明的深度,并多年以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悲悯情怀”被授予俄罗斯国家“诗人”奖。诗人、《诗歌与人》主编黄礼孩为英娜·丽斯年斯卡娅颁发“第五届‘诗歌与人’诗人奖”,并出版了她的诗选。
“白银时代”正像俄罗斯本身一样,当你身在其中时你会不知不觉地被感染和熏陶,总有一种激情被唤起,而要你说出时,却只能用别雷的一首诗来回答:“风从遥远的地方带来/不可言传的春天的歌声,/这儿那儿露出了/一小片明亮深邃的天空……风从遥远的地方带来/你的明丽的歌音。”
2010年底,我与诺奖前评委主席(现系评委)、瑞典诗人埃斯普马克在上海有一面之缘,他对诗歌语言中词的看法吸引着我。他去年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黑银河》诗集里,一首《语言死去的时候》表达了什么是诗歌中词的言说。在与他一起喝酒时,我说了他的这首诗给我的深刻的印象,诗中出现了诸多“词”的并蹬意象,分成两个层面来表述。一是一些如“掀翻土地的词”——潜意识中氤氲的不断萌动且充满生机的词;炙热而感受着生命疼痛,“带着伤”的词;而对世界的喧嚣,表现一种存在之思,即“突然静思的词”;表达一段情感经历时令自己沉醉的,甚至行气活血激发起情欲的“溢出暗香的词”;纪念被历史遗忘却能于瞬间“给死者生命的词”,这些意象使诗歌永远充满了鲜活的气息。另一层面写了被人忘却的虚无,一种悲哀:“这么多影子在消散/被迫进入最终的流亡/没名没姓”;一些死去的语言“长满荒草,没人再读”,而词的再生必须忍着“死去第二次”——在和埃斯普马克喝酒时,我问起这个为什么要死去两次,而不是死一次,或三次,他可能因喝高了,一时竞说不出话来——我想到了它的哲学意味,是否必须在否定之否定之后才是词的再生之时?值此,诗人在创作时为获得语言中一个个词的再生而战栗,亦如诗中所表述的那样,那些词像“脚就会突然跨过铁轨”,像“树冠的苍翠,溪流的清爽”,新鲜而生气盎然。这些词的来临的神秘莫测,落笔于纸的那种猝然而至,犹如神握住你的手写下了急速而至的诗行,令诗人惊异不已——如埃斯普马克所言:“没人知道风想让我们做什么/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它的陌生化,它的多义性,才是现代诗永远的魅力:“我们听见树上的鸟鸣/但声音落向何处?”
萨特在《论诗和诗人》中说:“全部语言对于诗人来说是世界的镜子。……词的发音,它的长度,它的视觉形态合在一起为诗人组成一张有血有肉的脸,这张脸与其说是表达意义,不如说它表现意义。”
瑞典诗人谢尔·埃斯普马克《语言死去的时候》
(李笠译):语言死去的时候/死者会跟着再死一次/那些潮湿的田埂/掀翻土地的词/装热咖啡的容器边角磨损的词/带着伤/对着窗和喧嚣的榆树/突然静思的词/黑暗中/手抖颤着寻找时/溢出暗香的词/给死者生命的词/鲜活的记忆/刚被历史刮掉//这么多影子在消散/被迫进入最终的流亡/没名没姓//五十四个字母组成的站牌/长满荒草,没人再读/你默默地忍着/只要这些死了第二次的词/留下泥土的苦涩/树冠的苍翠,溪流的清爽/脚就会突然跨过铁轨/没人知道风想让我们做什么/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是的,我们听见树上的鸟鸣/但声音落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