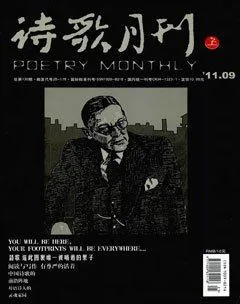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诗
如何能够写出一本好书?写一本体现了时至今日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水平、感受能力、语言特色、鲜明风格的书?这是一个问题。它的重要程度,大约仅次于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每个写作者在试图写一本新书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件事,我在做《诗坛N叟》的准备工作时亦然。
概括地说,我写《诗坛N叟》是想沿着自2003年《非典时期的了了特特博士》(2003年6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开始的路子,沿着《34份礼物》(2004年5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版)、《田楼,田楼》(2006年10月中州古籍出版社版)、《枫叶上的比尔》(2006年6月深圳海天出版社版)、《洛水之阳》(2007年4月河南文艺出版社版)、《四方步》(2008年3月香港美术市场出版社版)等诗集中的不同探索点继续前行,或者叫“撮其要,融会贯通”,以期形成自己创作特色。
我认为《非典时期的了了特特博士》是我在1992年同时出版三部诗集《不存在的女子》(1992年8月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名城与门》(1992年9月文化艺术出版社)、《日内瓦的太阳》(1992年10月台湾诗之华出版社)之后沉寂10年“突然苏醒”般地爆发。“非典”肆虐期间,十八天夜以继日挥写,43首诗歌塑造了了了特特博士这个忠厚憨直、对人生有着“另类体验”却不放弃修身达人使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夸张的笔触,跳跃的叙事,人物亦庄亦谐行为方式的自然表达,帮助我完成了从“朦胧诗歌”到“平民诗歌”的转变。从此我的艺术感觉之火重被点燃,新的创作道路被打开,精神上回归写作状态。
接着,《34份礼物》延续了我肇始于1988年(《名城与门》)的“集约式写作”方法,通过34首诗歌真实表现了北京广播学院2003级文艺编导专业34个学生的风貌与神采;接着,我为自己当年插队四年多的那个豫南小村庄创作了由47首短诗组成的《田楼,田楼》,把第三代诗歌的平民立场贯彻到中国当代社会的最底层——为真实生存状态下的农民造像,诗集中配以他们的生活照;同一年,我为自己在加拿大留学读书的儿子写了21首诗,配上他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的一些照片、我请人为他作的21幅漫画,和请比尔本人写的“致本书读者的一封信”(中英对照)形成一部诗集《枫叶上的比尔》,作为给他21周岁的生日礼物;2006年我还完成了主要根据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记忆写成的诗集《洛水之阳》。这四本集子各有侧重,它们的探索点大致可以概括为:(1)集约式写作;(2)平民立场;(3)叙实性特色;(4)图文结合;(5)幽默风格;(6)联动写作。下面是我的简要论述:
集约式写作。往远处说,集约式写作可能与我大学生活的记忆有关;往近处说,可能与中年以降我的大学教师职业的思维训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