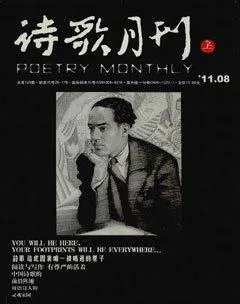惩罚(组诗)
惩罚
二十年多来,他一直不停地写啊,写,
他从中得到快乐,同时也感到
深深的失落:生不逢时啊,
诗歌不能让他出名赚钱,而且耽误仕途,
更无法藉此博取心仪女子的芳心。
想到这里,灵感瞬间被激活了,
于是他又投入了紧张的造句分行。
现在诗人已不再年轻,当然还不算太老。
他以娴熟的技巧、超常的毅力
继续消耗剩余的激情与才华。
他把写诗当作对时间最严厉的惩罚。
心理咨询
然后,年轻漂亮的心理咨询师打开笔记本,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她的对面
坐着一个年龄相仿、素不相识的女子,两人中间
隔着茶杯,桌面上的静物:
一盆鲜花、一本台历。
每次接待来访者,她总是这样,
屏息静听、轻声细语,并认真记录在案。
从不使用简单的肯定句或者否定句。
但这时,她的手微颤着;
她对自己提出了一连串无法回答的疑问。
有时候悲伤也像甲流一样会传染,
当它带着一股淡淡的花香。
她从一张憔悴的脸上理解了
另一个人的痛苦与无奈:谁在流泪?
谁能让一颗柔软的心依然快乐,当它小心翼翼
卸下了黄金盔甲,而永无伤害?
而她经历了这场未曾经历过的危情。
哭丧
哭丧婆穿素衣,缠小脚,
这时她开始高一声、低一声地哭。
没有眼泪的哭,更像婺剧里的唱腔。
不唱给生者,只对死者倾诉。
第一次哭丧眼泪就流光了——
她瘫坐在那儿,双手有节奏地拍打着
刚刚合盖的木棺;灵台烛光摇曳,
她不停地哭,哭她自己。
那一年,她儿子因病早逝。
村里的长寿老人死去。那是喜丧。
最悲伤的人,是静静地躺在
棺椁中的死者;被哭丧婆深深打动的人,
是那个头戴鸭舌帽的民俗学专家。
刻有名字的陶瓷碗
春节回老家,我又捧起了这口
旧陶瓷碗:碗沿有几处小缺损,
碗底刻有祖父的名字。那黑色字迹
显然不太工整,但依然清晰——
说得不错,艺术之美源于生活之真——
盛饭的时候,我读到它;吃完饭,
我又读到它。祖父已离世多年,
记得当年,他拿起小铁锤、细凿子
在碗底一笔一划刻下自己的名字,
像一个小心谨慎的民间艺人;
然后涂上墨汁着色,用抹布把碗擦干。
那时,我面黄肌瘦还是个懵懂少年。
兔年写下的第一首诗
除夕夜,我面对电脑写一首诗,
但是爆竹声铺天盖地,扰乱了我的思路。
我被迫中断写作,暂时给这首诗
留一截兔子尾巴。不想看春晚,
书也看不进去,那就翻读手机短信,
顺便简单回复。都是一些异口同声的祝词,
都是一些热情洋溢的客套。
是的,生活照旧,看你如何翻新。
现在我44岁,再过一分钟,我就45岁了。
再过二十年,我还能读诗、写诗吗?
还会有人记得我的诗吗?
——谁知道,管它呢。
我发现楼道那盏声控感应灯出故障了,
它迟迟不肯熄灭,在喧闹和狂欢平息之后;
这只天生蠢才的大傻眼。
在绿缘花木场
南方的春天一概湿气偏重,以致于
给我的忧郁增加了水分与重量
最高的是天上的阴云,最低的
是地上的枯叶,我与树
并立,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
春天还在继续蔓延:从合欢、含笑、喜树
三角枫、六月雪、八角刺,一直铺展到每一片树叶
并且投下冬天残存的灰影
如果春天可以缩小,就缩小到一只鲜花盆景
让蜜蜂在季节的案头陷入迷失
在绿缘花木场,我看到,最坚硬的是铁树
最虚弱的是风,潮湿的风
吹进我空荡荡的体内
不可避免地,被我瘦瘦地挡了一下
我整了整衣角,像一棵患上风湿性关节炎的香樟
裹紧自己的年轮
一个内在的人
他习惯于低着头走路,躺下来思考。
当他推开老百姓药房的玻璃门,一个人
回到拥挤的大街,你猜那手里拎的是什么?
他近乎抽象,而那移动的背影
是具象的:冷风中,浅灰色的风衣
紧裹着一颗孤独的心。
他习惯于以旁观者身份介入现世生活。
夹在街头闹剧现场的人群中间
努力使自己保持中立。
他想:与其在公园里筹备感情投资项目,
不如在市中心规划一座清冷的寺庙。
他想到的总是比看到的多。
他能做什么?最好做自己的忠实保镖。
别叫他表态,他宁可成为感情丰富的大哑巴。
不是不得已,而是不愿意。
臣服于内心与自我。
他出生卑微,时运不济,其性格
仍然完整:三分自卑,加七分自尊。
他从大街拐进小巷,手里拎着东西。
你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你,
当他转身。他是他自己,而
你是谁?为何尾随着他?爱着他?
在古樟树下
1
我不禁为某种奇异的力量所吸引
它来自于古樟树那庞大树冠
粗壮而挺拔的树干
裸露地面如同龙爪一般的根以及
沿着树干跋涉在悬崖峭壁与深壑险谷之中
缓缓而上的蚁队
2
古樟树沉默着,每一片深绿的叶子
都是自由和独立的存在
我听见鸟类在茂密的枝叶丛中婉转啼叫
仿佛清凉的露珠滴落
仿佛快乐思想者
在沉思的间隙吹响了春天的口哨
3
小鸟在空中筑巢,松鼠在枝头跳跃
树叶微微转动,遗漏点点光斑
我相信,任何事物的内心都是愉悦的,且不可言说
包括这棵返老还童的古樟树
尽管它主干早已中空
4
坐在古樟树下,让我多歇息一会儿
让我放低姿态默默地注视
一只蚂蚁、一株小草、一片在风中
旋转而下的落叶
独享那份静美,让我得到光阴的恩宠与庇护
让孤单的影子被巨大的浓荫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