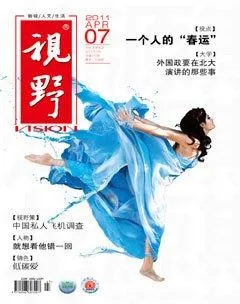风水:中国城市的宜居梦想
关于中国的风水(术),可谓毁誉参半,既有趣而又复杂。有趣,是因为到每一个城市,从出租车司机到地方行政长官,从街头的算命先生到大学教授,都习惯用风水来解释发生在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事件,从官员的升迁,到城市经历的灾难或发展,都与城市周围和城市内部的景观改变建立起联系。复杂,是因为风水从古到今,从来就飘忽不定,解释不清,再加上好事之徒极力渲染,而所谓“学者”又以捍卫科学自居,破口大骂,不论道理。
实际上,如果理性地分析风水术和风水景观,问题可能并不那么玄妙。首先,必须明确(看)风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文化对不确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一种景观认知模式,包括对环境的解释系统、趋吉避凶的控制和操作系统。
风水是人潜意识的生存选择
风水的深层结构是生物的,是审美的。风水感应——环境吉凶感应,源于人类漫长生物进化过程中在环境中的生存经验,表现为人对环境吉凶判断的本能,比如进入峡谷的压迫感、无垠沙漠上的恐惧感、面对急流时的不安感、靠山面水的安全感、身处暗处放眼明处的优越感、四壁围合的紧张感等。正是这种本能的景观感知和吉凶判断能力,使个体得以生存,而个体的生存经验成为群体和人类共同的心理能力。所以,风水是审美的,是源之内心的。
附着在生物本能之上的是风水的另一深层结构,那便是“文化基因”上的景观吉凶意识,体现为文化的图腾与禁忌。中国风水中对庇护、围合、藏匿、捍卫型、幽闭性景观的偏好,体现了中国风水文化的独特性,源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独特的农耕生态经验,当然也不排除各个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的独特的风水吉凶意识。比如《周易》的“利东南不利西北” 的风水方向吉凶意识,实际上源于季风性气候下先周民族的农耕生态经验及其与周边民族的长期斗争经验;比如风水中对重关四塞、罗城环护的偏好,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广大地区农耕经验中对丰产而安全的盆地景观的适应……所以,风水是先民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为适应环境,而经历无数次失败和实验后关于环境适应的宝贵遗产,最终都通过某种禁忌而成为集体的风水意识。
这种种审美的和禁忌的风水,实际上都被凝练为人们关于天国或仙境的理想模式中,最终通过“风水”两字概括: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故好风水就在于“藏风聚气”——山环水抱,罗城致密,水口关栏——一个活脱脱的“葫芦模式”。难怪,道家把葫(通壶)芦和壶天当作仙境,概括为“一壶天地”。
“葫芦”是最好的风水模式
既然一个理想的风水景观模式是一个四壁围合,仅有一豁口和廊道与外界相通的葫芦,那么,根据葫芦落到之处的不同,便有了不同的城市或居所的风水,我想大概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五种。
第一种是坐落山顶的葫芦,即昆仑山模式。无论是在神话中,还是在道教传说中, 昆仑山都被中国人作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神山仙境加以描绘,并不断加工提炼,终于使它成为一个能满足人的一切欲望,甚至可以使人不死的理想境域:“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山海经·海内西经》)在此高峻的孤岛之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淮南子·形训》)。世界有两座城市堪称昆仑山仙都落凡,其一是印加帝国的马丘比丘,而今已成废墟;另一座便是中国西藏的布达拉宫,至今香火鼎盛。只因这样的城市实在太过理想化,大有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因而只能作为神圣的宗教场所。
第二种是飘在水上的葫芦,即蓬莱模式。诸仙山俗以“蓬莱”概而名之,故可称为蓬莱模式。蓬莱“对东海之东北岸,周回五千里。外别有圆海绕山。圆海水正黑,而谓之冥海也。无风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来,惟飞仙有能到其处耳”(《十洲记》)。可以看到,这东部海中蓬莱仙境与西北部之昆仑仙境,竟都有一些趋同化的结构特征:高峻的山体,被重洋所阻的岛屿,非羽仙不可及,还有珠玉、黄金及珍禽异兽等珍贵的资源。中国的大江大湖中也多有许多村镇,保持它们的岛屿状态是维护其好风水的必要条件,然好事者不谙此理,修路筑桥,往往把好风水毁得一干二净,使其失去令人向往的魅力。
山间的葫芦,即桃花源模式可以称作第三种。读一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你便可知中国文化中理想风水的最佳景观格局:一条溪谷,夹岸桃花,经一小洞,进入盆地,豁然开朗,阡陌纵横,有鱼塘桑竹之属,群山环绕,内居者只知有秦不知有汉。以此为模式构建的中国城市与乡村的风水景观有很多,杰出的大城市如关中的西安和咸阳,太原和成都也有同样的理想风水格局。长江流域和东南地区的丘陵盆地中的许多大中小城市、村镇,都堪称绝佳的风水宝地,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则更是处处都有如桃花源般的风水吉地。
另外一种是山边的葫芦,即胎座模式。穴(城市或聚落)对自然山体的傍依格局也包含在上述各个理想风水模式之中。对自然屏障的依赖性,既是人类的共同特征,更是中国聚落选址的风水必备。如同餐厅里吃饭,人们最偏好的座位是溜边靠窗的一排,大小平原和盆地中的城市和聚落风水的最佳处仍然是溜边:坐北朝南,背靠山脉,面向平原(明堂)。明堂越大,则格局的气势越大,而“靠山”的特征从不可丧失。北京堪称有最佳的风水,背依军都山脉,并连接太行与燕山山脉,俯瞰的明堂乃是中国最大的平原——华北平原,恢弘大国之气势,格局之大,无出其右者。对大明堂和强靠山这种景观格局的偏好,风水上有形象的比喻:胎息!好风水源于生命对母体的依赖,可以理解为人对自然的依赖。
我想描述的第五种类型是水边的葫芦,它有拥山抱水的港城模式和长藤结瓜模式两种。港城模式以拥山含水最为理想,次之则是有水而无靠山。它可以理解为“山边的葫芦”模式的一个亚型,只是把作为明堂的平原换成湖海。但北边(包括东北和西北)有靠山仍然是理想风水不可或缺的要素,大连、广州、杭州、深圳、昆明都堪称佳地。大连坐西北而面东南,东南海域又有大山、二山和小山诸多岛屿,构成水口关栏,藏风聚气,当然有极佳风水;广州大局也是坐西北而面东南,背靠粤北绵延群山,面向珠江口,而水口含合,论都市风水,岭南无出其右者。“水边的葫芦”的另一种格局是长藤结瓜。傍依河流廊道是聚落风水的理想格局之一,以河道之凹岸(即非侵蚀岸一侧)最为理想,是聚落有三面环水之态势。小河小溪只能承载村镇,大江大河方可承载大都会,如南京、武汉、重庆等便是典型。
必须强调的是,理想风水格局之间是可以复合而存在的,而且,复合程度越高,风水越好。这点也可见北京之缺陷,那就是缺水。试想,如果北京南方有一如太湖般的水面或如长江般的大江,那该多好!
从风水意识的深层含义来看,我们关注的应该是风水的审美的、非功利的层次。实际上,今天的所谓风水已不再是农业时代的风水概念。现实的功利性往往替代了对理想风水的追求,昔日的许多风水宝地,如今已风光不再。
(刘新勇摘自《中国国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