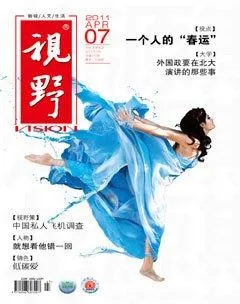字典里的中国
爱女生,更爱祖国
无数中国人的人生第一次都与一本字典相关。我们说话的腔调始终规范,且整齐划一;天空,总是“万里无云”的;走过的路上,必定是“载歌载舞”的;心情“兴高采烈”是必须的;见到五星红旗,立即想到是“烈士鲜血染成的”。
这是这本字典对几代中国人所产生的深入骨髓的影响。
男生甲的第一封情书写于小学四年级,为了搞清楚“爱”与“喜欢”哪个更精准而不得不求助《新华字典》。而答案却让他更纠结:字典上,“喜欢”和“爱”都是“对人或事物有真挚的感情”,比如:爱祖国、爱人民,当然还有“爱惜、爱护”的意思,但用于向女生表白好像不是那么靠谱,因为对应的举例是:爱集体、爱荣誉。
男生甲怎么也无法将集体和荣誉与自己体内的荷尔蒙等同起来。在私底下,许多遭遇青春期的男生都会承认,当年都曾厚着脸皮,在这本字典上查找过“敏感词”,只是答案都不太给力——比如,“性”只是“男女或雌雄的特质”;“精液”就是“雄性动物体内的生殖物质”;而“生殖”,也就是“生息、滋生”……
同志乙生于20世纪60年代,打从他懂事起,“同志”就是社交场合上最普遍的称谓。尽管在这本字典上,“同志”是“志趣相同的人。特指在政治上立场和见解相同的人”,但他与所有同龄人在情书或公开场合里都情愿彼此“同志”。
同志乙对这本字典的几乎所有释义及例句都能如数家珍,只是在若干年后,同志乙在指导儿子写作文时,常常感慨词不达意。比如,在向儿子解释“颠沛流离”与“倾家荡产”时,熟悉的两句例句便脱口而出:旧社会人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地主的剥削使农民倾家荡产。但儿子却不买账:现在不是也有人过着颠沛流离、倾家荡产的生活吗?
今天,就要配给你了
从60后同志乙,到80后男生甲,再到同志乙的90后的儿子,上小学语文课的第一天都曾被通知:请同学们尽快去买一本《新华字典》。
从1953年至今的57年,《新华字典》发行逾4亿册,这还不包括盗版的。无论从发行量、普及面、影响程度,还是读者忠诚度来看,它对中国人的意义都类似于《圣经》之于基督徒。
从第一版开始,《新华字典》就以“新华”的视角系统性地创造新话,重新划分世界地理与历史,将“旧社会”与“资本主义”切割开来,按字典上的例句,叫做“划清敌我界限”——作为新话,“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马克思的重要理论全都收录其中,在新话系统里,连“娶”、“嫁”、“媒”都成了旧社会的产物,“配”,才是“男女结婚”的新表达;“乞丐”什么的全是剥削制度下的毒瘤,因此在“新社会里再也看不见蓬头垢面的乞丐了”;美帝国主义“卑鄙无耻”,尽管“一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吓得打哆嗦”,但“这笔血债一定要偿还”。“敌我”的“三八线”遍布字典各个角落,即便是“淋病”,也只“在资本主义社会很常见”。
一颗红心累不死
如果说53版的《新华字典》是知识分子主动的“思想洗澡”,而到了71版的时候,《新华字典》已经全面被工农兵来营造了。
曹先擢的另一个历史身份是《新华字典》71版编撰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工宣队与军宣队的干部,以体现“工农兵营造话语系统”的时代要求。
时代要求编撰者将“封资修”全面赶出字典。比如,被划分为“剥削制度的产物”包括:婊、娼、妓、嫖、妾、宗祠、寺庙、伦常、典当、掮客;还有比“封资修”略显进步的字词,包括:官、自由、民主。
若干年后,同志乙被公派到当年在《新华字典》排名倒数第三位的“美帝国主义”考察,看到自由女神的那一刻,他条件反射地在脑海里对“资本主义自由”的释义轰隆隆过一串惊雷:在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只有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
尽管如此,《新华字典》仍是同志乙当年最心爱的读物,因为“那是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文革”期间,《新华字典》成为市面上惟一流通的一本字典。所有词条,事无巨细,都经历过编撰者的好几道“政审”——例句“巴不得马上回家”,革命性不强,改为“巴不得马上返回战斗岗位”;例句“累死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工作热情到哪里去了?删除;例词“背着太阳”,有影射毛主席之嫌,改为“向着太阳”;例词“利人利己”,不符合时代精神,改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找前途,查字典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而直到80年代,字典才开始试着回归常识。
许多行为与现象也取消了“主义”的界限,比如,妓女、嫖客、佣金、典当、抛售、出租等;许多例句则直接换掉或去掉带有意识形态切割的主语或定语,简化为例词,比如,“帝国主义前途暗淡”,要简化为“前途暗淡”。
字词表达的多样化也在逐步恢复。近年,“吧”这个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如酒吧、网吧、吧台,2004版修订时,就在“吧”字下增补了新的义项,下一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甚至考虑收录“给力”。 这样一来,表达是丰富了,但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与套话仍然没有退出历史。
在一些报道标题中,你仍会看到“某社会青年逼迫同学卖淫”的字眼,这是在“文革”前流行起来的叫法;消费埋单要开发票,收银员总会问你:“抬头写个人,还是单位?”在《新华字典》里,“单位”指“机关、团体或属于一个机关、团体的各个部门”,而个人,是被排斥于单位之外的无组织者。而在英语里,“单位”这个词是个谜。
绝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刻意回避这套话语,在网络世界中,数量庞大的网民也磨合提炼出自成体系的一种腔调,这两套腔调大多可以相互转换、翻译。
比如,男生甲说,“小姐”,按新话体,是“剥削阶级的产物”、“卖淫为生的女人”,不过,最近改叫“失足妇女”了。男生甲也有不得不操起新话体的时候,比如,作为班级党支部书记,主持班级的党支部生活和发展新党员的场合,男生甲总是需要努力板起脸,提醒别人“注意思想觉悟”。临近毕业,男生甲的工作还没落实,私底下,一帮哥们儿姐们儿有拜卧佛(OFFER)的,有算塔罗牌的,有把老爸老妈三姑六姨的关系全使唤上的……但在系里组织的就业动员大会上,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思想”。“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主持人说,“相信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也是已经被《新华字典》规划好了的,在第10版661页:“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周成志摘自《南方周末》,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