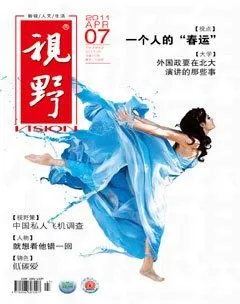一个人的“春运”
胡蓓蕾想到了最坏的结果——遇人打劫,就放弃所有东西,只顾保命。
他把一百块钱用力地折了两下,塞进了袜子里——如果遇到抢劫,这将是最后的救命钱。
历时13天,行程3700多公里,搭了25辆顺风车,从南京到乌鲁木齐,没花一分钱。当同学们还为一张回家车票发愁时,这名南京师范大学的大四学生以免费搭车完成了一次刺激而温馨的“春运”之旅。
看名字,以为是个女孩子。然而,他却是个身高一米八的帅小伙。
一路向西
一切均源于一部名为《搭车去柏林》的纪录片。片中主人公从北京出发,只依靠陌生人的帮助,搭车88次,最终抵达柏林。去年9月,胡蓓蕾看后难掩兴奋,其中一句话便刻在了心里: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也不会去做了。
“如果能搭车回家就是一个非凡的经历。”胡蓓蕾相信行万里路远胜读万卷书。多位同学劝他慎重,女友也急了:“你又不是探险家。”
的确,从南京到乌鲁木齐有近4000公里,只靠搭车,并非易事。
胡蓓蕾祖籍江苏,一岁时随打工的父母搬到乌鲁木齐,一直在那儿生活到19岁。他考上了南京师大,学习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这个要求严谨和细致的专业其实不适合他有些天马行空的性格。他的学习成绩不理想,但多才多艺。他是南京师大足球赛的最佳射手,是省级魔方速拧冠军。
出发前,胡蓓蕾在地图上仔细研究路程,突然有种感觉:顺着312国道从南京一路向西,似乎是在重演20多年前的故事:父母带着他,从故乡出发,去创造新的“家乡”。
2010年12月25日,西方传统圣诞节,他出发了。
从南京师大出发,坐公交车到312国道,他计划当天至少要到合肥。沿着国道,他边走边拦车,走了半个多小时,进了路边一座加油站。他预想,加油站应是搭车的最佳场所。他把搭车回乌鲁木齐的想法告诉大车司机,司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没人愿意拉他。一个司机甚至劝他,用学生证买张半价票,用不着这么辛苦。
继续徒步前进。他还在不停地招手,似乎没有人感觉到他的存在。“难道在中国搭车就是那么难吗?”三个小时后,胡蓓蕾有些不堪重负。他的背包有50斤重,里面有衣服、食品、帐篷和一双解放鞋。
“我当时真的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了。”胡蓓蕾回忆。
这时,他看到前面停着一辆正在检修的卡车。他凑了过去,对正修车的师傅说明来意。师傅将信将疑地让他坐进了驾驶室。师傅后来解释说,当时看他满头大汗,学生模样,不像坏人。胡蓓蕾很开心:终于有人肯搭我了。
胡蓓蕾发现,在服务区搭车的成功率远大于加油站。在合肥文集高速服务区,他相中了一辆奥迪车。展开招牌式的微笑,胡蓓蕾上前搭讪。没想到,奥迪车主犹疑了一下,查看了他的学生证后,居然让他上了车。
这成了胡蓓蕾13天旅行中最为愉快的记忆。事业有成的车主跟胡蓓蕾谈起了心事,虽然成功,但他仍然觉得缺少朋友。
当听说胡蓓蕾是学电气工程专业并即将毕业时,车主马上打电话给做电气工程的朋友,为他推荐工作。因聊得投入,他们还走错了方向,多开了一百多公里的冤枉路。可车主并不觉得冤枉,他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妻子:“今天我交了一个朋友。”
温暖的旅程
本来只是一次冲动而简单的冒险,却无意中成了胡蓓蕾了解和感受社会的机会。
在信阳服务区,他搭上了一辆重型卡车。两位司机轮换开,他也很快与司机熟络起来。
胡蓓蕾形容坐卡车是“全身都不舒服”,“浑身都痛苦”。
在从信阳到西安600公里的路上,他搭乘一辆拉起重机的载重卡车,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整整十个小时,只在午饭时间短暂休息了20分钟,下车后他整个人几乎散了架。但相比起其他社会车辆,卡车司机最好说话了。
大概是驾驶生活很枯燥,大车司机个个都有倾诉的渴望。
一位司机告诉胡蓓蕾,他们不是不想带人,主要是担心自己的安全,还怕发生意外要担负责任。
这似乎也是在中国搭车难的症结。除此之外,搭车有时还被认为是非法运营。2009年,上海白领张晖在上班途中,好心搭载了一位自称“胃疼”的“暗乘”,被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罚款一万元。
2010年12月30日,转了8次车后,胡蓓蕾到达兰州。行者的落寞,对于一名23岁的年轻人或许有点残酷。在兰州的一个小招待所里,他买了花生和啤酒,独自庆祝。“这是路上第一次感觉到孤单。”
13天中,胡蓓蕾很少住宿,大多在高速服务区的大厅里拼凳而眠,还睡过一次帐篷。饿了就吃些随身带的压缩饼干,泡上方便面,出发前再把水壶灌满。
简陋的跨年夜之后,他迎来一路上心情最差的一天。在青海收费站,他手拿地图不停地挥手,三个多小时都没拦到一辆车,以至每有车辆缴费时,工作人员都会热心地帮他问一句。
出发前,他预想在西部搭车会比东部容易。因为民风质朴,人们更愿意以提供帮助获得满足。事实正好相反。胡蓓蕾发现,发达地区的人虽多疑,但还能理解他的行为。西部人似乎就觉得难以理喻,大多张口就要报酬。
在青海收费站拦车的三个多小时里,胡蓓蕾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我是学生,没有钱。”但还有一位司机以为是自己搭车费要得太高,曾两次停下来,跟他讨价还价。
不过感动都发生在最后。在世界风库甘肃瓜州,这个身高一米八、仅60多公斤的男孩站在风中飘摇。一位司机滑行100多米将车停下,摆手让他上车。胡蓓蕾后来回忆说,那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是他听到的最美妙的声响。在去往哈密的路上,搭车司机甚至怕他没钱,还要给他一百块钱当路费。最后一辆搭他的车,听了胡蓓蕾的讲述后,司机说:“上了我的车,就算到家了!”
父母知道儿子的“壮举”后怒不可遏。他们都是生意人,不太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交付陌生人。弟弟则给了他一个“中肯”的评价:“哥,你越来越二了。”
有人认为,胡蓓蕾此行或许可以成为一次检测中国人的信任感的行为艺术。他本人并不赞同。“不是每件事都非要有意义。”他说,他从一开始就相信,“一定会有人愿意搭我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他在博客中写道:“25辆车子,无数的好心人,是你们让我相信在自己的天空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如果真心想做一件事,全世界都来帮你。不要让你的想法永远只是个想法。”
胡蓓蕾有一本中国地图册,每去一个地方,他都会事先撕下来,带在身上。如今,他有一个梦想:在26岁之前,把这本地图册撕完。
(张顺福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