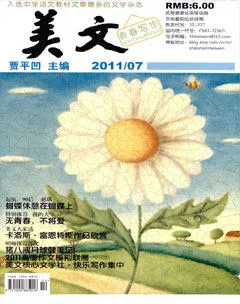小步的舞曲
许多人对新概念获奖作者都有认识的误区,以为他们可以保送大学,至少对于考大学有一定的帮助。但事实上,早在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就已经彻底取消了保送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如今司空见惯,当时却极新鲜的政策概念“自主招生”。
我可以算是“自主招生”的第一批获益者,原因是,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专业的名词。在我之后的那一届,复旦就正式铺开了自主招生的录取方式。
我于2004年获得第六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那时我高二,不是应届生。第七届时,获得二等奖,这在当时,几乎就意味着失去了与高校沟通的机会,直接回归考场。我理科成绩不佳,高二时却身在理科班,高三时转文,当时全年级180个人,我的排名是138。老师问我要考什么学校,我说我想考复旦。没有什么人鼓励我,班主任和年级组长找我谈话时,说的是十分蹊跷又幽默的话:“你有决心……是好的。”
好在上海的高考科目不多,3+1,理科卸下了物理化学之后,就仅剩一门数学是最大的磨难。彼时,我方写完20万字的散文写作及短篇小说集,后于2005年、2006年分别出版,几乎放下了一些学业。高三摸底考时,数学150分的卷面分,我只考了40多分。加上新概念的失利,只有平心静气地准备艰巨的复习任务,没有别的出路。当时总是扪心自问“我还来得及吗?”但不等回答,就又投入到汪洋一般的题海中。
如今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为纯粹的奋斗。我家离学校仅有5分钟的路程,但我每天6点15分就抵达教室看书,晚上7点离开。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位负责开门钥匙的男同学,因为实在被我的作息折磨得难以忍受。一天清晨他困势懵懂地对我说“我送给你一个礼物吧”。而后他递给我一把教室钥匙。
我的复习计划是极笨拙的。因我找出了高一高二全部的数学考卷,将错题一一订正。同时继续着数不清的周练、课堂练习、段考。因为错的太多,订正考卷时的抄题步骤对我来说是很费时间的。我便与老师商量,再给我一张空白考卷,我直接订正在考卷上。仔细回想起来,当时我有两个复习原则是非常有益的。一是我从不作弊,即使卷面再难看,我都能保证对与错立竿见影。当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德行,而仅仅是因为,卷子看起来会比较明晰。不会有模棱两可的地方。二是我不买辅导书做新题,因为旧题都没有消化完。
订正错题的过程是非常艰苦和枯燥的,绝不如做新题一样的有成就感。甚至会引得老师的反感,“你怎么还在做这么老的卷子啊”。“这个我不是讲过的吗?”但是我置若罔闻,呵呵,当时不知道是一股怎样的劲头,远不如现在这样圆融虚华。就是笨拙的、不解风情的晚上刻苦订正,到学校每节下课、中午休息、间中空堂,都跑去老师办公室,丝毫不给老师休息的余地(我现在都极内疚这样的行为,怕是当年数学老师看到我都会做噩梦)。
而老师的表现也是极有趣的,她总是看起来和蔼,实则也因为我难缠而避之不及。一会说“老师先吃个苹果好不好,你要不要?”,一会儿说“今天我儿子幼儿园要跳绳比赛,我能不能先走一下呢?”而对我来说,谁帮我讲题倒是不重要的,自己的老师不讲,就去找别班的数学老师。所以临到毕业时,我几乎是高三全体数学老师的噩梦了。
到了第一次模拟考时,我的数学成绩几乎已经能够稳定在110分左右。我的基本原则就是“我不奢望对,但是不能错”。卷面是极致变态的呈现,就是空余的40分,包括填空最后两题,选择最后两题,应用题,最后一道大题及最后第二大题的第三小题。除去这些惯例不会做的,其他的题我要求自己做到全对,事实也的确如此。
有了这110分,我其他科目正常发挥的话,要考复旦就仅差5~10分了。就在这时,我的命运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渐渐如砖瓦一般,给予了我人生最美妙的通路。
复旦每年都会举办俗称“加分考”的考试。考题包括10门学科,综合考卷,取得的成绩分为三档,A类为一本线即可录取(为的是能留住想考清华北大的上海考生),B类是线上加20分专业分,C类加10分。我参加考试的那年,是史无前例文科没有考数学的一年,我之前及我之后的一届都与此考题类型不同。我的考试一共分成两门,一门是文史哲综合,一门是英文。
我英文考的不错,文史哲综合也将将过得去,几乎没有暴露我知识结构的缺陷,最后加分20,但这与我意义不大。因为加的是线上分,我还是要考到复旦的录取分数线。就在我继续不停纠缠老师及折磨自己的档口,复旦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参加他们自行组织的面试。
当时我不知道这场面试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准备,事实上我们学校历年来也从未有人有此机会,根本没有前例参考。其实这就是后来的自主招生面试。
当年参加面试的人不多,40几个,分成文理两组。许多都是上海顶尖学校的优秀学生,面试他们,只是为了在加20分的学生中再挑选一批更保险的留在复旦。考题涉猎很广,有包括文学、哲学、历史,也有一些时政的评论。一周以后,我升到A档,虚拟录取。
这无疑是高考前最为振奋人心的消息了。我也是学校唯一一名补录为A档的考生。当时政治班50人,第一次模拟考20人上一本线,我位居18,几乎是以保一本为目标,但事实上,我只要考上一本线,复旦就能上。
所有的数学老师都安慰鼓励我说,我考110分很稳扎,只要放轻松,几乎不会影响大局。我也信了,当时时值上海的严冬,高三过半。我好容易订正完了高一高二的考卷,整理成册,每两周巩固一次,订正一错再错的题,杜绝粗心及遗忘的发生。老师还常在我的考卷上写“挺住哦” “加油哦”之类鼓励我的话,怕是我错题渐少,不再面目狰狞地难缠,终于放过老师了。
而我人生最辉煌时刻的到来,则是到了酷暑,公布分数的那一刻。我数学考了史无前例的139分,也就是除了最后一题,所有我落笔的考题,都对。我的“不能错”原则,也影响了我的同桌,她天赋胜于我,最后数学满分。我想我的原则,也许不够好,但至少是经过了两人的检验。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人生中所有的大考试中,我都运用了这般机械却有效的残酷方法。我中考时数学108分,除了最后一题全对。考研时亦是如此,我的专业全国只收1名学生,因为招的人少,几乎没有人知道会考什么,也没有所谓“历年考题”,但我还是考上了。
所以要回忆高考,我几乎没有什么浪漫的经验。我的高考历史,就是考数学的历史。我至今不知道数学的奥妙,可能一生都与之无缘。但我却需要它,我的复旦梦想、我的写作理想,以至于我如今能够就读于全国唯一一个“文学写作”的硕士点,没有数学是不可能的。没有曾经枯燥、绝望的重复操练,梦想只可能是空中楼阁。
甚至,数学会比新概念作文对我的影响都要大得多。写在这里,只是要鼓励所有的考生,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也无所谓什么“来不及”。尤其是应试教育中,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不需要太懂、只需要用功,要摒弃浪漫的想法,脚踏实地。
所谓“文学改变人生”的话,也是极有深意的。并不流于文学表面。走过高考,会发现“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人生任重道远,文学之路也是荆棘丛生,除却艰苦的努力,没有捷径。我也许是高考的成功者,但并不算文学的成功者。但我相信,从事任何一门事业,没有一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劲道总是不行的。希望大家将高考当作起点,守住自己,就是守住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