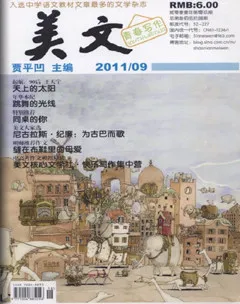老街漫游
困倦的下午,手捧一本书页早已发黄变老的书,怅然不知所云。风从窗外飘来,隐隐约约有一种像周记卤菜的味道,或像陈家铺子里醉人的米酒味。在这个难得放松的时刻,何不去游游久违了的老街?
快速地穿上平时懒得碰的黑色大短裤、宽大的白色衬衫,戴上有着十几年沉重生活记录的眼镜,骑上自行车,逃也似的出了家门,直奔老街而去。
每个人都有不同于别人的岁月,我也是。总是竭力为自己的岁月添加金色的光辉,可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岁月最多只像一杯橙汁,或是像夕阳西下时不小心丢下的那一抹余光的颜色,那是我极不愿看到的暗淡。感觉自己像一粒黄沙,有心去与那汹涌的浪涛争一争人们的高歌赞扬,可是更多的只是被作为沙石涂抹到某个角落,任由岁月流逝,渐渐地老去。人如此,老街又如何?
天色渐晚,太阳开始收拾光亮,准备休息了。边前行边四下张望,体验着曾经熟悉的感觉。夕阳余晖从繁密的树隙间漏进来,洒在我的脸上,阵阵的晚风吹起我的头发,带来一种舒爽的感觉。老街沐浴在夕阳里,像一个古老的传说,也如一首浑厚的老歌。每到老街都有一种特别的味儿,像从县城的学校回到家里。是啊,从小到大,生于此,长于此,老街不正亲眼目睹了我磕磕绊绊成长的日子吗?老街也已融入了我的岁月。
街边两排高大的梧桐树默默地守候着,叶子满是灰尘——有一阵子没下雨了。我缓慢地蹬着车,目光在街两边游移。街道两边的房子还是昨天的老样子,只不过青砖红瓦更加暗淡,屋顶的瓦松长得更高。熟悉的店铺依然在,即使它们很小、很杂,我也能一一叫出它们的名字。石板路有些残破了,也许它们也累了吧,毕竟它们比我的年岭不知要大多少倍。
夜幕初降,风也变凉了,阵阵从我只穿着拖鞋的脚丫子滑过,又拂过我的每一寸肌肤,一种清爽舒适使我的内心觉得分外宁静。
这是一个店面很小的理发铺,老板是一个六十开外的老头。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自降生以后就在他这儿理发,听妈妈说我的胎发也留在这里。过去在家读书时,很喜欢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与这个和蔼的老头子打招呼,喜欢听他说:“哟,又长高了哦!”
有几个老人围在梧桐树下下棋,他们可是绝对的棋迷——至少打我记事起就看到他们这么下着。没有坐的,每人搬半块青砖;没有桌子,干脆撂地开战;哪怕棋子早已旧得发黑,没了“老帅”就用酒瓶盖子代替。听着他们会心的笑声,看着他们惬意的生活,不禁在痴痴地想:若干年后自己也变成一个老头子,也能有这样的生活吗?即使只是棋盘上的生活,即使只是垂暮下一闪即逝的片段,活出这种滋味来足矣。
夜色渐浓,各家小店的老板都在收理自家的东西,为打烊做最后的准备。他们大都穿着露肩膀的背心、刚没膝盖的大短裤,趿拉一双哒哒作响的大拖鞋,一个个很悠闲,嘴里叼支烟,或衔着烟袋杆,端着小茶壶,听着黄梅戏。他们从不为自己的生意煞费苦心,似乎并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享受这份闲适而宁静的生活。这般平和,这般自然,这般毫无计较,倒真的让我有些眼馋了。
有几个拉板车的大叔归来了,屁股半坐在车上,一脚维持平衡,一脚轻点地面,车子便快速向前驶去。不需要任何燃料,也不要“宝马” “奔驰”的豪华,照样悠然地“开动”,而且洒下一路爽朗的笑声。望着他们潇洒的身影,心里又在痴想:那身价不菲的老板们,生活也能如此轻松自由吗?也许这些身板结实的大叔们在挥洒汗雨之后,数着为数不多的几块几十块钱,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绝对不亚于大老板们揣着几百几千万的支票,至少这些板车大叔们活出了一份坦然。
总感觉老街很老了,也许是因为从我记事起便听人们称它“老街”了。随着新街区的开发,它不再是集贸市场,没有大超市,没有名牌专卖店,没有十分招摇的明星广告牌,似乎已渐渐被人淡忘,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深深的感情,反而让我更喜欢这个纯天然的地方。在这儿我喜欢吃老街人自产的糖葫芦,喜欢看高高矮矮的孩子围着棉花糖机叽叽喳喳,喜欢嗅着风中散发的甜丝丝、暖乎乎的味儿。
老街很短,不一会儿便骑到了尽头。老街的另一边是霓虹闪烁的新街区,我毫不犹豫地折回了。
重新回到自家的阳台,捧起那本书,书名叫《岁月的痕迹》我恍然看到了岁月的年轮上那一个个圈圈的含义。岁月确实留下许多的痕迹,只是我们被形形色色的幻想或虚浮的功利蒙住了眼睛,丢了很多的东西,也增添了许多的烦恼。
很庆幸,我还没有把老街弄丢。
明师点评:文章真实地记录了自己漫游家乡老街的经过,细腻地描写了老街淳朴、平和、自然的风貌,表现了老街人一种无污染纯天然的生活状态,读此文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沈从文先生的力作《边城》。文中关于读书的安排和议论性的文字,不只是结构上的首尾照应,更是稍显散漫的笔墨的聚拢,更见得这篇散文立意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