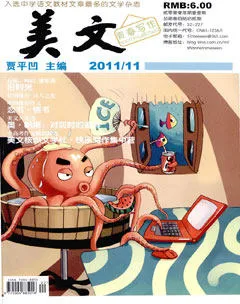现弱示强势不同因势利导两得之
张大文:1991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并被授予国家级“人民教师”奖章。1992年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现为复旦大学附中特级教师,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已发表文学作品1000万字左右。
战国时期的孙膑在齐国派遣田忌将兵直走大梁,迎战魏将庞涓,以解救韩国之危的时候,为什么故意显现疲弱之态,在魏地先做十万灶,再做五万灶,后做三万灶,表示行兵三天,一天不如一天,人马大为折损呢?从后来庞涓在马陵智穷兵败而自刭的结局来看,孙膑是通过强势示弱来诱敌深入,从而一举歼灭。然而,孙膑的谋划何以能遮住庞涓的双眼去一意孤行呢?这是可以经过分析得知的。庞涓是从魏与赵攻韩的前线应召回来的,他看到奇兵急速进军,经过大梁而西行,人已去,灶犹在,便耻笑它冒犯了兵法关于“百里而趣利③者蹶④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的告诫,而且眼见为实,更信奉兵法并不我欺,却远不能洞烛其伪;相反,在庞涓看来,目前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他们三晋(魏、韩、赵)之兵素来悍勇而轻齐,号齐为怯真是名不虚传,却远不知身遭算计;相反,庞涓大喜过望,利令智昏,不但在精神层面上失去警惕,而且在军事实力上弃重就轻,却远不防已陷绝境。
显然,这种种迹象都反映了孙膑策划的英明之处。孙膑是顺应着兵法理论固有的逻辑来进行策划的,使庞涓徒见形式,不明实际,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一回来便被假象所欺,只知道马陵上当,“遂成竖子之名”,这位兵法的信徒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这样看来,东汉时期的虞诩要通过增灶来示强,急行军越行,吃饭的人越多,因而灶头越多,要用这种反常的情况来迷惑对方,其难度显然大了许多。
当时,虞诩已被邓太后任命为武都太守,在从洛阳赶往甘肃成县上任路上,被羌人阻于崤山、函谷关一带。虞诩为了摆脱困境,利用羌人分扰旁县,分散兵力之机,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甚至将近二百里。这样的速度,不但不“军半至”,不但不“蹶上将”,反而兵力与日倍增。这不是太违背兵法了吗?这不是太无知妄说了吗?但是虞诩不怕,他认为行速之实与众多之虚,可使对方“必惮追我”;至于虚报的众多,为什么在对方看来已是“实有”,那是因为西边的武都已派“郡兵来迎”,当然要每天成倍地增灶了。可见关键在“郡兵”一说,可以化破绽于无有。
但是,无论减灶还是增灶,都只能在行军过程重施其技奏其效的。行军一结束,便须另有所图。孙膑于是集中优势兵力埋伏于马陵地盘,并把庞俊的一举一动纳入自己的设计之中:暮至马陵,道狭多阻,已是无路可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夜幕中隐约可见,却无法尽明其意;正要举个火看个究竟,却无异于自树靶子,死于万箭齐射之中。实际上,齐兵直走大梁之时,孙膑已布置重兵仍在大梁一带防守,此刻庞涓事出,便一举而虏魏太子申以归,取得击魏救韩的大胜。
在虞诩这方面,军队一到武都城里,便构成守城与攻坚的矛盾,灶头的多少对方已经看不到了,所以示强须另生一计。这个新计必须显示人多势众,并且让对方看得一清二楚。而贸易衣服,从东郭门出到北郭门入的回转数周的示威形式乃是使“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的最好办法。它是增灶举措在新形势下的灵活变通。
当然,在示强过程中也要根据具体情况相机现弱。刚进武都城,兵不满三千,被万众围困。为了打开局面,先潜发小弩,麻痹兵刺激对方并兵急攻,接着便动真格,集中相对优势的兵力,强弩共发在前,浅水埋伏在后,真是随机应变,以弱克强,转弱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