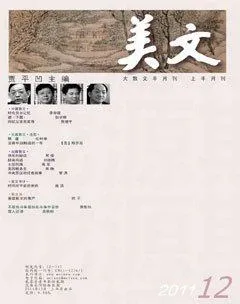重建散文的尊严
何平
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现执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99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批评。做规矩的学术论文,也做不规矩的文艺评论和媒体书评。近年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海文学》等发表文学批评40余篇,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奖。
这是我在《美文》“散文知道分子”专栏的最后一篇。
本来拟定的题目是“回到散文常态”。就是想你无论多么新潮和先锋,总应该讲常识守常态。想想这一年对当下散文说过的这些话;想想对当下散文种种病症批评的宽忍、节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想想汉语散文,尤其是散文经过“现代”洗礼之后作为一种“个人”文体曾经的辉煌和尊严,临到最后,我还是用“重建散文的尊严”做了这个专栏殿后的题目。因为,让我去说什么是散文的常识和常态,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在这篇短文中,我也许会重复和重申前面我已经说过的话。散文的尊严是人的庄严和真诚。因而,散文的屈膝是人的俯首和下跪。谈这百年的汉语散文,谈散文的尊严史,不能不谈散文的屈膝史。而今天我们躬逢散文“挥霍”的时代。美女赠我“王安忆”,说王安忆的《故事和讲故事的》值得读。信乎!如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说散文:“……字义的挥霍浪费,消耗了我们原本就有限的文字储存以及不断的积累,许多好字失去了意义,变成通俗的概念,许多好意义则无字可表达。由于小说和诗歌的生产及不上散文,其挥霍的程度也及不上散文。散文在挥霍文字的同时,其实也在挥霍文字所赖于表达的情感。在煽情和滥情的空气底下,其实是情感的日益枯竭。”王安忆用“挥霍”这个败家子行径来描述我们今天的散文,把准了时代的文脉。如果屈膝的时代是别人把“我”不当人,今天挥霍的时代则是自己把自己不当人。即便不屈膝不挥霍,散文还有个境界、品格的高下。我也认为王安忆这样说张爱玲其实不只是一个张爱玲:“张爱玲原本是最有可能示范我们情感的重量和体积,可她没有;相反,还事与愿违地散播了琐碎的空气。”是的,我们应该承认情感有小大之分,也应该承认作家的能力有所不逮,如周作人所说:“我平常很怀疑,心里的情是否可以用言全表了出来,更不相信随随便便地就表得出来。什么嗟叹啦,咏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戏,多少可以发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为艺术再给人家去看的时候,恐怕就要发生了好些的变动与间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很微末了。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最初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形容,更无论文字,至少在我是这样感想,世间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例外,那么我们凡人所可以用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要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琐碎的空气”在今天已经不只是局部的小气候,而是披拂文坛。那种“聊以自宽慰消遣”的文调文腔文风已经不是文人的专擅专宠,而成为普通文学公民所随手的文学家什,就像刨凿之于木工瓦刀之于泥水匠。散文文体的革命性、开放性在赋予写作者自由的同时,当然也为阿Q式的“同去同去”和“咸与维新”开具了通行证。于是,在一个富足而平庸的时代,散文的生产和消费市场像雪球一样越推越大。如果看我们今天散文生产车间的货色,最多的是栖身于多如牛毛的各式传媒的“新媒体散文”。这些散文氤氲着的是中产阶级或者沉浸中产阶级幻觉中的“摩登风”。如果中产阶级踮着脚尖也够不着,那就“小资”、“白领”一把,只是这样会自感委屈,自然字里行间会多一点怨愤和不平、多一点爱悦自己的撒娇和怜惜。这些散文的本质恰恰是以香艳的或者“假智”的“新腐新套”替代了旧文人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伤春怀人、三月小病和田园乡愁等等的“陈腐老套”;以“故作轻松”代替“一本正经”;以文字上的“小滑头”和批量复制代替“滥情主义”。问题的关键还不只在此,这些散文最致命的是,它所呈现的恰恰是描述的后道德社会“无痛”症候。在《责任的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中吉尔·利波维茨基谈到当代新闻时说:“人们不但消费着物品和电影,也消费着搬上荧屏的时事,消费着灾难,消费着现时的及已经逝去的事端,被如此制作出来的新闻,应和着个人享乐主义时代的社会节拍,既如同是一些高度写实的、富有情趣的有关社会日常生活的‘动画片’,也如同是一出让人喜忧参半的剧目。由此,朴素的责任隐没于毫不停息的新闻里,消散在由后道德主义时代的新闻所制作的场景和悬念中。”摈弃尺度、瓦解庄严,这些散文让我们享受到一种“无痛”的、麻酥酥的、微醺的、自恋的轻盈幸福感。 散文的“无痛”时代起来得早,也因为“无痛”式书写本质上从不掩饰自己经济、文化和思想上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它的假面在许多批评者不遗余力的揭破下早已难以遁形。即便如此,有那么多的“粉丝”“票友”,广阔的市场消费能力依然强劲地支撑着“无痛”式散文生产时代的延宕。但市场注定是喜新厌旧的,它意识到危机,就必然生产出新的产品,开辟新的市场。于是,“无痛”式书写不见式微,“炫痛”的时代已悄然降临。在“无痛”的假呻吟、小欣喜为人所诟病之后,当下中国散文开始打出悲情、苦情主义的牌。“炫痛”一定意义上是“无痛”的升级版。无须列举,苦难、苦痛予我们,既是漫长的历史记忆,同时又是触目惊心的现实经验。“痛”自然是我们无法绕开也书写不尽的文学主题,书写苦难和苦痛也容易获得道义上的支援。因此,和“无痛”相比,“炫痛”的虚和假更加具有隐蔽性,更加容易混淆视听,招人怜悯。但“炫痛”不是为了“揭示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炫痛”的目的不是反思,而是致幻;不是为了记忆“痛”,而是让你遗忘得更快。他们不问病灶,不查病源,而是挥舞着“苦难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利锉,漫不经心地锉钝你在惨淡的现实中可能滋生出的反骨。他们在城市的楼头、温度宜人的居所和清雅的案头,以一种自炫的语调告诉你:“只要悲痛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生活便都是可以好好珍惜的。”如果在“无痛”式的写作中我们还可以轻易地识别出一副自以为过得比你好的小资或者中产阶级嘴脸,现在“炫痛”的书写者俨然以一副过来的受难者自居,让你要对他们动一番拳脚还得小心他们迎上来的道德、政治等等的冠冕堂皇的盾和矛。说到底,“炫痛”,“痛”只不过是个跳板,他们会在滑翔的空中来一个漂亮的转体,然后准确地跌落到他们温情脉脉的生活水池。他们的最高境界是少压出点水花,这样可以赢得更多的掌声。从“无痛”时代到“炫痛”时代,我们的散文离我们的世界越来越远。《天涯》2005年第1期“读者来信”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说:“一切在苦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