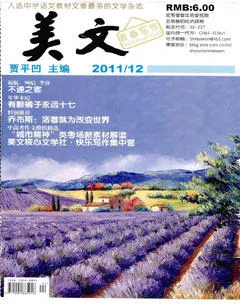杂忆录
二十四
小时家里有五六十幅画。有时在壁龛前,有时在堆房里,抑或在晾晒东西时,我曾轮流看到过。于是,我独自蹲在字画前,默然打发光阴,引为乐趣。至今与其看那像是把玩具箱翻倒了一般色彩花花搭搭的戏,不如面对着自己中意的画,心情要愉快得多。
画中最令我感兴趣的事用彩色的南画。可惜我家的藏画中南画不多。孩提时我当然不懂得画的好坏。至于好恶,只要构图上有中意的天然色彩与形状,我就高兴了。
我从未有机会增添鉴赏方面的修养,以后,我的趣味并没有起什么新变化地发展下去。所以,尽管或许有因山水之故而爱画的弊病,倒也未干过凭着名字而论画这类值得非议之事。正如大约与画同时爱上的诗一样,不论是出于何等大家之笔,也不论是何等不可一世之作,凡是不中意者,我一向不屑一顾(我把汉诗按内容一分为三,深爱一部分,大贬另一部分,对其余三分之一则谈不上喜欢还是厌恶)。
有一次,我看到一栋房子——当然是在画上——对面有座青翠的圆山,院子里种着在春光下熠熠生辉的梅花,一道小河沿着篱笆缓缓绕过,并在柴门跟前流淌。于是,我就对身旁的友人说:哪怕一回也罢。这辈子想法儿能够在这么个地方住住才好。友人端详着我那一本正经的脸,深表同情地说:你知不知道住在这样的地方有多么不方便吗?这位友人是岩手人。我这才察觉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同时又恨友人讲求实际,在我的牧歌情趣上涂了层泥。
这是二十四五年前的事了。其间,我也像那位岩手出身的友人似的渐渐不得不讲求实际了。如今,即使走下悬崖,从溪流中汲水,我也认为不如在厨房里装上自来水管更为便当。然而,南画般的心境仍不时现于梦中。尤其是自从仰卧病榻以来,心里不断地描绘着绮丽的云彩与天空。
这时小宫君寄来一张印有歌麻吕彩色版画的明信片。天长日久,这幅画的色调已失去光泽,自自然然地变得那么古雅,我简直着了迷,目不转睛地观赏着,可偶然翻过来一看,竟写着自己想托生为画中人等话,这话跟我当时的心绪毫无共同之处。于是我托旁人回复道:我最讨厌这种黏糊糊的美男子啦。我喜欢温暖的秋色,以及从其中飘逸出来的大自然之清香。然而这回小宫君本人坐到枕边对我这个病人说起陈词滥调来了:“什么大自然固然好,但必须是给人做背景的大自然才行”等等。于是我跟小宫君抬起杠来,骂他是个愣头青——病中的我就是如此眷恋大自然的。
天空晴朗得就像沉到苍穹尽底似的。目力所及的碧处,整个儿都被太阳高高地照耀着。反射下来的阳光遍布大地,我独自在其间静静地取着暖,并看到无数的红蜻蜓在眼前成群地飞着。于是在日记里写道:“天胜似人,默胜似语……恋人红蜻蜓,飞来肩上停。”
这是回到东京后的景色。因为返京后,美丽的大自然之画,一如儿时,不断地占据我的思绪。
秋露下南叽,黄花粲照颜。
欲行沿涧远,却得与云还。
二十五
妻子把嘴凑到我耳边说,孩子来了,瞧瞧他们吧。我都没有力气挪动身子,所以不曾改变姿势,仅将视线移过去,只见孩子们坐在离枕头相距约六尺的地方。
我睡着的这间八铺席屋子的壁龛,位于我的脚那一头。与邻室相间的纸隔扇被拉开了一截,我的枕头就堵在那儿。所以我是越过敞着的纸隔扇的门限看到我的孩子们的。
也许是因为隔屋而看高于头部的东西,两眼必须不自然地使劲看,所以坐在那里的孩子们的身姿显得意外地远。我勉强瞥了一眼,映在我眼帘中的那几张脸,相距那么远,与其说是见了面,毋宁说是眺望到了更为合适。我只瞥了眼孩子们的身影,一对眼珠马上就恢复了自然的角度。然而经这短短的一瞥,我便什么都看到了。
一共是三个孩子,按照十二岁、十岁、八岁的顺序被安排在屋子中央,坐成一溜儿。三个都是女小囡。为了未来的健康,兄弟姐妹五个原是奉父母之命到茅崎消夏去的,直到昨天她们还在海滨跑来跑去的呢。接到父亲危笃的通知,她们就由亲戚领着,离开沙子积得老厚的小松原,专程到修善寺来探望。
然而她们还太小,无从理解危笃意味着什么。她们记得“死”这个词儿。然而死亡的可怕与恐怖,尚未在她们那稚气的头脑里留下任何阴影。她们无从想象被死神缠住的父亲的身体今后会起怎样的变化。父亲死后会给自己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后果,这些她们当然都揣想不到。她们只不过是为了慰问病中的父亲,跟着别人搭乘火车来到父亲养病之处的。
她们脸上丝毫也没有那种由于意识到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而泛起的愁容。她们有那么一种超乎父女死别的天真烂漫的表情。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人,她们三人被并排安顿在其间特别的座位上,在严肃的气氛下,规规矩矩、装模作样地端坐着,好像是因受拘束而感到憋闷似的。
我只是吃力地瞥了她们一眼而已。我认为把这些并不理解什么叫作生病的小可怜虫大老远地特意拖到这里,让她们一本正经地坐在枕畔,倒是件残酷的事。我把妻子叫过来,吩咐她说,既然好不容易来了一趟,就领她们在这一带参观一下好了。倘若当时我曾担心这就是父女之间最后一次见面了,也许我就会更亲热一些地端详她们了。然而,我对自己的病情并不像医生和旁人那样感到危险。
孩子们立即回东京去了。约摸一星期后,她们各自写了慰问信装在一个信封里,寄到我下榻的旅店里。十二岁的笔子写的是夹杂了方块字的不规范的文言体书信:“祖母大人风雨无阻,每日拜佛百次祈愿父亲大人早日康复。闻听高田的伯母大人也到某神社进香。阿房、清美与武女等三人,每天换猫坟前的水,供上鲜花,祈愿父亲大人及早痊愈。”十岁的恒子所写的信很一般。八岁的英子全是用片假名写的。为了便于阅读,填上汉字如下:“爸爸的病好了吗?我们生活得平平安安,请放心。爸爸也不要挂念我,早点把病治好,早点回来吧。我每天上学,没请过假。还有:问妈妈好。”
我躺着从日记本中撕下一页,在上面写道:父母不在家的期间,你们要乖乖地听奶奶的话。不久有便人的时候,会给你们送些修善寺的土产去。写毕,立即叫妻子投了邮。我回东京之后,孩子们依然漫不经心地玩耍着。她们大概已经把修善寺的土产给弄坏了。她们长大后,倘若有机会读乃父此文,会作何感想呢?
伤心秋已到,呕血骨犹存;
病起期何日,夕阳还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