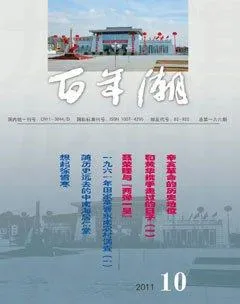从救亡走向革命
人的一生要怎样度过?青春要如何才不虚度?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学子作出了选择: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投入到救亡图存的伟大事业中。历史和实践表明,真心爱国、救国的人,无论是革命救国,还是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往往会集合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郑天翔和他的几位清华同学,正是从参加救亡运动走向革命、从青年知识分子成为职业革命者的一个例证。
2010年冬天,郑天翔同志送我一本战争年代通信集册,十分珍贵,富有感情。其中一封是1997年11月1日写给他的老同学、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的,原文部分如下:
俪生老友:
…………
“要为真理而奋斗!”我们唱过。
我回清华多次。我很怀念清华那个时代,一想到清华便想起我们曾一起高谈,以及王瑶、赵德尊诸位老友。在清华,你虽高谈,功课还是学。我那时确实患了幼稚病,对功课不重视。可以好好学一点知识,没有抓紧。时至今日,当自有悔。现在有许多事情要有好学问来解决,我已无力问之。
当年清华老友,纷纷逝世。赵德尊在黑龙江,去年丧偶,甚为悲恸。李昌在京。韦君宜重病卧床。有一位郭建恩大姐,现健在。有一位黄绍湘大姐,是社科院美国史家,现仍在旧金山,一方探亲,一方收集资料,准备写论文。给你说这些,足显怀旧之情。想到水木清华,会想叙一段青年时的故事。
那时,我觉得我们生活在无限希望之中。
…………
恰同学少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平各大中学的校园里都弥漫着愤懑的气氛。郑天翔当时正在师大附中念高中一年级,和刘玉柱、乔培新、陈忠经、李东流、王光杰(王士光,王光美的胞兄)都是同学。语文老师夏承焘给他们讲岳飞的“怒发冲冠”、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又给他们介绍“朝鲜遗民”金调元所做的诗“到底春归人未归,故乡风暴是耶非。覆巢燕子凄凉甚,更傍谁家门巷飞?”夏老师一边讲课,一边流泪,有时失声痛哭,同学们默默听讲,满座凄然。
1934年高中毕业后,郑天翔到南京就读中央大学,王士光则上了北大。1935年,两人不约而同考取清华,又分到同一间宿舍。王士光念电机,郑天翔则在文学院。虽然爱好不同,专业不同,但抗日救亡的志趣和很多同学都是一致的。
郑天翔的入党介绍人是赵德尊,赵是清化文学院的学长。赵德尊在沈阳亲历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奉命不抵抗、撤出沈阳城后,赵德尊亲见日军在沈阳街头横行霸道,奸污中国女学生,激起了他的滔天怒火和深刻思考。得知关内通车后,赵德尊便离家出走,南下流亡到北平,找到西城皮裤胡同东北流亡学生的难民收容所,这里后来改为“东北中学”,赵德尊被编入高二班。1933年,赵德尊考入清华。
十级校友郑季翘原名郑宗周,也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思索救国之路。1932年初,在太原第一师范求学的郑季翘经杜润生介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后又参加“反帝大同盟”,在太原参加并领导学生运动。1933年,因为暴露,郑季翘只好离开太原和五台老家,逃亡到北平。1934年,郑季翘用堂兄郑继侨的毕业证书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
与郑季翘同一个宿舍的赵继昌也是山西五台县人。1931年,赵继昌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市立第四中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赵继昌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爱国游行及宣传活动。1932年、1933年暑假期间,赵继昌回到山西老家与在平津读书的几位同学秘密组织“六月公社”,组织青年读书会,开办暑期学校,开展抗日爱国、反封建、反阎锡山的宣传活动。1934年,考入清华外文系、后改入经济系的赵继昌在山西老乡、清华研究院牛佩琮的介绍下,加入了“社会科学家联盟”。
郑天翔的老友赵俪生是山东安丘县人,原名赵甡, 1934年考入清华外语系。
1935年的北平,正处于日寇步步紧逼之际,国民政府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准备从华北广大地区撤退。此时的清华园里,赵德尊组建“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将王瑶、郑天翔、赵俪生、赵继昌等喜欢舞文弄墨的同学组织到了一起。王瑶、赵俪生和郑天翔三人交往密切,鲁迅及其作品、苏联文学,成了他们经常谈论和研究的内容。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左联”打算在24日开追悼会,会前邀请清华著名教授写挽联,郑天翔找了四位,皆因各种原因“碰壁而归”。同学们便决定自己写,郑天翔写的是:
树新兴文艺之教育,教育青年,教育大众;
为社会解放而战斗,战斗到底,战斗到死。
一二九运动爆发前,抗日救亡的气氛已日益浓厚。尽管一定程度上存在“左”倾关门主义,也曾受到破坏,但北平党组织在群众中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各大专院校,还有一些中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左派力量优于国民党操纵下的“老法”(法西斯)力量。清华的学生也分派,左、中、右都有,中派不过问政治,闷头学习功课;右派按月从南京励志社领取津贴,向进步教授丢鸡蛋,举手表决举两只手,即“老法”;左派是受共产党影响的一批人,热情于国家兴亡,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大部分学校中,各派力量都有体现。地下党组织在各校学生中争取领导权,1935年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简称学联),成为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的“司令部”。
从三分之一到绝大多数
彪炳史册的一二九运动,从广义上来说,包括1935年12月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多次活动:1935年12月9日与12月16日两次游行,1936年的南下宣传团、二二九反搜捕行动、三三一抬棺游行、六一三游行和一二一二游行。这些爱国运动,锻炼了清华学子,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才,可谓“云从龙,风从虎”。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子向国民党政府北平代表何应钦请愿,恳求出兵抗日。结果,不仅受到阻拦,还遭到殴打,史称“一二九游行”。这一次,参加的清华学子只有全校的1/3,即300余人,而北平城内的参加人数是3000多人。游行队伍无法进城与城内学校联合游行,只好在西直门城门外开大会,女同学陆璀手持简易大喇叭在方桌上作悲愤讲话“北平城是中国人的,我们大家进不了北平城,日本人却可以在城里自由行走”。在城内游行的学生们行进到王府井大街时,遭到军警殴打。
12月16日,北平学子再次游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日本促使成立的地方政府,史称“一二一六游行”。这次游行除少数亲国民党的同学外,几乎绝大部分都自觉参加。不参加的同学只能躲起来,以免被人看不起。全北平参加的达1万多人。“冀察政务委员会”这天没有成立,但几天后还是成立了。16日这天,城内各校学生在游行中与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军警用水龙头、皮鞭和大刀对付学生。北京大学山西籍同学李俊明挨了大刀队一刀,被同学们称之为“伟大的一刀”,意思是为爱国而受伤是光荣的。
1936年1月初,北平和天津市的学联决定,组织四个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河北农村,唤醒农民兄弟。清华在第三宣传团,1月4日出发,先后到蓝靛厂、八里庄、长辛店、良乡县城、涿州城、固安县、高碑店等地宣传。一路上,女同学们教小孩子唱抗日歌曲,赵德尊、丁则良等向老乡演讲和交谈,讲当时的形势,宣传必须起来抗日救亡。1月14日,队伍被警察统一遣送回北平。 第三团回清华后,民族抗日先锋团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很快发展到近200人。
南下宣传团回来后,清华园内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开展得更加活跃。女生宿舍发生一件事情,很好地显示了清华女生的革命觉悟。有一名姓纪的十级女生,山西大同人,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弄到一张清华进步学生的名单,正准备“揭发”之前,被一名进步女学生发现。结果引发众怒,全体静斋的女同学一起将那位同学的行李衣物从楼上扔下,把她赶出了女生宿舍。那位同学自此也再未回来。
要为真理而奋斗
1935年12月16日至1936年2月,清华罢课已经两个半月,学校当局和学生会达成一致,1936年3月初复课。2月29日,全校补考。可29日一大早,四座男生楼就被二十九军、东北军宪兵和警察包围。军警在宿舍里扑了空,但还是抓住了正准备撤离的清华党支部负责人蒋南翔、从城内做学联工作回来的姚依林、号召大家抢救被扣留同学的纠察队队长方左英。
四座男生楼的大部分同学以要去食堂吃早饭为由,由“民先”队员带头,一起涌向西校门,趁着配合二十九军和警察的东北军宪兵不积极,把扣留的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三人夺了过来。学生们不仅赶跑了特务军警,还将军警开来的10多辆汽车全部捣毁。
抓捕清华学生的计划被粉碎,再加上被捣毁军警汽车,北平当局恼羞成怒。清华大学的学校当局也坐立不安。清华当时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属于北平当局。国民政府的势力已经南撤,学校对北平当局毫无关系可以说情。学校既不能保护自己的学生,又约束不住自己的学生,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
29日上午,教务长潘光旦在旧校门台阶下,要求聚集在那里的学生不要再闹了。这引起了学生的不满,有些同学拾起地上的雪块扔向他,他说不下去,只好离开。
29日下午,梅贻琦校长在大礼堂召集全校学生讲话。同学们认为梅校长是忠厚长者,是真正的学者,对他非常尊重。赵继昌回忆,梅校长登台后,看样子心情十分沉重。他说,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很困难,同地方当局的关系不好处,希望同学们冷静一点。他说把汽车砸坏,一定会惹出事来。梅校长的讲话表明他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甚至可以理解为同学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更大事件。
学生会于是决定,派人手持木棍在学校大门口守卫。如果军警进校,就全部退到不容易发现的新体育馆,把灯关掉,使他们难以检查和登记。
29日这天晚上,大批军警蜂拥而至。一些党员、救国会和民先队的骨干夜里都没回宿舍,和绝大多数同学一起,隐藏在新体育馆内。军警最终还是找到了新体育馆,为首的警官扬言要检查,按照手中的“黑名单”捕人。在场的郑天翔、郑季翘、赵继昌、赵俪生都回忆,同学们很齐心,怕学生领袖给检查出来,先是围成一圈,不停地绕场走,不让军警和大刀队的人靠近。一个军警放了一枪,这才把队伍打散,分成几块,然后开始点名。
在点“赵继昌”名时,赵继昌应声而出,赵安全无虞。郑天翔担心黑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看到同屋的王士光(王光杰)不在,知道他离校外出,在点“王光杰”名时,就答“我是”,军警就把郑给放了。许多民先队员和地下党员都是这样做的,结果军警一个也没抓到。郑天翔出来之后,没有马上回宿舍,而是躲在一个地方观察,等军警走了后,才回到宿舍。赵继昌和郑季翘回到同住的宿舍,发现郑季翘的怀表不见了。一两天后,《清华周刊》登出全校同学在军警搜查过程中被窃去的贵重物品清单,其中多是手表金笔之类的东西。
军警当时在体育馆逐个点名,没有抓住一个人。但第二天,同学们发现军警抓走了 12位同学,关了半个多月才放。这些同学平时都不太关心国家大事,认为学校出了什么事情都与自己无关,那天晚上照常留在宿舍或图书馆看书。军警因为查遍学校都找不到几个学生,就把他们抓走了。其中一位被捕同学,因为受刺激太大,神经错乱。他们过去从不问政治,埋头读书,也从不参加游行,处于冷眼旁观的境地。这次在监狱里吃了苦头,得到了深刻教训,出狱后主动找到抗日民族先锋队,从此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这次反搜捕活动后,迫于家庭压力,再加上有些人相信“读书救国”,少数民先负责人和一些队员开始消沉。
纠正“左”倾与扩大统一战线
因为北平中学生郭清病死在狱中,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联借机抗议,仿制一口空棺材在北大三院礼堂开追悼会,并抬棺上街游行,史称“三三一抬棺游行”。因为组织不力,有“左”的倾向,参加的人越来越少,包围的军警越来越多。赵德尊、姚依林、李昌、杨学诚、王瑶、郑天翔、赵俪生等人走在队首,抬棺队伍到骑河楼就被打散。赵德尊、王瑶等几十人被抓。有一位警察是山东人,赵俪生和此人套老乡关系,并说郑天翔也是山东人,两人成功逃脱。不久,刘少奇来到北方局任书记,以“三三一游行”为典型,批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纠正“左”的倾向,为此后的统一战线指明了正确方向。
6月1dgPX1QPg5jWmzemF/4tYsw==3日,北平学生举行示威,响应5月28日天津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要求清查“海河浮尸”(日军杀死被迫为其修筑军事工程的中国工人,抛尸海河,5月间发现尸体120余具)。这次活动中,北平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清查海河浮尸”的口号,沿途的二十九军虽然阻拦,但不再殴打学生,“六一三游行”取得了成功。
此时的民先队伍发展迅猛。救亡团(前身是去南京请愿抗日的高葆琦、钱伟长等人组成的自行车队)和国民党学生组织的护校团一度与“民先”鼎足而立,此时“民先”与救亡团诚恳合作,救亡团从团员到领导,特别是自行车队的队员,很多都加入到“民先”队伍中。
12月12日,为纪念“一二九游行”一周年,支持绥远抗战,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北平学生举行大游行,这个日子与西安事变正好在同一天。这一天,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在景山公园召集学生们讲话,说了类似人要有人格、国要有国格的话。学子们听完秦德纯的讲话,步行回清华,先到体育馆洗了一个热水澡,回到宿舍已近凌晨1点,第二天一大早,宿舍里便像炸了窝,同学们欢呼着“蒋介石给抓起来了!”
西安事变发生时,蒋南翔看到中间状态的学生因为蒋介石被扣押,担心局势不稳,忧心忡忡。许多党员主张杀蒋介石,蒋南翔认为不能这样做,不让党员表态。事变解决后,有个教授带着一些学生欢呼庆祝蒋介石回南京,右派学生烧毁左派学生的《清华周刊》,左派学生与他们打了一架。
西安事变后,中共有意识地加大了与国民党一致抗日、抓统一战线的力度。蒋南翔等学生领袖指定几个人与国民党右派学生“献剑团”接触,并让当时的学生自治会主席王达仁和“民先队”秘书熊向晖每隔一段时间就到中山公园今雨轩与国民党右派学生聚餐,做工作。当时徐高阮(徐芸书)等在《国闻周报》发表对中共不利的言论,蒋南翔一方面和他们论战,一方面也认为救亡不能放弃读书,老罢课不行,号召大家回图书馆、回课堂,团结教授们。
1937年上半年,清华左派学生与右派学生聚会多次,团结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绝大多数学子都加入到救亡运动中。这一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中间同学开始持赞成态度,右派学生出现分化,左派力量占压倒性优势。
加入党组织
很多清华学子都是将一腔爱国热情在各次斗争中经受考验,从而产生了参加组织的要求;又在组织中经受考验,逐渐成长为组织中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但也有一辈子与党同行、却没有加入组织的人,譬如赵俪生。蒋南翔曾到赵的宿舍启发他入党,说:“你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赵俪生回答:我读列宁的传记,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来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地批评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马尔托夫被列入了黑名单,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赶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我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赵俪生20岁时的这一番话为他的一生留下了注脚:一方面,为了抗日,为了推翻蒋介石统治,他曾在西安等地为地下党提供情报8年,一生以革命同路人自居;另一方面,他探索真理,一生笔耕不辍,桃李满天下,成为深受学生爱戴的历史学家。
没有立即入党的还有赵继昌。1936年暑假期间,清华党支部书记赵德尊征求赵继昌意见,问他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赵继昌表示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做一名党员,暂不考虑,但救亡活动坚决进行。赵继昌在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也曾担心毕业后的工作问题,努力于功课学业,甚至还考虑过考取公费留洋。赵继昌在回忆录中写道:直至抗战开始,我只是一个党的同情分子,同路人,或者说是一个基本群众。党员同志把我当做自己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赵继昌辗转各地,后决定寻找党组织。此后曾在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贸易部、中财委外贸组、国家科委、国务院财贸小组等担任领导职务。
没有立即入党的活跃分子毕竟不多。在一二九运动中活跃的绝大多数同学,在蒋南翔、赵德尊、杨学诚等人的引导下,无论是通过清华党支部,还是中共北平学委,都陆续入党。1936年冬,赵德尊介绍郑天翔加入中国共产党,赵对郑说,我是北平学委秘书处负责人,你就在学委秘书处工作,任务是印刷和保管。你不编入清华支部,由我单线领导。随后,赵拿出一个绿色帆布箱子,里面是油印机和文件。赵指着两包文件对郑说,这一包你可以看,这一包你不能看。郑天翔于是把箱子带回宿舍。没过多久的一个星期六晚上,赵德尊来到郑天翔的宿舍,自费出版北平学委的刊物《生活通讯》。赵德尊挂起大床单,把窗子遮住,然后拿出纸笔就干起来。赵德尊刻好后,郑天翔印。刊物也就是一张蜡纸,大致半月一期。印出来后叠成小册子,赵德尊带走。
1937年8月上旬,郑天翔从城内回到清华,清华园此时已经看不到多少人。宿舍楼的工友递给郑天翔一盒火柴,说,把你那些东西烧掉吧,锅炉在地下室。郑天翔把保管的文件拿到地下室,付之一炬。原来,郑天翔的那点“秘密”工作,根本没有瞒过工友。郑天翔同宿舍的王士光,其实也知道,他们相互信任,王士光多方为郑提供方便。王士光后来去天津搞地下情报工作,在晋冀鲁豫军区培训无线电工程机务人员,成为太行山上的电信大王,成为新中国电信工业的开路先锋,电子工业的第一代拓荒者和领导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清华九级(1933年入学)至十二级(1936年入学)约有900多名学子,其中“民先”队员183人,党员40多人。在铁马冰河的抗战中,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成为新中国领导各方面建设事业的高级干部。
郑天翔和他的几位清华同学,在大动荡时代的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他们的人生轨迹证明:真心爱国的人,真心追求真理的人,往往都会集合到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感谢郑易生、郑京生为本文提供照片及素材)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