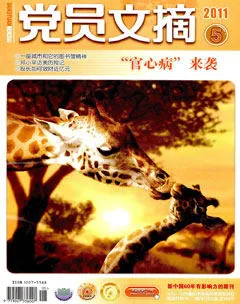基层官员悲喜录
外表风光、衣食无忧的公务员们内心到底有多纠结,恐怕除了他们自己,只有他们的心理咨询顾问知道。他们不但要面对普通人生活中所必然经历的种种烦恼,也要承受这份职业所带来的压力。
一位纪检干部的烦恼
□ 孙晓青
今年43岁的王芳,短发,面容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话语干净利落,十分符合她省纪检副厅级干部的硬朗形象。也许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她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大人物”,可当她面对自己的心理咨询师时,首先却是讲述了一段让她觉得至今难以平复的耻辱经历。
哥哥的孩子当兵,八个人选中有六个名额。哥哥打听到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是某公安局长,只是给征兵办打了个电话就很顺利地要了一个名额。为此,哥哥特地找到王芳,希望她也能为亲侄子“疏通”一下。这件事让王芳很为难。早前自己孩子念书想要转到一所重点中学,如果是普通官员,一通电话就应该能够办成,可她偏偏是纪检干部,当时有人还笑她说,就算是送钱,也没人敢收纪检干部的钱。后来没办法,她托了好几个亲戚帮忙,并以别人的名义才交了“赞助费”,办成孩子转学的事情。
这一次在哥哥的再三请求下,王芳还是硬着头皮打了一个电话。当对方听到她是纪检部门的人时,严肃地说:“请纪检部门盖个章、出个证明,这孩子我们就收了。”王芳觉得,这摆明了就是在为难她。这种被刁难和排挤的情况她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王芳有一次到市里开会,会前看到其他人在聊买房子的事,她本想笑着也搭个话,结果对方却戒备地说了句:“哎呀,我们哪有钱买房啊,就是随便说说的。”她知道别人顾忌她的身份,总觉得她想要刺探什么。
作为纪检干部,王芳不能像其他官员那样能轻易地为家人谋些方便,也并不像普通人羡慕的那样风光。虽然王芳有过难过,有过不甘心,也有很大的压力,但这些她觉得自己都能排解,“遇到这些事情,和同事发发牢骚,自己大哭一场,或在心里骂一通也就过去了”。
真正让王芳感到压力的还是来自纪检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考验。这份工作并不是朝九晚五的正常上下班,一旦有案子,为了保证能抢到有效办案的时间,大家都要没日没夜地工作。此前王芳接到了一个举报,查处一个有贪污受贿嫌疑的商务局干部。她带着手下的工作人员持续加班二十多天,终于掌握了这个人的确凿证据,结果却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基于各种需要,这个人暂时不能动。王芳了解到这个人是一个招商引资大项目的关键人物,为了维护稳定,暂时还不能查办。后来有一次王芳见到这个人,看到对方嬉笑得意的脸,王芳觉得很恶心,也很不甘心。
这些心酸和压力在她看来只有同行才能理解。
谁在压迫他们的神经
□ 田鹏 张然
政法系统公务员的心理隐患,在整个官员群体中属于最明显的。
一项针对天津、甘肃等地公务员心理健康调查显示,政法系统人员罹患某些心理疾病的比例高于一般公务员。在去年被公开报道的九例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中,至少四名死亡官员属于政法系统。
谈到政法系统官员的压力,北京一基层法院执行局局长列举了两大压力——社会压力和案件压力。
在社会压力方面,比如说,申请人权利未能实现时,就到处上访告状;而被执行人则有可能对执行依据(判决)不服,对其采取强制执行,就会采取过激行为。很多执行法官别无所求,只求“案子别炸”。
另外,近些年需要执行的案件数量飙升,人员配备却没有增加,这就使得工作压力加大,加班成为常态。执行中,各个部门的协调也远未完善。
沈阳市某区法院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涉法涉诉上访问题把我们基层法院搞得没有办法招架,每年一遇重大活动,全院干警都得动员起来,几人一组对重点上访人24小时“死看死守”,我们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吃喝也全在车上。如果被控人员突然一转弯没影了,我们就得赶紧四处撒开去找。有同志开玩笑说,法官都成“特工”了。
这位院长说,这些本不是法院的正常工作,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期,基层法院一直在做大量信访工作,有时连审判工作也得放下,哪有这些精力呀?最让人愁的是现在我手里还有十几个有关部门交办的上访案件,限期息访,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夹心层”的困惑
□ 孙晓青
47岁的陈述在机关兢兢业业地干了十几年,一年前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这个部门的主任,正处级干部,手底下管着十几个人。陈述心里很高兴,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地干点事业。
一年之后,他心灰意冷,感觉自己比以前还累,经常焦虑得睡不着觉。陈述手下的十几个人很多都是80后,学历和自身素质都不差,但在实际工作中,陈述放手让他们干的工作最后老是差那么一点,让他们修改还得费半天劲解释,费力不说,他们还不高兴。于是陈述总是觉得不如自己干,慢慢地,加班成了陈述的家常便饭。
家里人为此很有意见,妻子总是埋怨他不顾家。家里的不满意让陈述感到很烦。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辛苦付出不但没得到单位同事们的夸赞,反而遭到了领导的非议。事实上,领导觉得陈述这个部门的员工总是成长不起来,依赖性太强,看不出谁能发展成为业务骨干,长此以往对团队的发展会很不利。而陈述的这些80后手下们也不买他的账,觉得没有得到重用,看不到成长的希望。
如何平衡两边的关系让陈述格外纠结。一想到未来,更让他陷入深深的焦虑中。在陈述看来,以前升职快一方面是自己努力、运气好,另一方面是因为周围没有更多的竞争对手。现如今,升职越来越困难,既要“围着领导转”,又要工作不出错,而且他的人际关系不如其他同级别的干部,所以对未来发展前景感到十分灰心。
“三陪”书记“走钢丝绳”
□ 林 嵬刘 健周立权
河南一位县委书记用一幅“双三角型对顶图”显示他所理解的县委书记所处的环境:一个倒置的大三角形压着一个正放的小三角形,形成倒压对顶之势。在这位县委书记看来,基层官员总是处于上压下顶之间,执政压力大、困扰多。
作为群众眼中坐拥权力、风光无限的县委书记,他们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湖南省衡东县委书记刘运定、河北省成安县委书记张臣良这样描述高度紧张状态:“县长觉不够睡,书记则睡不着觉。我天天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可一听到下雨声就又惊醒了。”“当县委书记不得病的人不多,这就像在战场上负伤一样,很正常。”
责任大、压力大的另一面是迎来送往的接待赶场。县委书记整天陪着上级领导检查工作、陪着汇报工作、陪着喝酒吃饭,常常戏称自己是“三陪”书记。
“为了应付来自中央、省、市各个部门的领导和各种名目的检查评比,我马不停蹄奔走于一个又一个晚宴,陪上级领导喝酒吃饭,一个晚上竟然陪了八顿饭,喝的酒就数不清多少了……”一位县委书记苦恼地说。
“三陪”还仅仅是一个“累”字,“走钢丝绳”则是一个“险”字。在一些县委书记眼中,“踩红线而不越线”的特色非常鲜明。西部某贫困县的县委书记讲述:“两年前,县城控制规划不到六平方公里,还不如沿海一个乡镇,这怎么发展?后来采取了很多变通的办法,才搞到现在的三十多平方公里,许多项目都是边审批边开工。踩着红线搞发展让我每时每刻心惊胆战。”
县委书记还常常处于矛盾的中心,可谓“潜规则”无处不在,风险无处不存。
“人事漩涡”——西部一位县委书记说:“全县几百名科级干部盯着换届才能空出来的几个副县级岗位,如果从上面‘空降’一人,就可能会挫伤部分干部的积极性。找不到更多的调控手段,会引发一些干部不满情绪。”于是,很多县委书记在自己任期内不敢调整干部,怕把自己置于火山口上。
“权力陷阱”——由于县委书记“位高权重”,有很多人盯着你、仰慕你,当然别有用心的人会“研究”你的秉性爱好、人际交往及朋友圈和亲戚圈。如果这些都被摸得透透的,稍有不慎就会掉进“陷阱”。
“打招呼困境”——湖南一位县委书记说:“最怕上级领导‘打招呼’,80%的人打招呼是见不得阳光的事。而最头疼的是有的领导干部,美其名曰‘下来检查指导工作’,却交代一些违规的事情要办。不做吧,得罪了上级,一做,就会引起群众非议。”
置身于激流漩涡中,县委书记既要抵挡金钱美色的诱惑,又要一身正气、坚持正义、谨防“陷阱”,这给县委书记的心理素质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同时也对如何更好地营造风清气正、科学民主的政治环境提出了挑战。
(综合摘编自《半月谈》、《小康》、《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