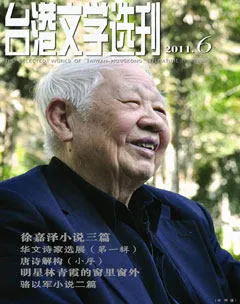秘鲁男孩
童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童年。它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个金色的梦!
但是,对世界上千千万万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童年只是一场挥之不去的黑色梦魇。据联合国发展署的最新资料,全球人口中,有四分之一生活于赤贫状况,十三亿人口的日花费低于一美元;而贫困国家的儿童,境遇更加凄惨。前些日子,我有机会去南美洲的秘鲁走一回,那贫瘠的土地,栖息着两千二百万人口,光首都利马就拥挤着近七百万,其中一百万是盲流。在这动荡的国度,我接触到许多秘鲁孩子,有在干燥的砂土上踢足球的,有在小巷里玩盖房子游戏的。不过,无论在大街小巷,在城市村庄,更见到众多的小孩,他们的童年生活,留给人们的不是灿烂的笑颜,不是悦耳的歌声,而是辛酸的日子夹杂着苦涩的泪水。我亲眼看到不少秘鲁孩子,或衣着褴褛,背着比他们更小的弟妹沿街乞讨;或手持旅游纪念品,紧围着游客卖力兜售;或提着一个小木箱,蹲在旅馆门口靠给人擦皮鞋度日;或挤在经常塞车的公路上,见缝插针,不顾危险地擦洗过往的车辆。他们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过早地被卷入了成人的生活领域,过早地被剥夺了快乐的童年……
那一天,我们参观完秘鲁的世界奇迹——失落在丛山峻岭中的古城马丘比丘,正搭乘旅游巴士下山,在返回火车站的行程中,一幕意想不到的情景出现在大家的眼前。记得上午乘巴士上山时,人们曾被蜿蜒陡峭的山路吓得惊恐万状,生怕车轮溜出狭窄的路面,人车就要从悬崖峭壁滚落摔成肉饼。因此,大家对下山早已有了心理警戒,准备再到鬼门关去逛一圈。
大型巴士开动了,车厢内鸦雀无声。峰回路转,雾岚缭绕。人们随着脱缰的车子东倒西歪。当巴士转过两个弯道,突然,一个身穿黄背心、约摸十岁左右的小男孩,正站在路口挥动着小手,向巴士大声地喊叫后立即消失。意图很清楚:他是要引人注意。然而,游客们似乎忽略了他的存在。因为秘鲁的孩子实在太多了,再说,车子早把大家的兴致摇晃得消失殆尽。
巴士仍在重峦叠嶂中绕来绕去,在接下来的转弯处,都会准时地出现一个穿黄背心的小男孩,大喊大叫地向游客招手致意后顷刻消失。这回,事情开始引起车内人们的注意:怎么回事?该不是同一个孩子吧?有些人怀疑,因为不可能是同一个孩子,如果是,他怎么会跑得如此之快?何况根本没有山路而又荆棘丛生,真是匪夷所思!当巴士又滑到下一个弯处时,嘿!又是那个身穿黄背心的小男孩,依旧像幽灵一样准时地出现,摇着小手,大喊大叫,然后消失。奇怪!于是,这个秘鲁孩子的举动不约而同地引起了全车人极大的关注。
接着,多变的高原天气开始飘洒着细雨。巴士仍在下坡的路上飞快地滑落,雨点轻吻着玻璃车窗。正当人们对下一个弯口纷纷猜测,期盼那个小孩会按时出现时,大家屏住呼吸透过车窗一看,真绝!那个黄色的身影果然已经等在那儿。大家连忙将玻璃窗推开,这下,人们才瞪大双眼将那孩子的形象嵌入眼底:就那么一个小不点,黄色背心,双颊赭红,满脸淘气,一付如假包换的秘鲁小孩的模样。由于过快地奔跑,他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雨水混着汗水,从头上往下淌。看了,真叫人又惊奇又心疼。车上游客的心情从疑惑好奇转为同情怜悯之余,对小男孩的举动还是感到不可思议。这时,全车人对这个小孩将出现在下一个弯处已不存任何怀疑。这不?往后,他与巴士几乎同时出现在好几个拐弯的路口,好像与车配合得天衣无缝,分秒不差,精彩!好精彩的一幕!
巴士经历了一场颠簸,终于在山脚的火车站旁停下,就在司机打开车门的刹那,钻上来一个小男孩,身穿黄背心。仔细一瞧,这不就是刚才与巴士赛跑的秘鲁孩子吗?车厢内顿时响起一片掌声与赞扬声,老外们个个欢欣雀跃,纷纷拍照的拍照,录相的录相,忙得不亦乐乎。只见他汗水渗湿了衣襟,满脸稚气,一双粗糙的小手捧着一个色彩鲜艳、地道秘鲁式样的小布包,沿着车座中的过道,呈现在众人面前。直到此时,游客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秘鲁孩子,在人们惊奇、同情、怜悯与钦佩之余,用他的脚力、汗水与惊人的速度,换取人们的施舍……
面对这样一个既懂事又可怜的秘鲁孩子,车厢内一片寂然。阵雨初歇,天色黯然。游客们感慨万千,纷纷解囊,一个个从钱包中掏出美元或是秘鲁索尔,郑重地放进那个虽还鲜艳却沾着泥污与血迹的小布包。小男孩的脸上掠过一丝天真而又稍许呆滞的目光,没有童稚的笑声,没有灿烂的笑容,只有令人动心的感激和谢意。
在回程的火车上,导游向我们透露了内情:原来由于生活贫困,大人们想出这种利用小孩来挣钱的生财之道。他们有一班人马,专门到山里搜罗八岁至十一岁的穷苦小男孩,进行训练,找一条从山上通往山脚的捷径,让孩子玩命地飞奔而下,一定得一站不漏地赶在巴士之前,抵达事先选好的转弯处向游客招手呼喊,利用外国游客的同情心来敛财。而司机及有关机构都从中配合,抽取红利。每个小男孩追逐指定的游览巴士,每天大约要往返冲刺三趟,这项“与巴士赛跑”的运动,便成了他们童年谋生的手段。超过了十一岁、久经沙场的小男孩立即“退休”,换上新的更小的一批。因为年纪越小的孩童就越能博得老外的好奇与同情,也就越容易从游客那儿兜得更多的施舍。
听完,我们不由询问导游一连串疑窦:是谁在统领这帮秘鲁孩子?有多少小孩靠此谋生?这些本该坐在学校的课堂里的适龄孩子,为什么要去卖这种苦力?这些靠出卖苦力的孩子一天能挣到多少钞票?他们本人能得到多少报酬?政府有关部门对此采取什么态度?
导游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但从他忧伤的脸上,人们读到了答案。久久,他只是用低沉的声调告诉大家:这里的许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加入这支队伍,不少小孩正在排队等待,眼巴巴地期望那些年满十一岁的同伴,赶快“退休”,以便自己能早日穿上黄背心接替他们,从事这项与巴士赛跑的职业。哦,身穿黄背心的秘鲁孩子!哦,滴着血汗的童年!
此时,我遥望窗外,火车正吃力地喘着粗气,爬上一个山坡。两道平行线伸向远方。路途迢迢,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