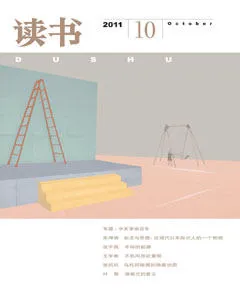在最后一节车厢里
一九八一年暮春,我从《文汇月刊》上看到赤壁籍军队诗人叶文福的诗《快生啊,大海》。诗以产妇临产为喻,焦灼地呼唤一个全新时代的诞生,一如他的惯常风格,我很喜欢。接着,又从《十月》上,读到他的诗三首:《路灯》、《我是飞蛾》、《天鹅之死》,诗之尖锐,即使今天也不多见。
从这时开始,赋闲的诗人时常返乡,回到蒲圻县文工团——后来是工人俱乐部的家。我和饶庆年、梁必文、叶向阳、欧阳明跟着诗人学诗,成为他在家乡最早的一批学生,他戏称五人为“元老院”。若干年后,我写过一篇小文《落叶》,记述这段时间的一些事情。
当时我们几个人里,饶庆年、梁必文擅长农村题材、现实主义风格,特别是饶的作品,乡土气息更浓郁,颇受好评。因为生活、阅历、气质、风格等原因,我更喜欢叶向阳的诗。那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期。国门初开,各种风格的中外作品纷至沓来,其中也包括外国现代派,他的诗就带有这样的味道,另外,我们住得也不远,走得较近。
那时,我们都住在蒲圻城的北门、水西门。我家和他家仅一墙之隔,都坐落在清代的青石古城墙边,看得见城墙下的陆水河、河对面的青山古渡。
一天,我从叶向阳家发现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其中收有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流派作品。我将书借了回来。上有编者袁可嘉先生的长篇前言,我花了整整几天,启用了一个最好的笔记本,将它抄了下来。当时,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少有的“豪举”,那时对文学的虔诚可见一斑。因为这篇序文,我从此对袁深具好感。
一本当时的购书登记本中,留下了诗友交往的一鳞半爪记录:向梁必文借《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将《诗刊》一九八一年第八期借给姚同欢,《文汇月刊》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借给叶向阳,徐鲁从阳新寄赠《金竹》创刊号。还有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将自己刚买到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留在叶文福老师家。为什么要留给他,现在已不可确考,是否潜意识里觉得他的诗还不够现代,需要再往前走一步?
冬日的长江上,宜昌开往武汉的“东方红四十六号”客轮犁开冰冷的江水。汽笛时而雄浑有力地低鸣。灰蒙蒙的天空,浑黄的江水,土黄的堤岸,收割过的萧瑟原野,辽阔的江汉平原似乎在缓缓转动。
客舱里,躺在上铺,我在读刚刚在宜昌淘买到的一本小书: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未列入名册》。这部中篇小说讲述的是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之初,斯摩棱斯克要塞的坚守者英勇悲壮的故事。看完最后一页,我猛地拉过毯子,蒙住头,热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久久不能止息,身体微微抽动。
那时,狂热地喜欢外国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
那时我读到蒲宁的《轻轻的呼吸》(一译《轻微的气息》),立刻就喜欢上了蒲宁。有人说蒲宁胜过另一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也许是这样吧,但我还是更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在我看来,他的熠熠闪光的《金蔷薇》是不朽的。虽然我也知道,喜欢的有时并不见得就是最好的,而是当时当地你所能接受到的——接受是一件偶然的事。
关于巴乌斯托夫斯基,还有故事。那几年,我每年都订阅上海《书讯》报,从中得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北方纪事》,立即汇款购买。不久,款被退回来,言书已售罄。我不甘心,又寄,又退。再寄,再退。如是这般者四。另一次,在县新华书店发现新到了《金蔷薇》,立即买下一本。二十几天后又买一本。次年初夏,那批《金蔷薇》还有,我又买下第三本,因为已有些破旧,这回仅花了两毛钱,为原价的三分之一。这样,连同借来的一本,我手头共有四本《金蔷薇》。
现在已难理解当时为何有着如此的狂热。那本旧的购书登记本上记载: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收到从商务印书馆邮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剑与犁——泰勒回忆录》和罗尔斯《政治正义论》一至三卷。两天后,收到从战士出版社邮购的《西洋世界军事史》一至三卷(钮先钟译)、《苏联武装力量》、《战争初期》,“二战”时期德军两名将领的回忆录:曼施坦因《失去的胜利》、古德里安《闪击英雄》以及《坦克战》。一个月后的七月三十日,收到从商务印书馆邮购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政府论》上卷、《社会契约论》、《人类理解研究》、《人的使命》、《麦克米伦回忆录》第二卷。当天,汇款世界知识出版社,邮购《第三帝国的兴亡》、《外交风云录》及其续篇、戴高乐《战争回忆录》、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第四帝国的崛起》。同日,汇款华东师大出版社,邮购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汇款天津人民出版社,购《彼得大帝》。九月二十三日,汇款上海文艺出版社,购《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外国文学作品选》及《一九八一年全国获奖短篇小说集》……
这一年的九月底十月初,有一次故乡洪湖之行。在新堤县新华书店,买到《戴望舒译诗集》——直到二十多年后,通过诗人、译家黄灿然的精微解读,我才真正领会、发现戴译之美。接着溯流而上岳阳,买到《世界文学三十年优秀作品选》、《世界中篇名作选》、外国中篇小说丛刊之《挤奶女的罗曼史》。
这年十二月一日,去信人民文学出版社,寻购《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迦尔洵小说集》、《荒诞派戏剧选》。十天后收到该社复信,告《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目前还有……当天,汇款购买该书,以及《梅特林克戏剧选》、《安德烈耶夫小说选》。在这前后,挂号去信上海文艺出版社金子信先生,其中夹寄现金,购他责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三册,《外国文学作品提要》第一至三册,《外国短篇小说》上、中、下册等。
那时就是这样狂热地买呀,读呀,写呀……
十月在岳阳,还买到译文丛刊之《在最后一节车厢里》,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那时也是在一个时代的“最后一节车厢里”。
那一年,我还订了《文汇月刊》——当时,它特有的文化气息是那么使我着迷,以及《书林》、《文学报》、《外国文学报道》、《书讯》、《社科新书目》。有心人会注意到,六种报刊中,就有五种是来自上海,可见那时上海在我的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书林》有点类似甚至过于曾经的《读书》。
一九八三年底,在购书登记本中,我做了一个简要的统计:当年购书总金额二百一十元,购书总数二百八十册,购书金额相当于我整整六个月的工资。购书登记本透露了我当时的精神生活线索,堪称一个年代的纪念册。
登记本还记载,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在江汉平原一个空旷无人的电排站里,桌上凌乱的旧报纸中,发现一份《文汇报》,上面刊有《南珊的哲学》。两年前的一九八一年初,从《十月》上,我读到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一种冰凉的奇异感觉如水沁入了我,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一种幻灭感。我以为礼平绝对是当时我国最好的作家之一,然而他在瞬间爆发耀眼的光芒后就消失了,如一颗流星。那时候的《十月》等刊物推出了多少名作啊。那时候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也是名家名作如云。还记得一九七九年一个夏夜,在离赤壁古战场不远的一所乡村学校里,就着一盏悬吊的白炽灯泡昏黄的光,我从《光明日报》副刊上读到王蒙奇异的《夜的眼》。
一九八四年是以旅行开始的,结果,这一年我都是人在旅途。一月二月之交,到宜昌过年,乘“东方红一二三号”轮上溯三峡,到了四川奉节、巫山。五月,赴游湖南长沙、韶山、湘潭、岳阳。七月,参加华中某著名工学院考试到文赤壁黄冈。冬天,因改稿旅居武汉。旅途期间,仍然买书不断,继续漂荡在精神的旅途。
我时常想韦尔斯的话,大意是:一个人要有闲暇的时间、闲适的心情才会弄文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文学热,就是这样产生的?
那时,我国人民似乎有着闲适的心情。我国社会也并不喻于利,普遍地还是喻于义:主义,道义,义理,不怎么计较功利。我不知道,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好,还是不好?
也许,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狂热迷恋的时期。也许,人一生应该有这么几次不计成败、不计成本投入一件事的锐气勇气。我又想,经过这样一次“热恋”,这个人还会是原来的人吗?他与周围的人在内心有没有区别?
今天,有人说“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些美好年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前期,应该就是这样的年代。它尚不富裕,更谈不上奢华,而是简朴、平静,却让人看得见希望,听得见幸福来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