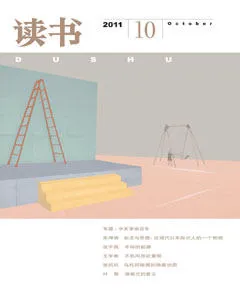范用与罗莎的画
我的父亲、母亲与范用叔叔是相交近七十年的三联老友。可以说,范叔叔是看着我长大,而我是看着范叔叔变老的。
八十年代,我常在文化界采访组稿,与范叔叔的共同话题渐渐多了起来。每次去北京朝内大街一六六号办事,我都要到五二○号房间去拜望他。碰到《读书》的“五朵金花”在那喝咖啡,就和她们共享共乐。有段时间,文坛风云变幻,大家说话都很谨慎,而范叔叔却仍在口无遮掩地针砭时弊,为一些文友遭遇的不公愤愤不平。我总是忙着把办公室的门关紧,说:“小声点!小声点!”他总是摆摆手说:“没关系,不要紧!”有次,范叔叔考我:“什么叫自由化?”我答:“越来越讲不清了。”一向思维跳跃的他,突然问我罗莎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了?
罗莎是妈妈罗萍的小妹,罗家六兄妹中最开朗活泼,也最有艺术气质的人。她崇尚自由,个性独立。为表示对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敬仰,她独自把我外公为她起的名废了,改名叫“罗莎”。抗战后期在大后方,她先在桂林美专学画,一九四四年又跟着演剧队撤退到重庆,经我妈介绍,在读书出版社义务当了五个月的练习生。范叔叔说,他印象最深的是罗莎的笑。她大笑时会旁若无人地前后翻仰,仿佛全部精力都投入在笑的声音和姿态中。别人有时被惊呆,她自己则非常享受,非常陶醉。在出版社,罗莎因为字写得漂亮,又会画,常给范用当下手,帮他搞封面设计,替他跑印刷厂,跟他学捆扎邮包。自从罗莎去成都艺专学西画之后,范用就再也没见过她。
崇尚自由、个性独立的罗莎在“文革”中自杀了。一九六六年夏,在全国愈演愈烈的大批判声浪中,邓拓、傅雷等著名文人义不受辱,含恨自尽。罗莎并不是什么名人,连党员也不是。她当时只是单位办公室的秘书。因为文笔好一些,受到重用,被列为单位“三家村”成员。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罗莎的肆意中伤,激起了她的愤怒。她“不识时务”,贴出大字报反击,引起轩然大波。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罗莎在批斗大会前服“敌敌畏”自尽了。
我妈妈从不愿谈这段伤心往事,所以从不向范用提起罗莎。
范叔叔听我讲述后神情沉重,不断地重复说:“我很难过。太可惜了,真是太可惜了!”过了两天,范叔叔打电话叫我去他家。在他卧室墙上,新挂出一个极简朴的木质镜框,框中镶着一张铅笔素描,是罗曼·罗兰的头像。图纸已泛出微黄,看来有些年月了。范叔叔指着它说:“喏,罗莎送我的,挂出来纪念她。”这张画经过战争的烽火、政治的浩劫,竟然在范叔叔手中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真令我惊讶和感动!它应该是罗家仅存的罗莎早年遗画了。我很想替妈妈讨要,但又不敢。上学时,我曾莽撞地向范叔叔讨要《浮士德百卅图》(群益初版)的精装珍本,因为那是一九四七年我父亲从头到尾负责印出的。精装本是布面的,只印了一百本,父亲手头没有存书,所以我很想讨要。那时,我不真正懂书,不了解范叔叔“爱书如命”,更不知道范叔叔正逢出书不顺,脾气很大。我的讨要遭到我认为非常粗暴的拒绝。之后,他有半年之久没有搭理我。我为此还委屈地哭了一场。那次的教训,我是刻骨铭心的。这次,我只默默盯着小姨的画,依依不舍地看呀,看呀,希望范叔叔从我的神情明白我的内心,就等他说一声:“拿走吧。”
但是,我一直没有等到,令我伤心失望。
事后向妈妈说起此事时,妈妈说:“能被你范叔叔收藏至今的每件东西,与书都有一段值得记忆的故事。”她说我们应当为此感到欣慰。
罗莎这幅画究竟与书有什么相关故事呢?我一直想问问范叔叔。二○○○年,我退休回上海协助妈妈整理罗家家史,并把她写的《童年记忆》一章寄给范叔叔。一天,邮局送来一个挂号邮件,像杂志一样大小,薄薄的,硬硬的,包装得很仔细、严实。拆开一看,两层硬纸板中夹的竟是那幅我想得到的罗曼·罗兰头像!范叔叔还附了一张给我的便笺,说明罗莎在画像右下写的英文名字,和“作于一九四四年”。妈妈和罗莎诀别了近三十五年,终于在她生前见到了妹妹珍贵的遗画。罗家几代人,都感激范叔叔将它完好保存了五十六年。
关于这幅画背后的故事,我原本以为与爱情有关。但那时范叔叔已有了儿子范里,罗莎也有了恋人,想想又不大可能。在得知真相后,我为自己有过的猜测感到羞愧。原来,范叔叔年轻时是罗曼·罗兰的崇拜者,这位法国大作家具有的音乐修养,令酷爱音乐的范叔叔钦佩万分。他不但欣赏罗曼·罗兰书中关于音乐的描述,而且认为他的文字节奏也很具乐感。他能熟背罗曼·罗兰的不少名句,如:“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有一天,我将为新的战斗而再生。”他一直热衷于搜集罗曼·罗兰著作的中译本。在桂林时,起先他手头只有陈占元译的一本《贝多芬传》,后来诗人洪遒送了他一本傅雷译的《米开朗基罗传》。他喜爱傅雷的译文,发疯似地从头至尾抄了一遍。当时,洪遒对《约翰·克利斯朵夫》非常着迷,说这本书好像一部宏大的交响乐,有序曲,有尾声,每一卷都像不同旋律的乐章。写得真是美极了!这感染了范叔叔,他千方百计从桂林、衡阳、曲江、南昌四地的商务印书馆,好不容易凑齐了一套四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傅雷的译本。范叔叔爱不释手,读得如醉如痴。他早已与罗曼·罗兰反战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着共鸣。读罗曼·罗兰的书,他更坚定地认为,人必须具有不屈不挠、永不气馁的个性和意志,方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一九四四年夏秋之交,日寇大举进攻我国西南。在书业湘桂大撤退时,范叔叔将店里存书打了三十多个包,从桂林辗转运到重庆。自己则随身带着一直珍藏的一批史料和书,包括罗曼·罗兰的这几本,还有周立波送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冯至的《十四行诗》、梁宗岱的《屈原》、纪德的《新的粮食》等书,以及聂耳日记的手抄稿。一路躲避战火,撤退到重庆。在贵阳中转时,书店同仁已疲惫不堪,身无分文,饿得吃不上饭。有人劝范用把书卖了,他死也不肯,说:“别的可以不要,心爱的书不能丢!”我父亲卖掉一条西装裤,大家这才吃上一餐鸭头面。“真是香得不得了啊!”——多少年后,范叔叔已是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并以“美食家”远近闻名,但谈起贵阳这顿“美餐”,还是念念不忘呢。
一九四四年真是令人悲喜交加的一年!中国北方抗日战场开始了局部反攻,但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的溃败,又一次导致大片国土沦丧。日军兵锋所指,重庆为之震动。国统区特务政治愈加黑暗,韬奋先生受迫害在流亡生活中病逝;但同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初现。罗曼·罗兰在见到自己祖国获得解放后去世了。罗曼·罗兰三十年代出任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二战”时在病中仍坚持争取民主、反对侵略战争,在中国文化人中享有很高威望。重庆文艺青年掀起了一股“罗曼·罗兰热”。范叔叔手中的那几本藏书,成了大家传阅的抢手货。无奈,人多书少,只好依次排队。罗莎当时就在店里当练习生,她整天缠着范用,求着让她先看。范用说,她是学美术的,就先看《米开朗基罗传》吧。谁知罗莎说她早读过好几遍了,非要看《约翰·克利斯朵夫》,并说:“我是有报酬的,可以预付!”罗莎亮出一幅罗曼·罗兰的素描头像,在范用眼前晃了几晃。喜好收藏的范用马上向她讨要。正好,诗人何其芳借走的书刚还了回来,范用就此与罗莎达成了口头交换协议。罗莎还书时,为范用背诵了其中她最喜欢的一段文字,还展示了据此段文字创作的一幅彩色写意画。画面上,黝黑的危崖后面,正在冉冉升起的太阳已将天空染成了金色。罗莎没有写实画出精疲力竭的克利斯朵夫,和他带着同达彼岸的那个沉重的孩子,只是指着自己的画,自问自答地说:“‘孩子,你是谁呀?’——‘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不用说,范用自然很欣赏,马上又向罗莎讨要。可是,罗莎这次说什么也舍不得送范用了。
如果罗莎当年将这画送给了范叔叔,后来它就不会在战乱中丢失了。其实,范叔叔手头与傅雷、罗曼·罗兰有关的所有资料全都完整保存了下来,罗莎的画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何其芳借书的信,罗曼·罗兰致隐渔函等等。还有,他抗战胜利前在桂林和重庆精心剪辑了一本有关资料,戈宝权根据他提供的这批资料,写了一篇《罗曼·罗兰生平及其著作和思想》,发表此文的那期《群众》周刊,他也一直保存至今。范叔叔说,与罗莎这幅画有关的文化背景,他都写在关于傅雷和戈宝权的文章中了。只是,当时没有篇幅写罗莎,他想以后单列一个题目,得先打好腹稿。
范叔叔的写作习惯我知道,他说自己“写东西很慢”。他曾初步拟了近二百个题目,想从童年写到老年。每写一个题目,都要看许多自己收存的有关资料,大致将腹稿框架打好后,便反复向别人讲述,在一遍遍的讲述中,激发补充新的回忆,然后一气呵成写下来,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动。关于罗莎,我有幸第一个听他不连贯的口述。那是因为,范叔叔的老伴去世后,他的心情久久不见平复。二○○三年三月,他接受李子云和李黎的建议,来上海散心,与老友聚谈,先在我家住了两日。范叔叔和我都是“夜猫子”。在月朗星稀的春夜,他终于得闲,容我细问细谈了许多事。
范叔叔最终没有来得及写罗莎。或许,他想写但没有写出来的,还有另一些有关书与人,或欢快,或有趣,或曲折,或沉重,或可笑,或哀伤,或惨痛,或值得回味反思的故事吧。
这些饱熏着人类各种情感,又能折射时代风貌,却稍纵即逝的历史细节,就这样随着他的逝去,永远地埋没了。
(谨以此文纪念出版家范用逝世一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