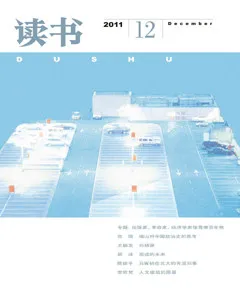传播的大道理与小道理
颇有大国气象的北京西客站已经建成N多年了,与地铁一号线“军事博物馆”站只相隔短短的几百米,与老北京站也没多远,可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为何就始终不能通上地铁相互连接呢?
都知道北京的回龙观小区人口密度大,尤其是每天早晚上下班的时候地铁里更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为何奥运地铁专线不连接上回龙观站分流一下呢——在普通的北京市交通地图上两站之间就那么一指头宽的距离啊!红红火火的北京奥运会已经结束整整三年了,至今奥运专线仍然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孤悬着那么几站。这类曾经风光过、也的确给大伙儿脸上贴过金的“奥林匹克遗产”何时才能转化为小家居民们真正能够享受的日常福祉,从而让北京奥运的光荣和梦想能够真正在老百姓的平凡日子里扎下根、结出果。
俗话说,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生活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尽管我们的载人飞船又上天了,我们的科研论文在国际上发表数量的名次又靠前了,我们的GDP更是一国之下、万国之上了,北京的电视上经常报喜讯,说本市又建成了什么高架桥、又修了多少公里的地铁、六环路又开通了哪一部分,然而这些对老百姓来说其实是没有多少感觉的,即使再宏伟的成就他们也是靠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去体验,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具体而微观的感受,前面那些无论看起来多么辉煌、气派的数字和成就对普通百姓来说都只能是一堆冰冷的、没有知觉的符号。
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在信息宣传和观念传播的过程中经常存在着一种语言上的误用,被称作“死线上的抽绎”现象(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二○○七年版)。它是指传播的语言常常被固定在过高的水平线上使人难以理解、敬而远之;或者相反,传播的语言被限定在过低的水平线上又使人不得要领、感觉乏味。例如当社会上的信息传播中充满了诸如“民主、法制”,“复兴、崛起”等高度抽绎水平线上的字眼,同时又没有相对低度抽绎水平线上的词汇进行配套阐释时,如此传播的信息就会让普通人觉得抽象难懂、与己无关,从而难以认同。要克服这一传播困境,就要求传播的语言信息根据实际内容和文体特点,沿着抽绎阶梯适当地做上下波动、有涨有落,既要有相对高抽绎水平的宏观概括和总结,也要有相对低抽绎水平的微观描绘和体验。通俗一点来说,不仅要讲宏观层面(如国家、社会整体的进步)的大道理,也要讲微观层面(如家庭、个人具体的感受)的小道理,二者兼顾互动才能有利于促进社会上下的广泛认同及相互共识。
在科学传播中通过调查统计很早就发现一个现象,公众对科学的认知往往有自己的视角和方式,如公众感兴趣的科技知识领域排在最前面的基本上总是医药健康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领域,因而科学传播的重点内容和切入点常被形象地说成是关于身体的科学和关于身边的科学。同时研究发现,公众会运用他们自己的范畴对所获信息进行重新解码(小约翰著,陈德民等译:《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甚至可能以传播者截然不同、或者完全相反的方式来重新解释传播给他们的信息。这也就是说,从受传者的角度看,外在的大道理是要靠其内在的小道理来理解和感受的。战后美国独领风骚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后期,科学家们试图一鼓作气,雄心勃勃地又提出了登陆火星的计划,但旋即遭到美国议会的否决。美国人民在最初的举国兴奋之后发现“阿波罗”登月计划实际上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看完激动人心的电视实况转播后他们该干嘛还得干嘛,毋庸讳言这也与当时美苏太空军备竞赛压力下导致“阿波罗”计划较少考虑经济效益有关。美国人民质疑:为什么科学家更关心三十八万公里以外的东西?花了二百亿美元就带回来几包土——尽管是月球上的土,可这对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又有多少意义呢!这表明,堂而皇之的大道理需要依靠亲切朴实的小道理进行解读和支撑,否则结果很可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力于我何有哉”!此外,根据传播学的交互理论,如果被传播者拒绝接受,或者没有感觉、无动于衷,那绝不是因为他们脑子笨、理解力差,而是因为传播大道理的人自己“嘴聋”。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高能物理研究遭遇重大挫折,已经投资数十亿美元的超级超导对撞机(SSC)项目被否决,其电子对撞机规模庞大、耗资不菲的地下运行隧道在今天的一个实际用途只是“养蘑菇”(迈诺尔夫·迪尔克斯,克劳迪娅·冯·格罗特编,田松等译:《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因为那里面冬暖夏凉。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哀叹:这是“二战”后该国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的最大失败,而主要原因就是与公众缺乏有效的沟通,没有得到美国公众的理解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