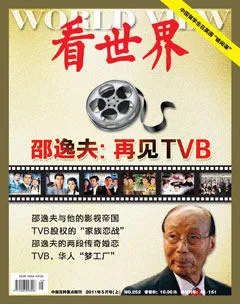亲历日本“黑船事件”的广东人
据说当年哥伦布船上有一个广东人,在看见新大陆时,他第一个喊出声:“啊!咩黎咖?”(粤语:“啊!这是什么?”)从此,美洲大陆就叫“America”了……这当然是一个笑话,而在历史上,有一个广东人,他和来自美洲大陆的人们一起结束了日本的闭关锁国。
当时的日本
乾隆年间,全国展开过一场查禁私钱的活动。这一天,例行公务的人们在沿海发现了一枚“宽永通宝”,成为了震惊朝廷的事件:因为中国并没有“宽永”的年号,而建号铸钱又是造反立国的事情,以致于当时的清廷认为有人图谋“大逆”,号令各省大力严查,一时间人人自危。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不过是一枚日本铜钱,结果闹得“守令仓皇,莫知所措”。
尽管明亡之后,有部分文人逃往这个国度,其中也不乏朱舜水这样的著名人士,但随着闭关的枷锁越来越重,到乾隆年间,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几近忘记了这个邻国。尽管民间的人士偶有与大和民族打过交道。如商人汪鹏曾经跟随商船到达长崎,在他的《袖海篇》记录了当时的一条谚语:“日本好货,五岛难过。”又说长崎:“风土甚佳,山辉川媚;人之聪慧灵敏,不亚中华儿女。”但这些记录无关痛痒,说出来也不过算是矮子里面挑高个儿。
更早之前,史书里并不缺乏日本的记载,只是大多很茫然,这个国家无非是被贴上了扶桑、乐浪海国一类的标签,人们对它兴趣不大。
这种情形,直到光绪年间也没什么改变,诗人黄遵宪写《日本国志自叙》,还说:“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历世纪载又不详其事,安所凭藉以为考证之资,其狭隘也亦无足怪也。”
这些直到“花旗火船”开来,才大有改观。“花旗火船”是指美国的商船,因为在当时的国人看来,绘有星星和条纹的旗帜过于花哨,故称“花旗”。在“花旗火船”到来之前,日本和中国一样,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国家。1635年德川幕府全面避国,比康熙海禁还要早80多年,并且幕府对出国、信基督和接触西学的惩罚,比中国还要厉害得多。锁国期间,被允许到长崎在严格管制下通航的只有荷兰和中国。十八世纪的最后一年,美国帆船商船“富兰克林号”第一次访问日本,船长奉命当海岸一旦在望的时候,立即悬起荷兰旗,冒充荷兰船只。船上的一切书籍,特别是宗教书,在临近日本的时候,必须装箱钉死。可见当年日本锁国的彻底。
1837年,美国商船“马礼逊号”以送回遇难日本船民为理由,从澳门行驶到江户湾,希望和日本建立联系,但日本的见面礼是大炮狂轰,七名日本船民也没能被允许上岸。
不懂日语的广东人
1853年6月3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狂热的扩张分子马登·柏利率领舰队抵达日本,以武力要挟日本开港。这次柏利的船队包括两艘轮船、两艘军舰,由于美国船只刷黑漆,日本史籍称之为“黑船”。当时的幕府被迫接受了黑船带来的美国国书,并答应次年春天给予答复,除了日本之外,柏利还鼓吹美国应该控制台湾、琉球和小笠原群岛,甚至把美国的“国家友谊和保护”延伸到暹罗、柬埔寨、婆罗洲、苏门答腊。
第二年柏利舰队再次来航,在从香港出发前,鉴于此前没有配备称职的翻译人员,柏利在香港特邀美国传教士威廉士担任自己的翻译官。威廉士精通汉语和日语,在广州开了一家印刷厂为教会服务,并广交朋友,罗森就是其中一位,并与之同行。当时日本著名画师锹形赤子曾经为“黑船”上的来访者一一画像。于是今天我们在《大日本文书》中所收录的《美利坚人应接之图》中就可以看到,在一群美国人之中,有一个戴着瓜皮帽、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画像旁边写着“清国人罗森”。而在罗森自叙里,他表字向乔,“产广东”。在他与日本人的笔谈里,他亲历过太平天国的战事,他似乎会一些英语,更可能是一名教徒。
威廉士在《日本日记》前言中明确指出:“今有一唐人,为余平素知己之友,去年搭花旗火船游至日本,以助立约之事。”也就是说,罗森并非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而是以美国舰队翻译的身份前往日本的。
罗森的生平已经无处了解,不懂日语,但是可以用汉字和日本人在纸上“笔谈”,因为当时日本的官员和读书人都熟悉汉字,更因为一个常常为人所忽略的事实:日美所缔结的一系列条约,除了日语与英语版本以外,还都有汉文与荷兰语版本。荷兰语在当时是作为正式的交涉用语使用的,但是二者之间实际的交流,在大多数场合所使用的是当时可以被看成东亚的“国际语言”的汉文,而不是英语、日语或者荷兰语。
当时的日本人基本不懂英语,当然,当时也鲜有美国人精通日语,能够懂荷兰语的只有一部分“通事”(翻译)而已;与此相比,尽管“笔谈”不得不倚赖于纸笔,交流受到一定的局限,但是几乎所有的粗通文墨的日本人都能够用汉文进行笔谈。因此,当柏利舰队第二次来航的时候,荷兰语不再被用作基本的交流语言,几乎所有的翻译都倚赖于威廉士和罗森。
罗森以当事人的身份考察了日本横滨、下田、箱馆等地的风土、民情、风俗、物产等等,看到了开放前夕的日本的历史面貌,他亲笔记录下来日本见闻回国以后以“日本日记”为题在1854年11月-1855年1月的《遐迩贯珍》上连载,真实反映了开国前夕日本的社会状况与开国的历史进程,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
幕府的仪式
幕府这一次已经做好了妥协的准备,十年以前,幕府大将军还在恢复荷兰国王的信件中信誓旦旦地说“祖宗成法,不可更改”;但这一次给美国总统的信件里却说“对我们而言,继续泥守古法,似乎是误解时代的精神。”但是,对于美国舰队,日本的基本态度仍然是严密戒备,罗森如实写道:
“初事,两国未曾相交,各有猜疑。日本官艇亦有百数泊于远岸,皆是布帆,而军营器械各亦准备,以防人之不仁。”
美方谈判人员住进公馆之后,日方又以馈赠之名送了200多包玉米,每包重200多斤,并且派遣90多位“肥人”(即相扑),裸着身体将这些东西送到海边,然后令他们进行相扑,以显示“日本之多勇力人也”。
幕府大将军(被罗森称之为“京城大君”)拍了大学头林鹈殿等人和柏利谈判立约的事项,罗森也参与了这一份工作。但是日本人竭力建议美国接受原来荷兰通商的条件,以长崎为口岸;柏利则以中美《望厦条约》给日本看,要求立即开放三到五个通商港口。
日本人对中国发生的事情特别关心,有个叫做平山谦二郎的,向罗森询问中国情况,看了罗森写的《南京纪事》以《治安策》二本册子之后,用汉字给罗森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这个日本人表现出了和当时中国保守派的人同样的立场上,认为国家与外国断绝交往,是因为外来者往往在欺骗愚蠢的国民,他们唯利是图,没有礼让信义。而平山谦二郎最希望的是保持现状,并且提出了一个天真的想法:乘坐外国人的火船周游四海,向全世界的人宣传孔孟之道。
还有一个叫做明笃的日本人,在与罗森交谈的时候说:“您是中国人,为什么还要改变自己的正宗语言,去学外国人的语言呢,岂不是弃明投暗吗?”罗森用诗歌:“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皆比邻”回答了他。从这两件事情中,可见当时日本的士人对开放的态度,反倒是罗森的态度,比他们要开阔乐观不少。
谈判在3月25日达成协议,日本允许箱馆(即“函馆”)、下田(今属于横滨)两个港口为美国(罗森称为“亚国”)取薪水、食料、石炭之处,“由是两国和好,各释猜疑”。次日柏利在船上宴请了林鹈殿等数十人,并向幕府大将军赠送了礼品火车、电话、照相机等。在当时,这些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对于日本人来说,比中国人更为生疏。
在锁国2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生活过来的日本普通民众,也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毫无思想准备。罗森记载,日本开国之后,火船开至箱馆,当地人民不知道来者何物,有一半以上的人逃到外地去了,直到“用温语安抚百姓”后,人们才“还港贸易”。在下田,美国的官兵排列队伍,游览乡下,“男女人民观者如堵”。日本历史上本该发生的“鸦片战争”,就这样一枪不响地结束了。
“其实,我是一个商人”
初到日本,罗森以好奇的眼光观察日本,不遗余力地描写日本社会的“怪异”之处。他发现日本人的服装颇有古风:官员都“阔衣大袖,腰佩双刀,束发,剃去脑信一方,足穿草绿,以锦裤套至腰”;日本女子则“衣长委地,腰后有裙,以红绸束其发髻,颜色多美艳”。
而他觉得与中国的宅子相比,日本的住房则像一座迷宫,“比邻而居,屋内通连。故曾入门见其人,再入别屋,而亦见其人也”。如果不了解日本房屋的结构,日本人看起来果真是“神出鬼没”,未免真会产生“白日见鬼”的感觉。
罗森还处处将日本与中国进行比较,并热衷于“发现”日本的“落后”之处。如饮食方面:“予见人家蓄鸡至数年而不宰者。以言食物,则万不及于中国。”而一直为现代宅男们津津乐道的日本人对性的随便态度,则更令他瞠目结舌:“稠人广众,男不羞见下体,女看淫画为平常。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于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
以正统的儒家道德为标准进行衡量,这种男女关系当然是大逆不道,匪夷所思,因此,日本在罗森笔下被丑化成了一个男女关系混乱的社会。相比之下,美国人的《菊与刀》显然要理性得多。
当然,日本也并非处处不如中国,他发现天朝的社会治安就大不如日本:“夫一方有一方之善政,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劫之风,亦未尝见。彼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有鼠窃狗偷之弊。此见之略,各有其能矣。”我们在审视、想象他者的同时,总是进行着自我的审视与反思。
回想1854年,日本人见证了美国人演示的火车模型、电话机、照相机,诧异为未曾见过的“奇术”;而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日本的汽车、相机、电子产品却牢牢盘踞了制造业的市场,这其中的深意,实在值得玩味。而罗森作为见证日本开放国门的中国人,用汉字写下的《日本日记》篇幅虽然不多,价值却超过了在他之前关于日本的记述,更不用说那些士大夫在书斋里遥想海外神山的作品了。
罗森的文字并不高明,诗歌也写得乏善可陈,可见罗森实在不算是孔门弟子。但在对日本的历史文化记载也不多的《日本日记》里,却对这个岛国的物产、贸易、市容注意得很。有趣的是,在舰队返航中,被罗森称为“美士摄被”的柏利的座驾“密西西比号”先回香港复命了,罗森和卫廉士则同船到了宁波。他在镇海收购了一批生丝,因为他知道,那里的丝“价略低于粤省”,大可以赚一笔。——在日本人绘制的《美利坚人应接之图》里,罗森科头皂服,当翻译、做笔录之类的事情实在不是他兴趣的所在。他的出海,更多是为了赚一笔,其实他只是一个广东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