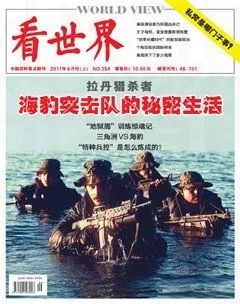学生不应是教育的对
“中国还不成熟的东西能成为模式吗?我们要继续探索、试验、改革、发展,这样中国的教育才会更好。”5月13日,广州中山大学“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年会”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民选发言说。每年一度的会议始终延续着对中国教育问题的面面观和深度思考。
大学的学院太多了?
会上,经济学家张曙光痛斥“市场化的扭曲腐蚀了学人的灵魂”:“我们现在的教育、学术还没有摆脱权力的掌控,又落入了金钱的奴役和驱使之中。现在的教学也好、研究也好,只要你不对现行的意识形态提出质疑,你可以不择手段去追求经济效益。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和学术环境我觉得是相当恶劣的一件事情。”
“第二,我们的学校官僚化。学校不是教育家、学问家在治理,而是官员在治理。学校里面的很多领导我觉得很官僚,很多真正的学问家、教育家被边缘化,因此出现了很多‘学官’和‘官学’。还有,我们的知识生产工厂化。有教授曾经说过学校不是养鸡场,但实际上我们的学校已经变成了养鸡场,主管部门变成了发包商,导师变成了承包商。我们只有知识,没有文化。”
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院长丁钢教授认为,只有反思从人才内涵和培养机制以及其背后的制度文化原由,我们才不至于仅仅停留在现象的分析。丁钢说:“目前,我们大学里的学院数量过多,这容易造成各学科专业之间相互独立。每一个院系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堡垒,堡垒越多,壁垒就越深,而壁垒越深,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一种合理的人才培养机制的原因之一。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三个和尚没水喝’,似乎中国人缺乏人际合作的可能。其实,关键是三个和尚是各自完全分隔的利益个体还是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体制和机制是用来调节人与人和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只有既关照每个个体或机构的利益,同时又考虑到个体和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的利益关系,这样的体制和机制才能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
香港中文大学校董、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卢乃桂则提出了教育中的“不开心”问题:“2003年美国《时代》杂志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报道,提出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亚洲的孩子不愿意上学?每一次香港有台风,不用上学,我自己的孩子会特别活泼、特别开心,为什么他们都不想回学校?学校本来是让人发挥所长的地方,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真的是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学生不是教育的对象
在不断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中国大学的自主权逐渐觉醒,但在大学自主招生之后,它们还需要做哪些观念的转变呢?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董云川教授认为,学生不是教育的对象,而是服务的对象。董云川说:“大学生是成年人,已经不是简单的受教育对象,大学教育活动ly9W8KhmytYqIEex4QeKoqWO8UatUKxySSyZ7NX5juc=由师生双方协同共生,因此,大学生其实是教育活动主体之对应方,而非上下位被动接受‘教育’的一方。在中国,好学生的标志之一是‘听话’,教师被视作当然的教育者,是上位概念,学生是当然的被教育者,是下位概念。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明示了‘我’教育‘你’之快乐。其实,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不仅仅是个说教者,更主要的是一个‘帮助他发现自己’(伽利略语)的参照系。”
相对于现今教育界炒得火热的“创新”,董云川反而认为,创新不是教育质量的关键,返璞归真才是当务之急,那么,“返璞归真”指的是什么呢?
董云川解释说:“许多大学在创新的大箩筐工程中盛入了许多闲杂事务,那些本该做到位而没有做到位的事情今天统统都被纳入创新工程,而且不断被‘深化’着。我的疑惑是,真有那么多的创新吗?如此价值判断使得人们误以为,中国大学的教育品质不高是因为创新不足。其实不然,中国大学的质量问题根本上是因为基础不实,不守学问之规矩,既不能够、又不安心提供足额到位的教育服务所至。也就是说,该做的事没有做好,而乱麻麻地去做了一些不该做或者暂时不必做的事情。”
中山大学教授夏纪梅则认为,中国的大学还需要减负。“中国是世界上博士最多的国家,却又是大学毕业生获‘诺贝尔奖’为零的国家;是世界上出国留学生最多的大国,却又是接受外国来华攻读专业留学生的非热门国家。所以,可以说中国是教育大国,但还不是教育强国。我国基础教育累死人,高等教育闲死人,这种状况和美国相比,正好相反。所以,中山大学率先在国内提出‘基础教育要减负,高等教育要增负’。”基础教育累死人,高等教育闲死人,这确实是让当今很多学生和家长最为头疼的中国教育现状的真实写照。
教育的公平性待关注
“我关心什么事情呢?我关心6000万的留守儿童问题。”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在发言中说。信力建认为,由于户籍问题的限制而影响到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6000万的留守儿童没有家庭教育,也缺乏学校教育的话,将来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最拖后腿的一个问题。统计数据表明,城市的刑事犯罪有50%来自于农村,其中50%来自于年轻人,我觉得这非常值得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教育行政领导和研究人员探索的问题。8年前北京市一年级入学学生从16万减到8万,广州现在户籍出生人口和非户籍出生人口1:1,50%是非户籍人口。如果我们固守户籍人口才有权限读书的权利我觉得非常不应该,因为本身中小学的学位是有富余的,如果我们不拿出来帮助穷地区,或者帮助常住居民的话,我觉得这是极其不道德的。”
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教育专家劳凯声教授也认为,有一件事情是互为因果的,人们都说教育会产生社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又会反过来加剧教育的进一步不平等。这就是现在教育问题的所在。同时劳凯声也认为,教育改革中的腐败也是亟需重视的问题。很多人都把腐败看作改革的伴生物,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如何能够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来遏制改革中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这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中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
“我们改变不了制度,改变不了时代,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云南大学高等教育学院院长董云川的话似乎最能够让人思索,教育问题往往不只是教育问题,但如果仅仅是把所有的改革之责任都推给其他方面,那也将是中国教育的最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