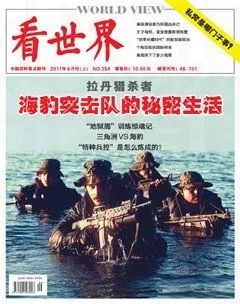巫术渗入美国人的生活
2011-12-29 00:00:00稼辛
看世界 2011年11期


女巫和房地产
“邪气!屋子里有邪气。一定要把它驱赶出去。火焰之王啊,愿你的圣名永不败退……妖魔鬼怪通通消失!”这是现年70岁的布鲁诺女士正在为托尼·巴莱塔于马萨诸塞州购买的二手房作法。
这是一所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子。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指借款人因还款违约而失去赎回抵押品的权利。在美国的房产市场上,这样丧失赎回权的房屋实在是太多;几乎每一个这样的房屋背后,都有一个经营惨淡的业主。于是一些买家不得不借助“魔法”的力量去除邪气,因为他们发现,薄薄的一层油漆根本不足以去除房子里的惨淡气氛。
托尼购买的这座房子位于塞勒姆的阿贝拉街31号,这里地毯破烂、光线阴暗、泡沫绝缘材料从墙壁的裂缝里支了出来。还好托尼也正打算对房子进行彻底的翻修,但让他心烦的是这里似乎有某种不祥气息。靠着取消抵押赎回权危机的推动,巫师、灵媒、神甫和风水师之类的人物重新走红。现在美国的房屋卖主们都赶上了这股潮流,请巫师净化房屋,为住宅举行赐福或是驱魔仪式——在美国有很多像托尼这样的买家正在纷纷向巫师求助;而地产人士也乐此不疲,为的是让陷在房市里的产业动起来。
谈妥价钱之后,托尼从自己的房产经纪那里听说了这对法师搭档。他说,“我是个相信灵性的人,这么做只是为了在入住之前清除房子里的负面能量。”
所以在签约之前两个星期,托尼跟着这位自称是十六世纪一名意大利女巫后裔的女士以及术士戴伊,把这幢三层楼的住宅清理了一遍。他们更换了门铃,在门口洒了点圣水,并倒了些祛邪的犹太盐,还在窗子上竖了几把铁剑。
这一对搭档的祛邪仪式包括几种手段:她说,响亮的铃声可以打破空间里的负面能量。与此同时,戴伊一边在起居室里挥舞宝剑,一边说,铁可以把邪灵挡在门外……
——也许很多人对90年代出现在香港电影里的常见风水记忆犹新,也许有人认为只有中国人才会对房子的穴位、布局十分在意。但的确这个产业硬生生地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并且大有跟随着房产业四处扩张游走的迹象。
1692年,塞勒姆曾经进行过一场女巫审判。就在这个地方,神奇巫术现在已经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拥有被命名为“女巫”的中学运动队,更有大量专业的“巫婆人士”。戴伊拥有一间名为“旧大陆魔力”的魔法商店,布鲁诺则在店里讲授通灵课程。
塞勒姆的地产经纪珍妮特·安德鲁斯·豪克罗夫特说,“这是个非常相信魔法的城市。”
“如今我们要对付的已经不再是有形的鬼怪。由于房屋的赎回权遭到取消,围绕这些事件的讨论、争议和金钱纠葛产生了许多负面能量,全都被吸收到了房子里。”——再三声明,这不是在拍电影,而是巫界的通灵人士朱莉·贝尔蒙特在发言。
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家斯图尔特·维斯曾长期从心理学角度对迷信做深入研究。还认为,在历史的特定时刻,人们更易迷信。如二战、经济大萧条乃至海湾战争时期,迷信的人就比其他时候明显要多,维斯解释说,这是由于在这些“特定时刻”,人们往往被焦虑心理所控而难以“清醒”。
朱莉·贝尔蒙特的工作地点是加州的橙县,那个地方去年的住宅销售当中有40%都属于贱价甩卖。这个地区经济的不景气显然是巫术复兴的温床:
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风水顾问洛金·诺斯利普与亚利桑那州斯科特戴尔的地产经纪詹森·戈德伯格结成搭档,为客户提供房屋转运的一揽子服务,时间可以在销售之前,也可以在购买之后。他们两位是在一个瑜伽度假村里认识的……
在加州的萨克拉门托,地产经纪塔马拉·多里斯也通过风水卖掉了一处滞销了一年多的房产。当时她在房子里的“招财角“摆了一株据信可以带来财运的发财树,然后就等着客户上门……
胡毒和运程
与源自欧洲的巫术一样,很久以前黑人奴隶在美国南部诸州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依靠符咒、药剂、精油和诅咒来实现愿望的古老的信仰体系,也开始在美国走红。它叫胡毒巫术。
几十年来,胡毒巫术商店似乎行将灭迹。但是互联网和这个麻烦不断的时代让这种曾经一度只在偏远森林中的小屋内或城市里破败商店中举行的宗教仪式获得了新生。胡毒巫术从业人员和零售商表示,随着全国各地的人们跑来要他们帮忙减少债务、防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或者找工作,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居住在康涅狄格州格罗顿市的39岁的詹妮弗·福尼斯发现她的生活实在是糟糕透了:她的丈夫向她提出离婚;她丢掉了商店店员的工作;因为压力过大,她的健康状况也出现了问题。
后来有天晚上,她发现了一个销售胡毒巫术产品的网站。福尼斯订购了几样产品以及举行某种仪式的说明书。她还和胡毒巫术专攻就业问题的“医师”进行了电话授课。从那以后,事情有了转变。福尼斯找到了在酒吧当服务员的兼职工作,她的身体状况也有所恢复。她说,我们有道理相信这些东西。
理查德·米勒说,我们的生意很好。米勒在亚特兰大市区的一处荒僻地段开了一家名为“米勒的记忆”。这家商店出售胡毒巫术和顺势疗法商店。米勒是个白人,和黑人没有一点关系,但尽管如此他的商店依然有顾客光顾,其中不乏许多著名人士,例如前披头士乐队的成员麦卡特尼曾经在他的商店买过一瓶名为“走开,魔鬼,走开”的浴盐,并且以此命名了1999年发行的一张专辑。——事实上更多的销售额来自于网络销售。尽管米勒那些“驱邪”和“龙血”之类名字的商品不过只是精油、肥皂和浴盐,但他承诺能够把邪恶的东西驱除掉;尽管在流行文化中胡毒巫术和更为知名的巫毒教之间的界限经常模糊不清:胡毒巫术产生于讲英语的美国殖民地的奴隶中间,而巫毒教则是在讲法语的海地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自己创立的宗教,其中还吸收了非洲众神论和天主教的教义;尽管罗格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唐纳德在自己的著作中说,胡毒巫术不仅仅是“噢,帮我把孩子找回来吧”或者“让我老公回来吧“之类的咒语。
如今胡毒巫术的兴盛主要还是由白人零售商推动的。一些黑人在批评他们把这种古老的仪式商业化,但一转眼,这些黑人也开始利用它们来投资赚钱:一位声称从小就被传授胡毒巫术的黑人巫师说,这些商店兜售劣质的、毫无效果的产品,专注于所谓的快速解决问题,而这正在败坏胡毒这种信仰体系。但紧随其后,她立即开设了自己的信息网站,声称它是唯一真正的关于古老的胡毒传统的网站。
年轻黑人也在发现胡毒巫术,即使这些很可能源自他们的祖先。生活在亚特兰大30岁的安吉拉·艾伦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她说,所有上了年纪的亲戚中没有人会跟她谈起胡毒巫术,因为他们认为它是反基督教的。但是,当艾伦在大约三年前债台高筑时,她开始对胡毒巫术感兴趣。她说,当时我感到很绝望,而且我必须得做些什么。她说,慢慢地,她的财务状况有所好转。现在,她定期会从网上购买胡毒巫术的产品。
斯图尔特·维斯教授分析了许多导致迷信的心理因素,其中包括无助感、恐惧、抑郁、沮丧和过分渴望成功等等。某些人或某些职业较易迷信,如赌徒、演员、运动员、商人、企业家、探险家等等。一般来说,这些人或这些职业有保持成功的巨大压力,“是否成功”常常会受不可捉摸的因素所左右,由此渐渐倾向于迷信。例如毕加索:一次,他回头看见不知谁把帽子放在了他的床上,从那天起,他相信,有人正在想除掉他,让他尽快到另一个世界去。——因为许多西方人认为把帽子放在床上无疑于把花圈送到棺材边。
巫医和灵魂
虽然美国已步入电脑和太空时代,科学技术可谓日新月异。然而让世人大感惊异的是,讲迷信的美国人却越来越多,其中不仅有平民百姓,而且也有达官显贵以及专家教授级的知识精英。
旧金山东南部120英里的加州默萨德仁慈医疗中心曾经开展过萨满教巫师计划,它是用来加强医生和赫蒙族人的信任感,并为了弥补多年来赫蒙人对医疗机构的误解。现在,这个计划已经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信任。
赫蒙族是东南亚苗族的一支,在30年前为逃避战乱由老挝来到美国。他们相信灵魂容易迷失或者被恶毒的神灵所捕获,在赫蒙人的信念中,外科手术、麻醉、输血和其它一些平常的医疗手段都是禁止的。
巫医李圭蒙(音译)经常身穿绣花夹克,并且胸前佩戴有官方证件。他能够随意进出被移交给神职人员的病人房间。他将一卷细线绕到病人的手腕上,用以召回病人迷失的灵魂。李站在来自老挝的病人邵长腾(音译)的身旁,通过他的手指,用一个无形的“防护屏”在空中追踪迷失的灵魂。赫蒙人相信:灵魂就像迷途的儿童,容易迷失或者被恶毒的神灵所捕获并导致疾病。
西方医学中融合萨满教巫师的政策和计划是美国重新考虑病人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而推行的全国计划的一部分。为了迎合移民、难民和少数民族的需要,这种方法被美国全国几十个医疗机构和诊所采用。取得执业资格的萨满教巫师,身穿绣边的短上衣、别着官方颁发的徽章,和牧师一样有权利接近病人。萨满教巫师接受活鸡作为酬劳,可是他们没有其它的保险和报酬。
美国作家安妮·法迪曼在1997年以“一个赫蒙族家庭和默萨德医院因沟通不良导致产生巨大影响”为主题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一个赫蒙族儿童和她的美国医生们》。这本书跟踪了一个年轻的赫蒙族女孩治疗癫痫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医院没有认识到这个赫蒙族家庭根生蒂固的文化理念,最终导致病人的疗效受到影响。这个事件产生的余波和这本书引起了医院的反思,最终导致萨满教巫师治疗政策的最终建立。
在维斯教授的新作《相信魔法:迷信心理学》一书就曾写道过,相信迷信的美国人的“实际比例”可能还要高一些。这是由于在许多文化,包括美国文化中,迷信往往被视为“笑柄”,因而美国人对自己的迷信行为往往羞于承认。
本刊曾报道过美国的魔法学校。事实上,在这个科技最发达、科学最深入人心的国家,时下最常见的“传统迷信”还包括:人不能从梯子下走过;夜行遇黑猫意味着不祥;看到4片叶的苜蓿草是好运即将来临的征兆……另据一项民间调查,时下有25%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多少有点迷信”,至于把“6月13日又是星期五”认同为“不吉之日”者的比例,则更是高达半数以上。
在美国这个文化多元化的国家,巫术也一样的多元化,当然细心的人们都能发现,无论是女巫净化凶宅,还是胡毒改变人生,或者病怏怏的巫医治病,有一点不会变的是,这些黑色巫术的背后,是经济不景气后一颗更加黯淡的心。就像2001年9月11日那一声轰天巨响,在今日美国,“9·11”这个数字毋庸置疑地成了最不吉利的“黑色数字”,如同那天的阴云,久久笼罩在美国人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