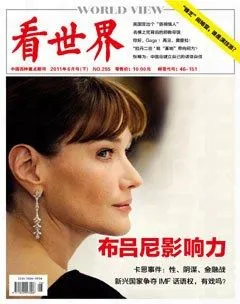大清女子海外游记
走出闺房
在蒙昧的年代,中国妇女的启蒙和觉醒自然更加艰难,而走出国门和走向世界的则更加稀少了,这其中除去一些商人的家属,剩下来的知识女性更是屈指可数。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秋瑾和何香凝。更早以前,在梁启超的笔记里,可以看见一位康女士。她是九江人,自幼失去双亲,被美国人收养并且进入了“墨尔斯根省之大学,以发念救众生疾苦因缘故,于是专门医学”。这位康女士在大学毕业之前的经历和容闳十分相似,遗憾的是,未能有类似于《西学东渐记》的作品传世。所以在民国成立之前,经历列国,并有所记载的中国女性,便只有单士厘了。
这位中国妇女出生在一个文化教养程度极高的家庭。其外祖父家先人官至礼部尚书,舅父许壬伯的著作多达十余种,她的自述曾写道:“家世余黄卷”、“书籍不少”。这些书成为了她一生中的宝物。
单士厘生于1856年,幼年丧母,随舅舅读书,受到了慈母严师般的照顾,得以在闺中涉猎子史,玩习文字,大概是由于舅家钟爱,择偶严格的关系,直到29岁,她才出嫁,在当时,这样的大家闺秀是很少的。而她的丈夫,是钱玄同的长兄钱恂。钱恂比钱玄同年长34岁,青年时期就出使过欧洲,后来又到过日本,并先后做过出使荷兰和意大利的公使大臣。他身为清朝外交官,思想上却接受了中产阶级民主观念的影响,在清末甚至加入了光复会,并以实际行动参加了辛亥革命,当了民国政府的顾问。
即便到了晚年,钱恂的思想依然能够与时俱进,对保守顽固势力持批评态度。在鲁迅1913年9月28日的日记上,就有记录到钱恂在祭孔“大声而骂”的事迹。
单士厘与钱恂结婚以后,感情不错,她常常在诗歌里表达对新婚远别的丈夫的思念,而钱恂对妻子的习惯和趣味也表示理解。在单士厘后来写出的《马哥博罗事》一文中,回忆钱恂20年前从西欧回国,为她讲述了马格博罗(即马可波罗)的轶事,令她艳羡不已,对意大利的山川、人文无比向往。她立志与夫远游,能“亲履维尼斯,仿马哥之故居,瞻马哥之石像,既记游事,又记马哥父子叔侄来华之踪迹及行事大略。”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才学、有才智的女子不少,但像单士厘这样对外国如此向往并能亲身游历的,并不常见。更多的是委身闺中,叹几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首访日本
“汽笛一声,春雨蒙蒙,遂就长途。”这是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1899年,单士厘以外交使节夫人的身份首次赴日,这一年,距离秋瑾赴日还有5年。
在这个她第一次到访的国家,从大阪到京都,单士厘见到日本游览地陈设朴素,不似欧美浮夸炫耀,不禁洞悉到日本专务实用,不尚耀。“东京市场所售的西式物品,以图籍、工艺为多,不象上海‘洋行’多是钟表、戒指以及玩品。”其观察入微,议论中肯,对于维新时务具有真知灼见,远非以手表、戒指为时髦的夫人小姐可比拟。
这个年代的日本,正在从向中国学习的惯性中脱离出来,并转投欧美国家的怀抱。在参加了万国博览会后,日本开始大力在国内兴办博览会。单士厘也有幸参观了大阪博览会。
在参观完后,她颇有感触,觉得在国内也应该举办博览会,尽管规模不能与万国博览会相比拟,但能“唤起国民争竞之心”。在大阪的“山寨世博会”里,单士厘对各馆分别进行了考察和记述,在论及教育馆时,单士厘感慨:“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日本之所以能举办第五次博览会,也是因为教育发达。教育的根本是为本国培育国民,并非为政府储备人材,所以男女并重,且孩童无不先本母教。因此教育的根本,女尤倍重于男。”
也就是在大阪博览会时,她和儿媳一起游览,虽遇大雨,也依然步行,当时国内的妇女很少出门,更何况冒着大雨步行于人流熙攘的场合,她的儿媳似乎有所顾虑。见此,单士厘对她说道:“今日之行专为拓开知识起见。虽踯躅雨中,不为越礼。况尔侍舅姑而行乎?”
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审视中国传统文明的缺点时仍不忘其具有不可抹煞的优越性。如在谈到女子教育时,她提到了中国女子对道德培养的重视,并认为是西方妇女所不及的;中国的缺点在于完全没有认识到女学的重要,以为“妇德”就是“一物不见、一事不知”;甚至衍生出“由女德可兴女教,由女教可以强国”的独特看法。
游欧洲列国
1903年,钱恂受命去欧洲列国考察,单士厘随同前往。他们回国盘桓了小段时日,重新由日本出发,经中国东北,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游欧俄诸国,计程2万余里,八十余日。单士厘把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想都记录下来,撰写成了《癸卯旅行记》三卷。书中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对弱小国家的沉重的忧虑,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痛恨,和对清政府投降屈辱感到羞恶。按当局禁忌,外交官员之家属不许“妄谈政事”,然而单士厘却敢于冲破禁圈。
单士厘随夫自长崎乘轮北上,至朝鲜釜山停泊,她目睹了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人民遭受奴役的情景。釜山为日本占领,驻有军队、警察,并有移民居住。朝鲜国民在日本军警的监视下,身背重重的木头,在街道上一边喘气一边走着;轮船装卸工也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下从事繁重的劳动,装卸完毕,日本人逼令他们钻入狭窄的轮船底舱,实在容不下了,“日本人捽其发捺入舟底……”——单士厘所记虽不多,但形态逼真,把日本人的横暴,朝鲜人被宰割的可悯形象都揭示出来了。
对朝鲜人民寄予深切同情的同时,单士厘更希望他们能摆脱愚昧,奋发图强。“又见其一步一坐,无丝毫公德心。无教之民,其愚可叹,其受辱不知又可悲。”其实,这种民族意识的唤起,不单单只是朝鲜人民所需要的,单士厘在当时也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人也缺乏这种意识。当她的旅程到达哈尔滨时,俄国人已经掌握了哈尔滨的大权。
船至海参崴,进入中国东北境要受到俄国人的严格搜查。俄人对中国人的大小包裹、衣物无处不查,就连铺盖也要拆开来搜……没人知道日俄战争就会在第二年爆发,而单士厘对此情此景极端反感,她愤然写道:中国妇女深居家中并不知道国家大事。但自从我走向了世界,就知道了妇女也是国民,国家是否富强,也同样与女国民脱不开关系。所以,每当我看到中国国民进入自己的领土却要受到俄人的搜查,心里怎能不愤慨?
这样的景况之下,单士厘在宁古塔反而却看到了清政府献给“大俄国东海滨省巡抚迟公”的一座功德纪念碑。读罢其中那些谄媚的碑文,单士厘的笔下极尽冷嘲之意。
而当她在莫斯科游历时,她游博物院,游画院,甚至育婴院,每日都记载了有趣的风土人情。而且,单士厘还购买了一张上面印着托尔斯泰肖像的明信片,“托为俄国大名小说家,名震欧美。一度痛气,欧美电询起居者,日以百数,其见重世界可知。”由于个人兴趣的所在,她成了第一个将托尔斯泰介绍给国人的女作家。
推介托尔斯泰
在单士厘的翻译作品里,我们很轻易就能体味到她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良心和激情。她在自己的作品里专门介绍了托尔斯泰。在她的介绍词里,说托氏“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故俄政府禁之甚严。……俄廷待托极酷,剥其公权,摈于教外(摈教为人生莫大辱事,而托澹然);徒以各国钦重,且但有笔墨而无实事,故虽恨之入骨,不敢杀也。”可见她对托尔斯泰的兴趣,除了在文字上的钟爱,更多集中在对这类作家的同情。
这在她的一些译作中也能看得出来,她的用心更在于用译作来表达自己对中国现状的关注,如她刻意翻译了《罗马之犹太区——格笃》中描写罗马迫害、歧视犹太人的情节,并表明就是要“为示王国遗黎受辖于白人治权下之情况。”“阅者宜细心味之。数百年后,吾人当共知之”——这无非是暗示同胞,如果中国还不保国保种,惨状就会与犹太人没有区别。
而她的一系列有关古希腊神话以及罗马神话的神话学论文,在近代中国神话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
从国外归来后,单士厘继续潜心文史,从事著述,她的诗文始终交织着启蒙思想和国民意识的觉醒。钱恂逝世后,她和次子钱穟孙寓居沈阳,1936年钱穟孙亡后,单士厘被长子钱稻孙迎到北京奉养,她活到了87岁,直到离世的三年前,她还写了一首诗关心侄子钱三强的诗歌,名为《庚辰端节家宴,忆三强侄时在巴黎围城中》:可见这位老太太直到暮年,仍然关心世事,关心被困小辈,既不失启蒙时代先进妇女的本色,也不失中国式大家闺秀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