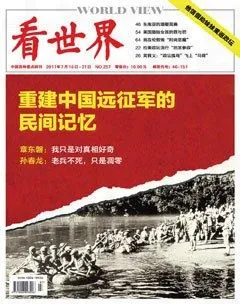远征军老兵的故事
除了认同,别无牵挂
对于战争的记忆,曼德勒的老兵韩天海更多的是不断重复一句话:天天枪响,天天死人。
韩天海出生在重庆,父亲在成都一个叫棉花街的地方开了一家织袜子的店铺,聊以为生。年幼时,韩天海就跟着父亲往来于重庆和成都,帮父亲做事,学业也因此受到影响。有一天,学校的老师找到韩天海的父亲,说这孩子挺聪明的,好好供他念书,将来肯定会有出息。父亲听了老师的话,送他到重庆一个学堂。
1938年的一天,韩天海正在上课的时候,来了一帮兵,要求年仅16岁的韩天海去当兵,那时他正跟着老师唱“抗日救国来当兵”这首歌,没有任何反抗,韩天海跟着这帮人走了。
“那时候好多新兵连手榴弹都不会甩,自己把自己炸死的都不少。”韩天海说。韩天海所在的预备二师,是第一支打入敌占区的成建制的中国军队,在滇西的多场战斗中,功绩卓越,死伤惨烈。
在滇西的高黎贡山上,即使现在,当地的村民翻修土地时,还经常会发现当年死去的士兵的遗骨。
“上了战场,猪狗不如。枪一响,人就成堆成堆地死。”每到雨季来临,韩天海至今还残留着弹头的右腿总是隐隐作痛,也总是让他回到那场不堪回首的战斗中,“我们排在二台坡遇到敌人的伏击,全排人几乎都死光了。那是命令,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师部下令,要地点不要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限几点几点攻下来,前面有日本人,后面有自家人,都会打死你。”
和其他远征军相比,韩天海更多一份让他心悸的经历。就在那次二台坡被伏击之后,韩天海被俘。在日本兵押着他经过刚刚打完仗的一个战场时,他看到,地上全是预备二师兄弟们的遗体,路边的一条小溪,也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被俘的日子里,韩天海受尽了折磨,他亲眼看到,被俘的战友被活埋或者被灌水致死。让韩天海心惊胆战的是,有好几次他都被日军蒙着眼睛押上刑场,但最后,他身边的人都被杀了,他却没有被杀,后来才知道,他是被押去陪杀。
经过几天折磨后,韩天海被送到了宪兵队。因为韩天海是一名新兵,且年龄太小,经过一番审讯,日本人并没有问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谁都知道宪兵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韩天海已觉得难逃一死,想到还未孝敬的父母,他不禁唱起歌来:“第一杯茶敬我的爸,您在家里不要怄,儿去当兵保国家;第二杯茶敬我妈,您在家里不要气,等着儿子回来吧。”
就在韩天海唱歌的时候,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松岗从旁边经过,听到歌声,叫卫兵将韩天海带到自己面前。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当说话已经颤颤巍巍的韩天海在曼德勒的家中给我讲到这里的时候,竟然当着我的面失声痛哭。拉着哭声的韩天海说,他已经是一个快死的人了,有一个秘密在他的心里一直隐藏了几十年,让他一生都感到压抑和自责,始终无法摆脱。
在经过一番讲述之后,我才知道,韩天海是求着松岗才被放过一命的。韩天海说,当时松岗找到他时,问了他一些情况,他感觉松岗可能有一些同情他,就借机乞求说,他是被抓壮丁才来当兵的,打日本人并不是出自他的真实意愿,恳求能放他一条生路。松岗接着问他,“那你愿意做我的儿子吗?”韩天海赶快说愿意。最后,松岗让韩天海帮自己去放马。
韩天海说,他是一个俘虏,他去求日本人才讨了一条命,这让他一生都感觉到非常的内疚和痛苦,他一直也不敢把这个秘密告诉太多的人,害怕别人看不起他,但现在,他觉得说了可能会轻松些。
听到这里,我坚定地告诉韩天海,他没有出卖国家,没有出卖自己的兄弟,是舍弃了自己的尊严挽回了一条命,这没有什么丢人的,不管怎么样,“您永远都是我们的抗日英雄。”
日本宪兵队撤走后,韩天海被日军带到腾冲城里,在军营里干苦役。有一天晚上,一同被俘的一位连长告诉他,日军马上就要完蛋了,肯定会在最后关头对他们下毒手,应该尽快想办法逃走。
1944年5月,反攻腾冲的战斗打响,韩天海和被俘的其他士兵一起,趁乱杀掉三位哨兵后,逃出俘虏营,返回部队,被编入预备二师师部特务连。随后韩天海跟着部队一直打到畹町,跨过河界与驻印军在芒友胜利会师,韩天海也历任排长、代理连长等职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天海离开部队去边境上做一些小生意,以此维持生计。他的另一个打算是,攒点钱后再回家看望父母。但局势逆转,身为中国远征军战士的韩天海已经难以回到他的家乡。
1953年的一天,他因做生意在云南边境碰到了当年的一位战友,这们战友告诉他,当年他被俘后,部队以为他牺牲了,在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里,有刻着他名字的墓碑。
在曼德勒的老兵里,韩天海回老家探亲的心情最为急迫。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曾回到成都找那条叫棉花街的地方,但最终没有找到。当听说我可以帮他找家时,韩天海脸上竟然露出难得的笑容。让我遗憾终生的是,最终因为安排上的一些保守,韩天海至死没能回到家乡。这位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在中国境内有了自己墓碑的中国远征军战士,仍然客死异域。
(摘自《异域:1945》,孙春龙著,新华出版社)
(更多“远征军”内容参见P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