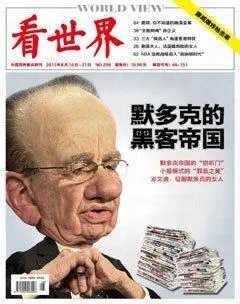雪珥:你不知道的晚清变革
2011-12-29 00:00:00王猛
看世界 2011年16期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大国海盗》、《辛亥:计划外革命》等。
史学界来了个生意人
雪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迈入大学校园,时值改革开放的激情岁月,带着使命感与浪漫,毕业后他回到老家。然而,在最基层的单位,却遭遇了困境: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抱怨,所有人都有不满,在种种利益的纠结下,善治的推行竟如此艰难。表面上看,每个个体都善良且向上,都具有理性,可组合在一起,却如此盲目,甚至明知走在错路上,也不愿改变。在“民意”、“正义”等大词的装点下,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理由,都是那么的豪气干云,然而,当共同的悲剧降临时,究竟谁该负责呢?难道这一切,只是命中注定?离开了机关,雪珥下海经商、当被告、在澳洲洋插队、成了太平绅士……但曾经的困扰萦绕不去,热爱研究历史的雪珥选择了晚清政改作为其思考的开端。
“历史拾荒者”雪珥进入这个领域时,国内清末变革的研究状况是这样:史家往往以“皇族内阁”的骗局和闹剧作为结论,论证的过程充满了荒诞气氛。雪珥自2009年萌发了撰写“石头记”(摸着石头过河,喻改革之意)的梦想,至今已撰写出晚清变革三部曲。当《绝版恭亲王》、《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在国内相继出版后,颠覆了许多人的观念。有人说,他“美化”了昏庸的晚清,一个血腥腐败的政权,居然主动地大力推行全面变革,积极地、冒险地扩大执政基础……也有人说,他的书比教科书更加可靠。因为谁也无法否定,雪珥的研究横跨整个时代横切面,著作中不仅引述了大量被国内史学界忽略的国外文献资料,还有当年大量震撼人心的图片。
由于长久浸淫在单一的历史叙述之中,国人对晚清的印象更多的是老迈与麻木,但在雪珥笔下,这个时期却风云激荡。可惜的是,一番又一番嘹亮的口号,迎来的是一次又一次惨痛的失败。雪珥难以理解的是:难道这种种挫折,仅仅是因为出了几个坏人,仅仅是因为少数人犯了错误?这一切,真的没有我们自己的责任?
多研究些问题
雪珥写史,抱持:以“人性”为中心,以“利益”与“权衡”为基本点,不倾向任何“主义”,只研究各种“问题”。利益是外在的砝码与动力,权衡是内在的行为与抉择。
众人皆知,任何变革,最重要的是警惕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才是变革最凶恶的敌人。皇权、绅权、民权,其实是三方博弈,其中的枢纽是绅权。在雪珥笔下的晚清变革中,绅权绑架了民权,将自己打扮成民权的代表,最终导致皇权失控,民权最后也没有伸张。
就拿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四川保路运动为例,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发生争执的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200多万两资金被老总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他们要求中央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来补贴他们这个损失。四川公司和中央谈不拢,就骂中央把路收回去是卖给老外,其实中央是借外资来推进铁路国有。川路的股东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为自己的血汗钱着急,加之革命党趁机捣乱,中央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武昌空虚,起义成功。
结合康梁和孙中山等人在海外的所作所为,雪珥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在野者永远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执政者描绘成魔鬼,这是一种夺权的策略需要;同样的,后世的执政者也永远把前代的执政者妖魔化,以便证明自己是伟大的、正确的。自晚清以来,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到石头、摸错了石头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统统成为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热闹、讲风凉话、等待着时机以便“彼可取而代之”的人,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当然永远正确了。指点江山太容易了,关键是怎么做。唾沫横飞的批判者并不当家,其实并不关心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事务在他看来,无非是将当家人赶下来取而代之的“投枪和匕首”而已。
中国是个大国,而变革是一种利益调整,因此,在变革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体系来支撑。雪珥认为,实现公平、公正的前提之一是稳定,在稳定状态下尚且不容易达成的目标,是绝对不可能在动荡中达成的。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问题还得靠变革,靠建设。
告别革命
晚清制度变革是必须的,关键在怎么改。任何变革,都应循序渐进,可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人却沉浸在浮躁情绪中,认为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时间长、见效慢,想在制度建设上强行超车,完全不顾基础。戊戌变法时,皇帝和杨锐等四个小秘书(即“四小章京”)一下子推出了100多件诏书,很多是将日本文件翻译过来一发布,就算改革了。这样强行推动的体制改革,将张之洞、刘揆一等改革的操盘手都推到对立面上,怎么可能成功?这种浮躁心态愈演愈烈,到最后,清政府提出准备立宪期为9年,被一致批评为“假宪政”,只好改成6年,可日本宪政改革的准备期却是30年。
雪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应给群众以幻觉,不能忽视改革的难度。用几个口号调动起人们的激情很容易,但解决问题是另一回事。雪珥将国家比作一家公司,“革命”只能解决所有权的问题,不能解决经营权的问题,必须将经营权的问题和所有权的问题分开来看,不能一锅饭没煮熟,就把锅给砸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亨廷顿说过,变革的关键在于有效行使权力,但在晚清变革中,绅权却绑架了民权,导致皇权失控,其实变革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官绅却操控着实际的行政权,为一己之私,他们不惜上下拨弄,最终造成了大分裂。所以说“清亡于地方分离”,如果在变革时能加大集权,可能会少走弯路。不过,这个集权未必是中央集权,像日本变革,集权于议会,最终取得了成功。
清代的放权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中央让曾国藩他们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这就造成太平天国打完了,军队方面尾大不掉,大量财权下放后,中央手里的砝码严重不足。到了1909年的时候,中央一方面继续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权,把司法权、立法权从原来的省长、市长手中分割开,在各个省建立咨议局,选举产生一些地方领袖,来与地方官员形成制衡。各省咨议局成立之后,不断与地方衙门出现矛盾。而当时中央政府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议会。地方的长官也是人精啊,在大清的官场上混到总督巡抚,那都是人中龙凤,他们马上就看明白了,纷纷向议会靠拢,宪政的旗子举得比谁都高,民主的声音喊得比谁都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权力越来越分散。
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权威的保障,改革如果没有有力的行政资源去保障,改革措施如何推进?恰恰是晚清政府,用自己权威资源的放弃,来换取改革的推进,最后事与愿违。中央放了很多的权力给地方,最终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
于是雪珥得出一个结论:晚清的改革失败,不是太慢而是太快了,最终导致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