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烂的帝国
2011-12-29 00:00:00雪珥
看世界 2011年2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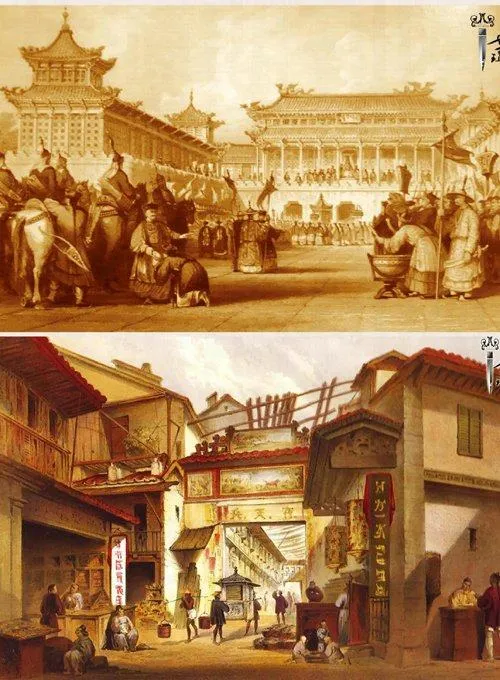
1821年(道光元年),叶恒澍被捕了。他绝对没想到,自己将打开一个新的时代。
这位小名“阿西”的广东人,有好几重身份。在官方看来,他是位候补干部,通过捐官获得了“州同”虚衔。实际上,他是一个小老板,在澳门有一艘船,经营渔业。
他的被捕,罪名是贩毒。根据两广总督阮元给中央的报告,案情其实并不复杂:“道光元年七月,叶船泊娘妈阁,偶遇来澳门贸易的相熟者福建人陈五。陈五告诉叶,有一批鸦片,每斤12银元,问要否买进。于是叶与同伙一起凑集1320银元,向陈五购入110斤,旋以1斤16元洋银的价格,售与一不知名的墟客(市场客商)。后被逮捕。”
但是,根据在华西方人的记载,叶恒澍的被捕,是因为杀人或者雇凶杀人。
最后,叶恒澍因贩毒而被判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到达配所后杖一百。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广东地方当局只字没有提及叶恒澍行凶杀人之事。
一个小小的私营老板兼候补干部,为什么能逃脱如此凶险的杀身之祸呢?
原来,叶恒澍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为澳葡当局的一个基金服务,而这个基金的唯一作用是向大清国的干部们行贿,以换得领导们对鸦片贸易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叶恒澍得以重罪轻判,正是因为他被审讯时,揭出了与杀人案无关的大量行贿细节。这张遍布广东官场的鸦片保护黑网,最后成为他的救命网——为换取他的沉默,广东当局只能重罪轻判。
利益纠葛
有关叶恒澍在专政机关内坦白从宽的记载,有很多版本。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其著作《中国总论》中记载,叶被捕后,受到了香山官员的刑讯逼供,为了报复,而将行贿基金的事抖了出来。马士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中说,叶恒澍认为把官员们拖进来可以为自己免罪。马士记载说,叶恒澍是向广州府检举揭发的;而现代历史学家格林堡则认为,叶是直接向中央揭发的,并且,中央还为此下派了工作组……
无论细节如何,西方史料都肯定了一点:叶恒澍的确是澳门行贿基金的权力掮客,负责行贿的具体运作。
这一基金,1年前(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由澳葡当局设立,对输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40银元,专款专用于对大清国领导干部的行贿。根据当时鸦片进口量推算,这一行贿基金每年可收10万银元(约7万两,折合如今1400万元人民币)。
葡萄牙人设立行贿基金,是因为大清国通过了一项新政策,进入澳门港的葡萄牙船在卸货前,必须接受大清官宪临场检查;如发现装有鸦片,则禁止该船一切贸易,斥其退去。这一加强管理的举措,被官员们当作了权力“寻租”的大好机会,而深谙大清国情的葡萄牙人,则与时俱进地设立了行贿基金,羊毛出在羊身上,以维持鸦片贸易的和谐局面。
大清政府之所以对葡萄牙商船进行临检,也是因为一起鸦片走私案。
那是更早前的1815年,以朱梅官为首的6名鸦片走私者在香山落网,香山办案人员开价8万银元(折合1120万元人民币),可以放人。但是,这6人要钱不要命,拒绝勾兑,于是被押送广州,在刑讯逼供后全部招认。
而在当时的两广总督蒋攸铦发给中央的报告中,对朱梅官贩毒的情节多所开脱:朱梅官等人持布匹与茶叶去澳门,与葡萄牙人安多利交易胡椒、海参等物。安多利尚欠朱梅官番银3480银元,又将返回葡萄牙,只好先向偶然在场的一位葡萄牙船长借款;船长手上并无现银,只有鸦片,朱梅官就收了120筒(每筒约二斤七八两)鸦片作为货款;朱梅官对销售鸦片还是心存顾虑,只将鸦片售给偶过小船上的不相识者,总共得款3840银元。
按照这一说法,朱梅官是受了欠债人的拖累,而且走私情节并不严重。其判决结果是:枷号一个月、而后发黑龙江充当苦差。这一事件称为“澳门事件”,其处置方式与之后的“叶恒澍事件”相仿。在大清官方的所有文件中,丝毫没有记载香山办案人员索要8万银元“放人费”的蛛丝马迹。
“澳门事件”后,两广总督蒋攸铦乘势而上,报请中央批准,开始对澳门的葡萄牙船只进行临检,催生了澳门的行贿基金,令广东地方官员们在与鸦片商人“勾兑”时获得了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
“叶恒澍事件”后,两广总督阮元则借势向广州商人的领袖、公行总商伍敦元下手。阮元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弹劾案,要求撤去伍敦元的三品顶戴,中央迅速批准了这一请示。
吊诡的是,在针对伍敦元的弹劾中,阮元只字未提“叶恒澍事件”。东印度公司的史料证明,“叶恒澍事件”正是弹劾伍敦元的直接原因,而在构成弹劾的一连串因果事件之中,还有一起“渥巴希号”事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渥巴希号”事件发生在“澳门事件”后2年(1817年)。“渥巴希号”是一艘美国商船,在广东海面受到疍民李奉广等袭击,这本来是一起纯粹的治安刑事案件。但是,李奉广等被官方抓捕归案后,却检举“渥巴希号”走私鸦片,这令案情变得复杂起来,“渥巴希号”也没能获得赔偿。借助这一事件,广东政府要求包括英国商船在内的所有外国商船,都必须接受临检,但遭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严厉拒绝,东印度公司为此甚至不惜调来了英国军舰“奥尔兰陀号”,进行武力威胁,最终广东当局被迫让步。
在这次事件中,伍敦元作为“保商”,向政府支付了巨额罚金,令“渥巴希号”摆脱了官司;而“案发地”澳门的“同知”(类似副市长)钟英被问责,险些丢官,因此与伍敦元结下梁子。根据马士的记载,1821年“叶恒澍事件”发生时,钟英已经升任广州知府,他试图运用此事报复伍敦元,推动总督阮元对伍敦元进行弹劾。
阮元在弹劾状中,将走私的责任都推给了伍敦元等商人,指控他们协助走私、“通同徇隐”:
“惟向来臣与监督衙门传谕各国大班事件俱发交洋行商人,照缮夷字,转为传谕;全藉该商等钦遵办理,敬布天朝法度,使知畏惧,不宜但以奉文转行了事。盖洋商(即洋行商人,垄断外贸的华商,并非外商)与夷人最为切近,夷船私带鸦片,即能瞒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瞒该商等之耳目。……乃频年以来,从未见洋商禀办一船,其为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显而易见。洋商内伍敦元系总商居首之人,责任尤专,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
在官方的强大压力下,1821年11月12日,以伍敦元为代表的公行商人,向外商们发出书面警告:停泊在黄埔水面上的鸦片走私船只必须即刻退出,否则公行只能提请官方强力介入;今后只有出具不装载鸦片的“甘结”(保证书),公行才能对外商的商船予以担保。而公行的担保,是外商在华进行贸易的通行证,没有担保,一切贸易都是非法的。
外商们开始还置若罔闻,公行商人却绝不敢再与官府玩游戏,他们主动向官方举报了涉及鸦片走私的4艘外籍商船,其中英国商船3艘、美国商船1艘。官方随即对这4艘船予以强制驱逐。4艘船被迫退到了当时被当作“外海”的伶仃洋,并在那里继续进行鸦片批发交易。
从这一天开始,中国的鸦片贸易进入了所谓的“伶仃洋时代”,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
行贿基金
行贿基金的建立,并非澳葡当局的创举,他们只是借鉴了大清国商人们的先进经验而已。
公行的商人,虽然是获得了帝国政府授权的外贸垄断者,得以坐享暴利,但是,在更为强大的公权力面前,他们无非也是官员们的“奶牛”而已。根据马士的记载,为了应对“潜规则”,行商们于1775年建立了一种秘密基金,每名公行商人都必须将自己利润的10%上缴,而从1780年开始,公行也开始向外商征收货物价值的3%作为“规礼”,纳入行贿基金,否则就不予担保。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外商们也只好乖乖就范。鸦片贸易因为极其丰厚的利润,成为这一行贿基金的主要资源之一。
这一行贿基金,如果仅仅应付官员们的私人需索,还是相当宽裕的。但是,从乾隆末期开始,为了应对天灾人祸,及皇室持续扩大的消费需求,中央不断向各地摊派临时费用。广东作为摊派的重点地区,官员们自然将负担转给了行商,而行商们则用行贿基金来应对这些“爱心奉献”的勒索。需索越重,鸦片贸易的重要性就越大。
鸦片的厚利与走私的泛滥,与官方公开的禁烟强度成正比。有学者统计,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大清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这60年间总共下发了45道严禁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谕旨、文告,旗帜不可不谓鲜明、态度不可不谓坚决,但是,鸦片的进口量及吸食人数却依然急剧攀升,禁令反而成为鸦片贸易和利润率的激素,而公权力因为既可毁灭鸦片贸易,也可为走私鸦片保驾护航,其身价大为提升,而且,不少官场中人也成为追逐鸦片时尚的瘾君子。林则徐曾痛切指出:“衙门中吸食最多……嗜烟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现任督抚,嗜烟者约占半数,若辈岂肯回扳石头压自脚,则阴持两端,模棱其辞,势所必然。”
负责查缉走私的水师巡船,成为鸦片走私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两广总督阮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坦陈,以缉私为名而从鸦片中分润的,上至副将、守备,下至普通士兵。拿获鸦片之后,他们要么“私卖分赃”,要么“得胜放纵”,到1826年,猫和老鼠在多年相互试探之后,终于达成了和谐同盟:走私者向缉私者每月缴纳36000两(折合如今720元人民币)买路钱,缉私者则“放私人口”,为走私护航。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缉私者一年可以获得相当于如今8640万人民币的保护费——这已经不是贿赂,而是分红了。
在猫鼠同盟中,知名度比较高的是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这位相当于广东海军(海警)司令员的高级军官,“专以护私渔利,与南洋船约,每万箱(鸦片)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报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紊,而鸦片(走私量)遂至四五万箱矣”。
福建的水师也不落后,“收受陋规,每船得洋银四百圆、六百圆不等”,水师收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缉私者的收入,居然有99%来自走私的分红,也难怪出现了“海口兵弁代藏毒品”的故事,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左近”。
马士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指出,随着大清政府对鸦片的禁令加强,“禁烟造成关税停征,但是却被贿赂代替,而贿赂居然三倍于关税。”这位深谙大清国情的汉学家说:“用不着说,帝国官吏是贪污的。非法贸易的扩张,之所以超过为公行垄断权所束缚的合法贸易而驾凌其上,正是广州和沿海口岸官吏们卖放的直接结果。一面使这种贸易扩张,而一面又把禁令列诸法典,以备不时之需。这对有关的官吏们是有经济上的好处的。”行贿基金的润滑作用十分显著,“一等交涉停当,各方面的眼睛就立即都闭起来了,甚至连在走私船只边上的缉私艇上官员也不例外。”
伶仃洋里
行贿这项工作,在1821年的“叶恒澍事件”之前,是公行华商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特权。但是,“叶恒澍事件”之后,鸦片走私船只都集中到了伶仃洋,行商们在鸦片走私中的中介作用大大下降,这导致了官商勾兑程序的巨大变化——外商们越过了华商,直接与官府开始勾兑,用马士的说法,这“大大提高了行贿的效率”。
马士将鸦片走私的“伶仃洋”时代,分为3段。第一阶段,从1821-1828年,伶仃洋逐渐形成鸦片集散中心,外商开始直接面向终端渠道批发鸦片,原先的中介者行商们日渐退出,鸦片的走私量从1811—1821年的年均4494箱,增加到1821—1828年的年均9708箱。
伶仃洋在当时算是“外海”,大清政府的公权力根本就管不到这里,而这里本是各国军舰、商船等待入关引水的锚泊之地,十分热闹。如今,成了鸦片集散地之后,从印度开来的满载鸦片的帆船,在这里将鸦片卸到大趸船上。大趸船其实就是海上的仓库和分装车间,鸦片在这里被包装分成小箱,然后卖给中国的零售商们。零售商将鸦片装入快艇,由50~70名水手操桨,行走如飞,根本不在乎缉私艇,而能迅速地将货送上陆地,供应各类瘾君子。
1828—1835年,是“伶仃洋”时代的第二阶段。在两广总督于1828年颁布了更为严格的禁烟令后,鸦片交易市场再度向北扩张,到了闽粤交界的南澳。这一时期,鸦片的走私进口量猛增到了年均18712箱。
自1835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39年,伶仃洋时代进入全盛时期。精简了行商这一中间环节后,外商们的利润大大提升。鸦片走私大干快上,年均进口量达到了30000箱。
在“伶仃洋时代”,在广州经商的外商们,因为原先的“硬通货”鸦片被禁,无法以货易货,只能将在伶仃洋销售鸦片后的白银,带到广州采购回程的中国商品,多了道程序。但这一来,他们在广州的交易就成了纯粹的采购,而没有把柄可抓。一个“干净”的商人,对一个期待“不干净”的官员来说,就是一笔损失——广州的官员们少了巨大的灰色收入。同时,因为都在外海进行交易,并与中国的消费终端日渐实现了无缝对接,外商们开始不再将大清国的缉私干部当干部看了,这大大激怒了这批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的沦丧,令广东的官员们开始真的痛恨起鸦片贸易了,并试图惩罚那些破坏潜规则的人。根据马士的记载,广东官员真的缉私了,缉私艇与走私者之间不断爆发武装冲突。这一切,令主张禁烟的体制内人物如林则徐等,获得了极好的动手时机。正为自己能独享鸦片走私暴利而高兴的外商们,并没有看到,一场疾风暴雨正在广东上空酝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