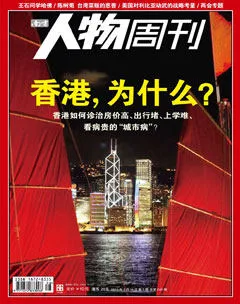来信
国人渐已醒
虎妈蔡美儿引起的争议纷纷,折射的不只是培养孩子的教育方式问题,还可能是教育儿女之外的那些延伸思考。
虎妈蔡美儿和她的“我在美国做妈妈”,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成功的商业行销案例。现实中的虎妈,并非大家所说的那么严厉无情,真正的虎妈也是慈母,和天底下所有母亲一样。
在独生子女的国度,如何培养孩子的书籍从来不欠缺市场,尤其是稍微带有美国和其他国家教育符号的书籍,几乎都是一再出版的热销书,这种趋之若鹜,反映了人们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机制的羡慕和向往。
人们对虎妈现象没有一窝蜂,而是多元思考,这是一种进步。
习惯于单一崇拜的国人,开始有更加独立的思辨和选择,令人欣喜。
曾有首粤语歌唱道:国人渐已醒!
杨锦麟(凤凰卫视)
《最富争议的虎妈》
虎妈只是美国千万家庭中的一个普通的个体,却被无限地放大,上升到中美的教育对比、中国威胁论,甚至还有人拿《国际学生测评》来证明。但是这个测评只是在中学范围内,为什么不比比我们有多少个诺贝尔奖?多少真正的科研成果?看看《生活大爆炸》就一切了然,是什么使我们这些优秀的青少年不再优秀……
——我是真正的77(新浪网友)
也许您不知道,天王巨星迈克尔•杰克逊有一个“虎爸”,别的孩子在玩时,他则在“虎爸”的淫威之下练声、练舞,虽然最后成就了一代天王,但是面对记者回忆起童年时,天王泪如雨下,说自己没有童年,很不幸。
——西亳教育(新浪网友)
虎妈的教育方式还是有一定道理,在孩子还不会自己选择时,父母必须帮他们选择和设计人生。那种放羊式、任其自由发展的做法纯粹是扯淡。即以学乐器为例,枯燥技法几乎没有孩子感兴趣,贝多芬也是在父亲棍棒下练成的,更不用说郎朗之类。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必须有这样一个过程,你能放任吗?
——abuabua(新浪网友)
我有无数的同学小时候都被逼着学钢琴、小提琴,这些同学百分之百又都在中考的时候放弃了;但是现在工作以后,这些同学又都在跟我说,“要是我父母再逼我狠点,我在坚持下来多好呀”。这些同学现在又吭哧吭哧地自己报班,重新学起了。
——黎址煵(新浪网友)
美国“考察”的收获
我在旧金山机场等候飞往北京的航班。一群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位二话不说,把我放在椅子上的行李拿开,坐了下来。他们手上拿着绿皮的中国公务护照。那副神情也是某种我们见惯了的公务员类型:老子做什么事情不需要跟你解释。
他们旁若无人地大声说话,从“考察”观感到某款名表的价格,如此种种。根据这帮人谈话的内容、语气和口音判断,他们是从中国某省来美国“考察”的政府官员。
候机的时候,机场工作人员推着一车中华烟过了登机口,然后将这些香烟一袋袋分好。我猜想:这些香烟估计是我身旁这帮“考察”官员的。据说现在流行在国外买国内品牌的烟酒,价钱便宜,而且品质有保证。
上了飞机,这帮官员坐在我的周围。我放完行李,好不容易把塞得满满的行李舱关上,这时,一位官员一句客气话没有,让我把舱门打开,他要拿东西。于是我把我的东西拿出来,让他去翻他的行李。等他拿了自己的东西,“啪”一声就把舱门关上了,完全不管我手里还拿着东西在等着。
航班起飞后,一位官员开始跟坐在我旁边的华侨老太太聊天。他对老太太说,你应该回中国了,中国现在发展得比美国好。他所说的“好”有几点,比如说中国的高楼比美国多,美国许多地方的房子很矮很旧……
有意思的是,这位华侨老太太等那位官员打瞌睡的时候,转过身来疑惑地问我:他(那位官员)说中国现在发展得比美国好,你觉得呢?我有些苦笑地说,我对“发展”的理解和他不一样。然后,我说了我的看法。(此处省略10000字)老太太对我说,我跟你的看法是一样的。
航班飞行了十多个小时之后,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果然如我所料,这些官员们每个人拎着一袋中华烟下了飞机,这是他们“考察”美国的一大收获。
本刊记者卫毅
制造愚蠢是最大的恶
2010年末,我“混”进了江苏南京一个自称为“自愿连锁经营业”的“高级”传销组织。里面的人用“善意的谎言”(其行业用语)骗亲人与朋友来“看行业”(他们的行话)。在我“看行业”的5天中,所受的待遇和所见的情形,与以往我所了解的传销并不相同——传销人员或以家庭为单位,或三两人合租,每日伙食也都不错——所以称其为“高级传销”。但传销无论挂上何种招牌,升级为第几代,终究改变不了其控制人思想的本质。
第一天,被领去见“在这里认识的一位好朋友”(每次与人见面,带我来的人第一句话一定是它)。对方是个姑娘,干涩的寒暄让我不得不挤点笑容给她,纸笔备好,姑娘开始给我描绘“五级三阶制”,并像念诵“小九九”一样唰唰地写下一套套计算公式。简要地说就是:一次性投资69800元,发展自己3个下线链条,两到三年后能赚10400000元。姑娘问我:“帅哥,你觉得我们像做什么的?”我笑着反问:“你说呢?”“传销!不,我们这个行业绝对不是传销!而是国家多年前从新加坡引进的,由政府扶持的全新行业……”
接下来的3天,每天4到5个人,一人一小时。路数都一样:倒上白开水,寒暄,询问,开始“宣讲”。起初我一直持抗拒和反驳的态度,甚至请对方“把普通话说清楚些”。但我发现,这样下去,接下来的人不会讲新的东西,只是再将前者重复过的内容变换方式重说一遍。为了搞清楚内情,我做了“顺毛驴”,还时不时地掐着自己大腿谄媚说:“我觉得吧,你们这个行业有点意思,有发展,有钱途!一千多万哪!后面那零我都要数好一会儿呢!”对方不是哈哈笑,就是夸我“聪明”,说我悟性高。
在江西上饶传销组织卧底了23天的作家慕容雪村说过:为什么一个愚蠢的把戏能欺骗如此多的人?为什么传销者竟敢明目张胆地行骗?为什么传销总打不绝,甚至连打击本身也成为了他们行骗的证据。
这是一片崇拜仪式感的土地,充斥着急功近利的文化,和缺乏常识但又甘于听话的人。慕容雪村对我说:世界上最大的恶是制造愚蠢。其实,最大的恶是教人听话地不思考。
本刊记者 王年华
那个充满愧疚的老人
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起袁迪贵了。
在乐清采访“钱云会死亡事件”时,我想找人来谈钱云会北京上访的那段生活,才知道有这么个人。
村民说,这个人是温州永嘉人,年龄不小了,因为在北京常年上访,各方面都熟,人热心,钱云会到北京上访,就找他,吃住都很帮忙。
打电话给袁,没想到,老人知道很多情况:钱云会在北京的上访、困境、被抓,以及王立权的逃亡,他都清楚。
甚至连钱云会死亡当日中午,王立权拿下了钱云会的手表,手表能录音录像他都一清二楚。
钱死亡当天,老人还热心地帮村民联系了媒体,让记者前去报道。
那么 ,老人为何这么热心,是否从村民请律师费用中收好处了?电话中,我直接这么问了。
没想到,老人也很坦率:是的,我拿了两万元,但我帮他找人复印、邮寄材料这些,都要花钱的。
但是,老人说,得知钱云会的死讯后,他的愧疚产生了。因为,2008年,钱云会在他介绍住的地方被抓,后来又因为筹律师费卖宅基地而被判刑。现在,刚出狱不久,又不明不白地死了,他很难过。
电话里,我听到老人有一些停顿。
他说,他也比较担心自己的安全,手机都不敢随便接听,但为了钱云会的死因,他也没办法(寨桥村上访的人在北京没什么熟人),只能帮忙。他说,要邮寄一份比较齐全的钱云会上访材料,我把地址告诉了他。
由于截稿的缘故,我没能去北京见这老人,只是将他的联系方式告诉一位可靠的同行,让其有空去见见。
结果,1月8日那天,同行打来电话,说约了老人见面,在寒风中一等几小时,不见老人踪迹。据说是去取40万的律师费发票回来给他看,哪想到,一去不返,“打了很多个电话,都没人接”。
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老人去了哪里呢?很快,“袁迪贵失踪”的消息在网上开始疯转。
半个月后,传出消息,他被浙江警方带回乐清市拘留所了。
两个月过去了,这位充满愧疚的老人,你在看守所过得还好吗?
本刊记者 陈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