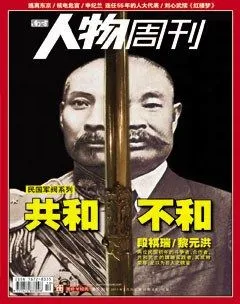观察
“作家工资”该涨了吗?
“事业人员”跟“公务人员”毕竟是表亲,总体上是利益均沾的,十亿中国人可以写出比这封信更加动人的诉苦信来
何三畏
3月17日《南方周末》评论版,某省作家协会一位副主席来信,抱怨“专业作家”的工资2006年以来就几乎没有涨过了,而作协的“行政人员”,倒是一涨再涨,形成了不小的差距:“一个五六十岁,有十多年正高职称的专业作家,比刚提拔的副厅级干部少一千五六百元,甚至比二三十岁的年轻处级干部少六七百元。”
在这个“收入分配不公”已为官方所坦承的年代,这算一个事儿吗?
算,也不算。
放在“收入分配不公”的大背景下看,这不算什么。“收入分配不公”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两方面的含意。在经济制度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三十年走过了西方三百年的道路”,从“公有制”的起点上,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获利者,同时,也造成了国家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巨大”的现实。来信中,“专业作家”对比是他们身边的目标,即管理他们的行政人员。这么对比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是把眼光向上,再向上,比一比,那就是另外一种气象了。
在政治或者政策方面,我国规定了工资和福利跟一个人和政权或政府的远近关系相匹配的原则。服务于党政部门的“正式员工”,都叫公务员。公务员居于核心利益保护层。他们的收入和福利,和其他行业的劳动者比,固然悬殊,在系统内部,高级公务员和普通公务员之间,也悬殊。“专业作家”来信所说的情况,应属后者。
从前,中国的“专业作家”差不多等同于公务员。而且用行政的方式给作家评级,然后按级拿工资,“一级作家的工资跟局级干部同档”。但来信所说“异动”是怎么发生的?因为:“专业作家”被归入了“事业单位”,而行政人员则靠向了“公务员”。就这一句话,已经说明了一切:事业单位的工资福利,跟公务单位不一样,这是国家政策。不仅现在不一样,等你退休了,养老待遇还不一样,等你死了的最后一次福利也不一样。这等于是说,“专业作家”在“行政人员”面前,是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样的情况,落到具体的个人身上,当然“算一个事儿”,而且是大事。
但是,“事业人员”跟“公务人员”毕竟是表亲,总体上是利益均沾的,比起绝大部分从来没有见到过政府如何分配利益的社会群体来,那是“幸运”多了。假使每一个人都能像“专业作家”这样善于表达自己的委屈,也许会有十亿中国人可以写出比这封信更加动人的诉苦信来。所以,“专业作家”倾诉的这点事,又不算啥。
我觉得,作为“专业作家”,既要会表达,也要“会想”。他们应该知道,在人类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作家领一份公务员似的工资,只是相当于流星在天空划过一样短暂而偶然的事情!你怎么能幻想永远留住这样的“偶然所得”?虽然,现在也还有像郭敬明这样的年轻作家和“作家体制”两情相悦,也还会有“新鲜血液”不断补充进去成为“专业作家”,但是,新一代作家绝大部分在体制外,只靠着常常因为市场以外的原因而不能发表和出版的“不成熟市场”的收入生存。
不用说,你的愁苦来自于政策的纠结。应该说,把专业作家归入“事业人员”,算不上什么改革。也不知道这是地方的“土政策”,还是全国的一刀切。但似乎国家并没有改变现有“作家制度”、使它向市场接轨的意思。所以,退一步说,今天的“专业作家”暂时还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担忧。即便国家下了决心要改革,无数事实证明,也一定会“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不会把你一手放归市场,断然不给包养的。
我理解把你们“降格”为事业人员,至多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何况,来信提到,2009年国务院有规定,事业单位从2010年起实行“绩效工资”。按政策推理,你们期盼的“2011年,该轮到我们这群作家了”的(涨工资的)愿望,是应该实现的。看看,国家多么爱你们呀。
但这里同时也透露了一个问题:相对“应该感谢”的阶层也发出抱怨。这是因为工资福利没有法制化和公开化,而是被权力化和私密化,以致它成了一个社会敏感区,并且还是在加强之中的新闻禁区,从公开的资料中,查不到任何级别的公务和事业人员的账面收入。虽说改革就是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但对于不公开、不讨论的利益,谁都找不到合理的期待,从而只会导致社会心理失衡而不是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