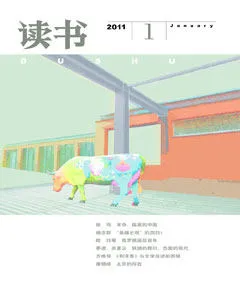环境成就
梁天监七年(五○八),萧梁取代萧齐天下后的第六个年头,建康光宅寺的法云和尚读到了一篇题为《神灭论》的文章。
作者是中书郎范缜。法云对他早有耳闻。这位中书郎的故事,简化到骨架就是,才华横溢的没落贵族,个性横冲直撞,自认为有卿相之才,好发危言高论。因为太骄傲,“自我”便与环境相互纠缠折磨,身边喜欢和支持他的士人朋友非常少。好在南朝是“文化大朝”,貌似古怪的文化精英依旧不少,“尚通脱”的晋人之美仍然延续着。范缜并没有被完全埋没。还在齐代的时候,他先出仕任齐宁蛮主簿,积功升迁为尚书殿中郎。永明年间,南北王朝互访通好,范缜被选派为外交使臣。他的机智敏捷在北方国家中留下卓著名声。
不过,真正让范缜闻名南方朝野的,是齐永明七年(四八九)发生在竟陵王萧子良鸡笼山西邸中的一场论战。
从北方回来后,范缜做了萧子良的宾客。萧子良是齐武帝的次子,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极富政治才干,且清雅高尚、品性淳厚。据说,他与齐朝太子有着共同的爱好,关系非常友好。他对帝位似乎没什么兴趣,除了帮忙处理政务外,闲时便以文会友。大批文人聚集在萧子良鸡笼山的西邸之中,不少新鲜华美的诗词文章从这里流出。萧子良既有实践才能又肯尊重文化的骄傲,士大夫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大人物,有些人甚至天真地在私下为他做着篡夺皇位的准备。
西邸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沙龙,范缜却颇为寂寞。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萧子良与太子的那个共同爱好——佛教。西邸之中,佛教气氛浓厚,佛法讲论成为时尚。范缜常常目睹着身为当朝宰辅的萧子良在家宅举办斋戒活动,与许多朝臣、名僧一起礼佛,甚至亲自为僧侣端茶递饭。范缜是学儒出身,对佛教既不信仰,也不同情。以他的性格作风,自然公开地大唱反调。终于,萧子良决定,找范缜来辩论,试图用理论征服这个在西邸文化圈中特立独行的人。
《梁书·范缜传》记录了这段辩论:“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不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大概,范缜还是喜欢萧子良的,虽然彼此意见相反,但一个比喻,把自己比到了“粪溷之侧”,也算是谦卑得可以了。但问题是,萧子良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什么“茵席之花”,因为,他的人生并不由于生在帝王家而更幸福。他看惯了皇族家庭的自相残杀,也看惯了臣子们的见风使舵。
萧子良的祖父萧道成是通过“禅让”得到帝位的。这种最古老的称帝方式,在当时往往意味着大量地屠戮异己与刻薄的武力胁迫。禅位的那天,十一岁的顺帝刘准躲在一个佛堂里瑟瑟发抖,萧道成率军入宫,把小皇帝揪了出来。孩子哭泣不止,官员王敬则对他说:“今天不是要杀你,只是要你搬个家。你应该知道,当年你们刘家也是这么对付司马家的。”刘准流泪道:“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一个月以后,已经“禅位”的刘准终于还是被萧道成杀了。
萧道成的皇帝也只做了不到三年。他死后,萧道成的长子、萧子良的父亲萧赜继位,是为齐武帝。
史书上说,齐武帝是“太平天子”。他在位期间,政权也算平稳,但皇室仍然纷争不断。太子萧长懋一直忌惮着深得父亲宠爱的第四子萧子响。所以,当武帝对萧子响有所猜忌时,太子便立刻乘机谋杀了他(执行谋杀的人便是萧子良的叔公、萧衍的父亲萧顺之)。不过,在杀了亲弟弟后,萧长懋没等登基就一命归西了。
皇孙萧昭业顺理成章地继了帝位。登基后,他重重赏赐了一个叫做“杨婆”的女巫,这是为了感谢她用法术“咒杀”了祖父齐武帝,让自己可以尽快地登上皇位。
萧昭业皇帝没做多久,又被自己的叔公萧鸾杀了。从此,皇权握在了旁系手中。
由于是旁系,登基后的明帝萧鸾一个接一个地杀了武帝的十二个兄弟、十七个儿子,以及大部分孙子,还有一些功臣宿将。杀人大部分是在夜间进行,基本程序是:士兵围宅、砸窗,入宅杀人,顺便抄没家产。明帝养成了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总在杀人前夜焚香祷告、流泪哭泣。每当这个时候,身边的人便知道明天定会有大规模的流血。临终前,他这样教导自己的太子:“当年,萧昭业猜忌我,想杀了我,但他优柔寡断,反被我杀了;这就是前车之鉴。谨记:做事不可在人后!”
被如此训诫的孩子,便是萧齐最后一代皇帝——荒唐透顶的萧宝卷。他完全不具备父亲的政治头脑,却牢记着父亲死前“做事不可在人后”的遗训,并将它贯彻到底:猜忌一动,即刻斩杀,不做考虑,不做调查。
再说回萧子良。自从太子萧长懋死后,身为次子的萧子良知道自己的处境微妙,便安守本分,小心过活。然而,身边的一些宾客却被太子亡故的有利形势弄昏了头。王融,东晋宰相王导的后代,出身高贵,学问又出众,在萧子良的所有心腹中风头最健。他私下为萧子良准备好了登基诏书。但宾客中像这样实际参与篡位行动的人似乎很少,有些人仅从道义上表示支持,有些人甚至持反对意见。从史书上看,似乎连萧子良本人也被蒙在鼓里,只有以王融为首的一个小集团在积极活动。政变的准备相当不足,所以,当萧昭业与西昌侯萧鸾率甲士入宫时,矫诏篡位的活动顷刻瓦解了。新皇帝继位后,王融就被诛杀了,凡预此事的官员也都陆续被处刑。对于王融擅行废立之事,萧子良的叔叔、后来的梁国皇帝萧衍料定了它的失败。他深知,凡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成就帝业者,只能是那些真正能济世定乾坤的人。王融,还不够格。志大才疏的宾客给萧子良惹了大麻烦。从此,他不得不在新皇帝的猜忌中艰难度日。
王朝的权势斗争异常残酷,官宦生涯危如累卵。在乱世中,礼教信仰变得可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教导越发显出不切实际。人们早已发现:个人的道德行为与家族的福祉昌延是两码事。祖先的行为并不能决定家族的命运,同样,家族的现在也未必掌握着子孙的未来。当残酷的命运降临时,一切美德——仁爱、正义、礼让、诚信,都无济于事。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的人往往生保荣贵、子孙繁炽。
“一种无为和中立的态度于是成了最好的全身之术”,“《老子》、《庄子》之脱俗的特点和古代巫术的宗教背景相脱离,并转而成为士大夫的语言”(许理和语)。崇拜个体心灵自由生长的玄学出现了。玄学讨论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名士们都说要“弃彼任我”,也就是反对繁琐礼教、追求自然,拥抱自由自在的思想境界与生活方式。他们在理论中淋漓尽致地发挥着老庄的逍遥之道。但是,名士的实际生活被人诟病不少。他们中的一些人“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祖尚虚浮”,“以遗事为高”;也有些人裸体、酗酒、居丧淫乱,过着“任情率性”、“恣欲而为”的生活;还有些人提倡“心斋”、“坐忘”,“堕肢体”、“黜聪明”,把自己变成“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活死人。冯友兰说,玄学名士活得风流浪漫,过着艺术家的日子。不过,放下政治责任,放荡日常行为,放弃思想智慧,这些行为似乎并未表明他们找到了真正的乐园,也容易使自由流于表面形式。
与玄学不同,从心性到修行、再到规范修行的僧团制度,外来的佛教拥有自成一家的关于解脱的理论与实践纲领。它为每个个人找到对个体存在问题的回答,它以一种独特的对于存在本质的观点来证明同情的伦理,它唤起了个性的宗教感觉及愿望并试图去满足它们。所有这些,对于心灵渐趋空虚的华夏民族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士大夫们在“无情世界”中找到了足以慰藉的“感情”。
范缜说“生如一树花”,把历史与现实都推给了“不知其所以然”但“知其不可奈何”的偶然性,当此之时,萧子良静默了。魏晋以来的名士辩论中,沉默不言就等同于理屈词穷、竖起降幡了。根据史书的记载,萧子良后来把辩论形式从“单挑”变成了“围攻”。他发动了许多僧人与文士,大家软硬兼施,对范缜一面口诛笔伐,一面诱之以高官厚禄。这些不但没有奏效,反倒令范缜更加出名。不过,范缜貌似玄学的说法,听起来是无伤大雅、有本有源的主张。人们还没有看到范缜为“排佛”所做的颠覆性论证。
当时,“排佛”的依据无非三类:
其一,依古。代表言论:夷夏有别。
这种观念有着以文明对抗野蛮的合理性。然而,当士大夫们意识到佛教顶多算是异质而绝非野蛮时,“胡人鄙教”的说法不再能维持它的说服力。文化多元本就应该是理性社会的常态,用夷夏有别来反对佛教,虽然合乎传统,却不能真正地收拾人心。
其二,依政。代表言论:无益国治。
这种说法一到佛教鼎盛时,便会被声色俱厉地提出来。公元四○二年,三吴大饥,户口减半。加上与北方的兵事不断,全国粮食严重不足。情况非常糟糕,一些富户都粒米束薪,大家只好穿着精美的丝绸,怀里揣着黄金珠玉,然后关起门来等待慢慢被饿死。就在这一年,摄政者连发了两道有关佛教的政令:第一,沙汰僧众;第二,组织臣子们讨论“沙门应不应敬王者”。这表明了统治者对佛教的两个清晰认知:第一,佛教与国家争夺社会资源;第二,僧伽是王教中的“飞地”,滋生着不安定因素。这两个认知导致了限佛的政令。类似的事件还有:约公元三三五年,北方后赵石虎朝境内“民多奉佛,营造寺院,相竞出家”,王度上书要求限佛;公元三四○年,代替王氏家族主导朝政的庾氏集团挑起反对僧伽权力的争斗;公元三八九年,因孝武帝宠幸道子、荒废朝政、亲昵尼僧,将军许荣上书说“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并斥责僧人“侵渔百姓,取财为惠”。这些指责都是有事实根据的,而在任何情况下,佛教徒的反驳论调都基本一样:“神道助教”,佛教可令统治者“坐致太平”。事实上,在王权与教权关系的实践中,主导权其实始终在王室方面,统治者完全可以径直行使政治权力来主宰佛教僧团的沉浮,但“排佛”者显然还需要在理论上做更深刻的建设,也就是要争取从教义上驳倒佛教。
其三,依教。代表言论:神灭论。
公元四○一年,桓氏家族权势盛极一时。这个南迁世族的第五代子孙桓玄刚刚任职荆、江二州刺史并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及扬、豫等八郡军事。他写信给庐山慧远,希望慧远罢道还俗。根据史料推测,桓玄很可能还随信附上了一些关于佛教的疑题。那些质疑并不纠缠于佛教存在的“功利性”问题,而是围绕纯学理的主题展开。论议有很多细节,其中干系最为重大的论点就是“神灭论”。
桓玄写道:“根据佛法,人的身体是神的居所,身体在本质上是由地、水、火、风四要素构成,伤害它无损于神,那么,杀生不过是在消灭天地间的水火而已,佛经怎么能以杀生为重罪呢?”桓玄试图说明神不灭与佛教戒律的自相矛盾,攻击矛头直指“轮回报应论”。在当时中国知识与信仰的世界中,“轮回报应论”实乃佛教理论的核心。桓玄此举无异于试图动摇整个中国佛教理论大厦。慧远做了比较详细的回信。他反复解释“神”的存在以及它与情识的内在关系,并论证“神”就是轮回报应乃至涅解脱的主体。
事实上,公元五六世纪,“精神”的性质问题是教内教外争论的焦点与思辨的核心,围绕神灭与不灭主题的辩论不断。在这些辩论中,中国古来的灵魂观与气论影响着争辩的双方。神不灭论者与神灭论者都把超验的“精细之气”作为“神”的本质,也都利用薪与火来解释形神关系。这种比喻常常令争辩双方落入形与神这两种具体物质是否共生的思考界限之内。
不满于以往争论在思想水平上的简单重复,再加上与萧子良辩论事件的刺激,范缜觉得有话要说。他专门撰写了《神灭论》,用刃利关系来喻证形神关系。刀刃是质,锋利则是刀刃派生出来的用;同样,形体是质,精神则是形体之用。神的性质被限定为身体的功能与属性,而下一步要回答的问题是“何以身体能派生出精神之用”。形神关系自此就可以被放置在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的新视野中来研究。从当时的科学水平来讲,范缜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更何况,《神灭论》的最终目的仍是功利主义的,它在结尾中自问道:知道神灭理论又有什么用呢?范缜的回答是:在胡汉二分天下的局势中,它的最大“利用”就是富国强兵。此处,范缜无疑在借《神灭论》向自己的皇帝呼吁,要求他在文化乃至国家政策上表现出理智。
好文章流传得很快,在此期间,建康的龙椅也换了主人。公元五○二年,萧子良的叔叔萧衍即帝位于建康,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梁武帝是一个佛教徒。他在称帝的两年后,正式公布了自己的信仰,并在公布的诏书中阐明了理由:儒、道“止是世间之善”,而佛教“能使众生出三界之苦,入无为之胜路”。这一宣告背后所隐藏的世界观完全是佛教的。以“能否出三界之苦”为真、善的标准,自然认为佛教是比儒、道更为优越的信仰。舍“邪外”之儒道,事“正内”之佛教后,梁武帝还要求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诫,有事佛精苦者,辄加以菩萨之号”,并邀请高僧为六宫王姬们授戒。一些高僧大德成了梁武帝的“家僧”。文章开头所说的法云法师便是其中极受皇帝器重的一个。他不仅获得了条件优厚的奉养,而且长年出入皇宫,协助武帝召开各种佛教会议以及编制佛教文献。现在,文章终于流入了法云手里。
法云将《神灭论》报告给了梁武帝。进呈之书是这样写的:“中书郎范缜著《神灭论》,群僚未详其理,先以奏闻。”梁武帝与范缜在信仰上的对立公开化很快成为朝野的焦点。对范缜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形势。让我们来看看北方中国的类似事件。北魏在太武帝时期(四二四——四五二),负责国政的宰相崔浩对佛教极为反感,他抱怨说,佛教受到北魏朝廷的过分保护,逐渐堕落,寺院成为收纳匪徒、逃脱役税以及流民的黑窝。于是,他向太武帝推荐了道士寇谦之,希望把皇帝培养成道教徒。崔浩成功了,太武帝果然开始讨厌佛教。其实,僧团中出现各种腐化堕落的现象也存在于南方王朝中。对此,佛教徒的解释是:正如不可因为少数荒唐的儒生而废除六经一样,你们也不能由于局部有恶行的僧人而放弃整个佛教。基本上,这种辩解在南方是奏效的,统治者最为严厉的处理措施也仅仅是“沙汰僧众”。但是,在北方,不检点的僧人带来了整个僧伽的厄运。公元四四六年,北魏的军队为镇压一次流民叛乱,进入佛寺,发现僧侣不仅饮酒,而且还私藏武器。太武帝以此为契机,出兵镇压佛教。长安的僧侣被屠杀殆尽,佛典、佛像、寺院几乎全部毁灭。太武帝被学者称为“魔性之人”,仿佛他是一个极端的特例。但事实上,在整个北方王朝中,皇帝通常都是保守型专制主义的化身。即便在崇信佛教的帝王治下,类似沙门应否礼敬君王的辩论也是绝对不允许的,而在南方,这种辩论发生过很多次,僧人甚至争取到了实际的胜利。对于北方僧人来说,南方那种自由的义理讨论可能很危险。
现在,范缜的命运取决于梁武帝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历史记载,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长寿皇帝之一,也是最为勤政、最为俭朴的皇帝之一。他在位的四十八年,被史家评价为魏晋以来最好的时代。萧衍热衷书法与围棋,能诌几句诗,尤其喜爱读书。战争时,武帝总要求城平之日,先收图籍。南面称孤后,他立即颁布征书令,求天下遗书。大凡对文字典籍心存敬重的人,多半也不会愿意在历史中留下“钳制文化”的恶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位知识渊博、具有高超哲学修养的皇帝为自己的臣民创造了“公开地运用自己理性”的开明专制主义。“朕乃君王,故应为所欲为”这句话不适合描述梁武帝。
关于《神灭论》的敕旨很快下达了。皇帝希望朝野上下能就“无佛”问题设立正反双方(“设宾主”),大家一齐“标宗旨”、“辩短长”,如果“有佛”之义踬顿,那么“神灭”之论自行。他认为,一场哲学辩论远比只有一种思想或观点发出声音来得合理。也许,正是这封敕旨令范缜轰动了萧梁朝野:详细阅读《神灭论》并对其展开驳斥的,有连同僧人与王公大臣在内的六十二名知识精英。这个数字可能更大,因为范缜自傲地宣称他“辩摧众口,日服千人”。无人能使范缜在理论上折服,他的论敌曹思文甚至对梁武帝坦陈自己“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虽然《神灭论》未必完美,梁武帝最终也没有改变对佛教的信心,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记住,那是一场没有政治压力的自由辩论。
《弘明集》中保存了范缜与梁武帝等人辩论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思想成果。书的作者僧佑经历齐、梁两代,与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亦师亦友。他的老师便是宋、齐两代僧主、律学名师法颖和尚。齐、梁两朝的上位者对师出名门的僧佑深相礼遇,凡有僧事硕疑,都交给他审察决定。在宫廷及贵族的支持下,僧佑还有机会施展艺术与工程方面的出色才华。他搜集歌呗、法乐、梵舞、造像、雕刻的文献资料,制成《法苑集》;亲自设计规划并监造各种大型佛像,其中有当时被誉为“东方第一”的铜质佛像,也有雕刻精美的剡县(今浙江嵊州)五丈坐佛与十丈立佛,还有摄山龛石雕千佛像等等;主持营造道场的工程,其中包括建初寺和定林寺(中国历史上最古的佛教图书馆便开设在这两个寺院之中)。博学多才的僧佑在朝廷权贵中吸引了许多崇拜者。南朝的一大特色是僧尼参政,但僧佑却既不喜欢追逐功名,也不愿意攫取权力。他说:“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松清密;以讲习闲时,僧事余日,广讯众典,披览为页;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略。”(僧佑:《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二《释僧佑法集总目录序》)显然,佛学讲习与著述是僧佑压倒其他一切兴趣的事务,也是他给自己选定的人生道路。在环春接冬的讲肆活动与平静精严的山林僧事之余,僧佑撰写了两部律学著作:《萨婆多部记》与《十诵义记》。著作亡佚不存,我们无法弄清法师那些律学耕耘的本来面目。对于后世来说,僧佑一生的标志还是他的佛教文史著作《出三藏记集》与《弘明集》。
在《弘明集》这本书里,僧佑关注了五百年来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界乃至社会的突出问题。大量三教融合与交汇的材料说明了当时南朝社会的思想繁荣。僧佑的本意是“弘道护教”,但他在《弘明集》中纪录了不同的思想之声,有儒家的攻难,也有道教的批评。如前所述,由于才能和爱好的缘故,梁武帝提供了一种积极的从单一、同质的文明形态中走出来的政治环境与人文氛围。学术思想的自由辩论杜绝了思想史上的荒芜与静止的状态。如同先秦的百家争鸣,各种思想都在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强调自身的优越性。不同思想文化在争论中前进是这个时代的一大成就,而内典与外书兼收、方内与方外并置的《弘明集》,就是这一成就的明证。它超出了单纯的宗教意义而具有思想史的研究价值。应该说,环境成就了僧佑其人,也成就了《弘明集》这本书。
(《弘明集读本》,彭自强校注,华夏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