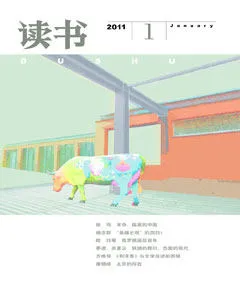从斯图尔特.休斯说到彼特.盖伊
虽然休斯的著作只有一本中译本——《欧洲现代史:一九一四——一九八○》(陈少衡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版),但是有识之士在今天还是会不时想起这位故人休斯。也就在二○○五、二○○六那两年,中国出版界还接连出版了五本彼特·盖伊的著作,即《启蒙时代》、《魏玛文化》、《历史学家三堂小说课》、《弗洛伊德传》和《施尼兹勒的世纪》。彼特·盖伊与斯图尔特·休斯在学术上有很近的亲缘关系,都是从政治学转向历史学研究,都对欧洲追求整体性的传统学术保持很深感情,最主要的他们都反对单纯、偏颇的实证主义历史学,他俩的历史哲学观极其相似。休斯的政治观、学术上对近代德国思想关心,是在“二战”结束后、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在战略情报局(OSS)与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朗茨·诺伊曼共事时,受到诺伊曼的影响;而盖伊则更是弗朗茨·诺伊曼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政治学时的直系弟子。刚买到盖伊的五种新书(中译本)时,我曾想动手写篇介绍彼特·盖伊的短文,但是,饕餮的阅读欲望不断夺去了我的时间,以后几乎完全忘记了这个念头。去年十月中旬,奥巴马总统因为呼吁核裁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让我重新想起要写介绍休斯的短文来——因为休斯人生的起伏与其参与反核武器政治运动有关。当然,提起休斯,也总要联想起盖伊,因为他俩在学术上有亲缘关系——都是身在北美、心怀欧洲的历史学家。
说起来,休斯是个长年涉足政治活动的、就像今天中国人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休斯出身于政治家家庭,父亲查尔斯·埃文·休斯,曾任纽约州州长,还在胡佛总统时代担任过首席大法官。进布朗大学后。他就对欧洲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二战”爆发前,他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博士论文题目是《法国第三帝政时期的经济》,所以,战争爆发前五年逗留在欧洲搜集史料。“二战”爆发,他才返回美国。珍珠港事件后,休斯加入美国陆军,最初的军衔是少尉,因为精通德语、法语,分配在军队情报部门工作,参加过解放法国的战役。在军队内,休斯一直被认为思想左倾,但是因为工作努力,成绩卓著,接连得到嘉奖,一九四六年复员前已经晋升为中校。休斯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期间,除了弗朗茨·诺伊曼,休斯还结识了利奥纳德·克利格(Leonard Kiieger)等历史学家同行。一九四八年休斯入哈佛大学任副教授。一九五二年因为大学方面认为他论文业绩不足,不得不离开哈佛大学,去了斯坦福大学。但是,也有人认为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才是他在哈佛待不下去的真正原因。一九五七年,休斯积累了够格的研究成果,返回哈佛任历史学教授。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正值壮年的休斯学术和政治活动的顶峰时期。继《意识与社会》(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1890—1930,1958)之后,重要著作《被堵塞的路径》(The Obstructed Path: French Social Thought in the Years of Desperation 1930—1960,1968)和《大转变》(The Sea Chang:The Migraton of Social Thought 1930—1965,1975)问世,构成他的所谓欧洲思想史研究“三部曲”,在欧美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他不仅在普林斯顿、斯坦福兼职,也是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一九六二年休斯还作为和平运动、无党派人士参加上议院议员竞选,虽然在马萨诸塞州获得选举规定的超过七万名选民的签名,但是由于发生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民主党转向与苏联对抗的政策,他那几乎要求美国单方面废除核武器的选举纲领(休斯当然也表示要警惕苏联的核威胁),马上在竞选中陷于极其孤立的境地。也许这件事也蕴含一点授予奥巴马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休斯曾这么回顾当年的选举:“二十世纪后半期,先进民主主义国家大概都存在如何开展少数派政治运动的问题。欧洲各国情况也差不多,那里也是少数派只有很小发言权。知识人组成的政党只能获得百分之二三的选票。美国也是同样,激进的少数派据点,已经不是工人阶层,转移到了有教养的中产阶层。大众不肯侧耳倾听少数派的意见,选举成了‘繁荣’和‘抑制’的现代社会的鸦片。”越南战争爆发后,休斯积极参与反战政治活动,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年担任和平行动组织(Peace Action)主席。他还主张保护黑人和工人的权利,甚至积极支持女权主义。这些激进政治活动使他在哈佛大学同事中待不下去,一九七五年再度无奈离开哈佛大学,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到去世一直住在圣地亚哥。休斯的遭遇说明民主国家的大学里的学术自由也是有局限的。雅斯贝尔斯当年也这么感叹过。
休斯的研究领域是思想史,却与以精神分析历史学著称的盖伊的历史观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继承其启蒙主义的传统,坚持理性,却都反对片面的理性至上,不恪守历史学界实证主义的教条陈规,虽然休斯没有像盖伊在精神分析道路上走得那么远——亲自接受精神分析训练,但是休斯受了精神分析医生、历史学家妻子朱棣斯(Judith Hughes,也是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影响,与精神分析学说也充满感情。读《意识与社会》,你会有这样的感觉:休斯是把弗洛伊德看做一八九○至一九三○四十年间出现的、对欧美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甚至放在韦伯和涂尔干之前。休斯与盖伊一样,有一种想通过精神分析把历史学从刻板的实证主义中解脱出来的倾向,对德国文化、特别是对魏玛时代文化抱有特殊的情感。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基于观念论的德国新人文主义的好感。在《被堵塞的路径》中他感叹韦伯和弗洛伊德在法国,从来没有获得在一九三三年前德国和四十年代后在美国发挥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对二十世纪中法国新理想主义的社会史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转变》集中叙述三十年代因法西斯迫害逃往美、英的中欧德语圈的知识分子对盎格鲁传统学术影响之历史,书中关于精神分析学派在美国的繁衍、对美国心理学发展影响的叙述占据了很大篇幅。与盖伊一样,休斯把精神分析作为分析历史人文个人动机的一个方法,也把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学科。
他的另一著作《历史学是艺术,也是科学》(History as Art and as Sc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