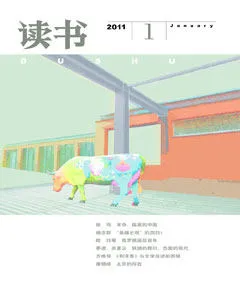“洋客”的琴学研究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本业是外交官,但他却触类旁通,因缘际会成了一位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及日本文化──深造有得的学者,著作涵盖宗教、书法、绘画、砚台、音乐、房中术等常人等闲不易涉足的领域。公余之暇,钻研学术之外,高罗佩还舞文弄墨创作了十余本以唐代狄仁杰为主角的英文畅销小说《狄公案》,他著作等身,兼顾了学术研究之严谨与文学神思之富赡,天才横溢,令人叹服。老外交官胡光先生,将高罗佩与李约瑟、伯希和、高本汉等学者同列,推崇为百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百大“洋客”之一。
根据高罗佩好友、另一位老牌外交官陈之迈的记述,高罗佩一九三五年出任荷兰驻日大使馆秘书,对日本文化源头的中国产生了兴趣。这位二十余岁的年轻人多次到中国搜集典籍器物,研习书法绘画。据说他在北京访师学琴,随身携带节拍器一具,以测试琴人抚琴节拍的稳定度,琴人关仲航连弹两次《平沙落雁》,速度分毫不差,让高罗佩大为惊奇。说真的,这个小故事也让我大为惊奇:本来传统琴人抚琴操缦是比较自由的,不像西方音乐强调节拍观念。我本以为高罗佩一心向往中国传统文化,不料还是有着西方人的“赛先生”本质,仍然忍不住要以西方科学的角度对东方艺术冷静客观地评量一番。
无论如何,高罗佩最终拜在逊清贵族琴人叶诗梦门下。叶诗梦原姓叶赫那拉,名佛尼音布,号师孟,后改诗梦,他的姑姑即是系近代中国大政于一身的慈禧太后,其父是晚清两广总督瑞麟。叶诗梦以贵公子而精于艺文,即使清室覆亡,家道中落,他的气度涵养、举手投足之间想必仍凝聚了贵胄世家的典雅高华,让高罗佩这位“洋客”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段师弟琴缘为时甚短,叶诗梦逝世于一九三七年,但高罗佩对老师念念不忘,数年后出版《琴道》一书即是献给叶诗梦,又手绘叶诗梦小像,“遍请中国友人题咏”,可见叶诗梦对高罗佩影响之深。
高罗佩音乐研究主要集中于英文撰作的《琴道》(The Lore of Chinese Lute:An Essay in Ch’in Ideology)及《嵇康及其〈琴赋〉》(Hsi K’ang and His Poetic Essay on the Lute)二书,其中尤以《琴道》最能呈现高罗佩对于琴的全面及深刻理解,但至今仅有部分章节译为中文,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琴道》一书以英文写成,初稿于一九三八年面世,分三期刊载于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的《日本文化志丛》(Monumenta Nipponica)上,一九四○年上智大学结集成书出版,一九六九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全书包括七章、四个附录,插图数十帧,以及一篇作者自撰的文言文后序,文字颇为雅洁。第一章《概论》开宗明义说明琴为文人雅士之器,同时兼具合奏及独奏功能,并由文字学论琴的源流发展,及琴在日本的流传。第二章《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介绍《乐记》之中以礼统乐、礼乐偕配、“声音之道与政通”等礼乐治国的音乐观。第三章《琴学研究》是内容最丰富的一章,第一节《资料》说明研究资料来源,第二节《起源及特点》,由中国音乐史讨论琴道之所以生成,且归纳了儒、道、释三家在琴道中的体现,可以说是琴学的“三教论衡”。第三节《琴人仪止及规范》,论述抚琴的场域空间、弹奏环境及聆赏对象的规范,如何携琴,琴童、琴社等。第四节《选文》则选译了五篇琴学论文,以显示琴道内涵风格的差异。第四章《曲调的意义》分析琴谱中常用的“调意”,并由标题音乐(Programmed Music)的概念将琴曲分为神秘行旅、历史之曲、文学琴歌、自然之曲、文人之曲等五类,同时以曲例详加说明。第五章《象征》,第一节介绍古琴各部件名称及象征意义。第二节翻译冷谦《琴声十六法》以解释琴的音色和触弦手法的象征意义。第三节介绍弹琴指法及其象征。第六章《关联》,前三节阐释鹤、松、梅、剑与琴的关联。第四节翻译二十二个与琴相关的故事。第七章《结论》。以下又有附录四种,包含《西方琴学文献资料》、《中国琴学文献资料》、《古董之琴》、《中国琴在日本》等。
仅就以上非常简略的内容大纲,已可看出《琴道》的内容闳富,包罗万象。无怪乎此书至今仍被学者推崇为“巨著”、“研究中国古代琴学的权威之作”。但也许是作者的自谦之辞,高罗佩的初心似乎无意于成就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他在序言里自陈本书仅是一篇文学性的“散文”(Essay),提供理解琴的门径,尝试去描写琴。虽然如此,翻开这本问世已七十年的著作,还是很容易震慑于这篇“散文”的深度和广度。首先,此书在取材上异常丰富,包括散见于古籍中有关琴的论述、琴学专著,以及最特别的琴谱。明清两代有大量的琴谱传世,高罗佩显然是由搜集的过程中发现这也是绝佳的研究素材,而《琴道》中有关琴的曲调、曲目、指法、空间场域、抚琴规范等论述,很多就来自于这些琴谱的记载。高罗佩说,有些资料是经过年余的寻寻觅觅,才在日本或中国书店的阴暗角落发现的。这种走街串巷搜集资料的方式,与今日学者坐在电脑前运用数据库可谓大相径庭。其次,高罗佩并非是只精一门的学者,胡光说:“高罗佩一样专家都不是,却是一位业余研究汉学范围最广的怪才。”因为视野广,因为天赋高,所以注定他的入手不局限于琴,《琴道》中除了广泛地观照经史诸子,更经常援引书法、绘画、园林、砚石等其他的文人艺术体验来诠解琴,可以说,他是以文人生活的整体品味衬托了琴。其三,高罗佩的琴学研究兼跨了中日文化,这是源于他对东皋禅师的推重。东皋禅师俗名蒋兴俦,字心越,号东皋,康熙年间东渡日本长崎。禅师精于琴艺,为虞山派传人,《东皋琴谱》在日本流传甚广。高罗佩既对东皋禅师感兴趣,辑有《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一书,对于琴在日本的流传也特别关注,这些论述占了《琴道》相当篇幅,体现了他跨文化的宏观格局。
然而,《琴道》毕竟已是七十年前的旧著,此书出版时高罗佩也不过是三十而立的青年,如果我们仅能叹服于此书是古琴研究的“集大成者”,岂不代表了半世纪以来学术的停滞不前?此书其实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例如琴道的儒、释、道“三教论衡”(高罗佩自己并未提出“三教论衡”之名,但表述手法却近似唐代的“三教论衡”),其实“三教”是“失衡”的。再如他将琴译为Lute而不用较为合适的Cither,当时的乐器学权威萨克斯(Curt Sachs)已觉不妥,但高罗佩以为欧洲文化中Lute与游吟诗人有特别的联系,更符合琴的文化位阶与内涵精神。此一观点恐怕悖离了乐器学的科学分析,而文化位阶与内涵精神的认知更是见仁见智。
高罗佩的朋友都知道他最推崇明代文化,他的收藏以明代文物为多,书斋也名“尊明阁”。因而对明代文人生活的向慕追求也体现在《琴道》中,书中取材、观点大抵不脱明人风味。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罗佩是以明代的琴学理想框架了整个中国琴史,历史长河中的琴学发展经过他的筛捡压缩,成为一片明代风景的画片,这也许是本书最大的遗憾。
高罗佩曾说:“余癖嗜音乐,雅好鼓琴。”一九四三年,大战方殷,高罗佩奉派调任重庆,担任荷兰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在连天烽火中,他依旧以琴会友,成立了“天风琴社”,与旧雨新知鼓琴不辍,还曾经与琴家张子谦先生一起“琴集”,在张先生的日记《操缦琐记》里留下了一段有趣记载。观察高罗佩的交游过从,以及他与当时学术环境的应对交涉,我们注意到了《琴道》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二十世纪前半期,整个中国沉浸在追求“现代化”的氛围中,当传统艺术面对“现代化”的大纛时,无不努力重整原有的知识体系,为自己在新时代里找到合理的定位点。以古琴而言,不论王露进入北京大学教琴、王光祈译琴谱为五线谱,还是今虞琴社诸公以西方音乐理论诠释琴乐声响,都反映了这种与西方知识接轨的企图,这是《琴道》写作时的时代氛围。但高罗佩却另出机杼,他不以西方音乐理论来合理化中国的琴学传统,反而以明代文人生活的整体品味来衬托琴。他采用了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书写策略,“君子不器”的通才视角,为西方读者建构了以琴为中心的明代文人生活想象。这种书写策略是否隐含了对于当时学界风潮的反思?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这位现代洋客外交官,借着《琴道》及其他众多汉学著作,的确展现了他暂别现代的企图心,以及对传统眷眷不可自拔的向往。异哉!此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