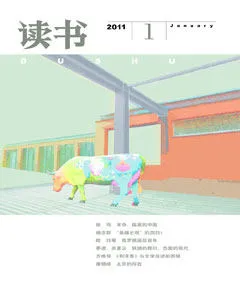冯友兰视域中的大学与学术独立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教育家,冯友兰的教育论著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在报刊上发表的评论,这些文章最直接地反映了他对教育问题的见解;一类是他在参与清华管理工作时起草的公文和发表的讲话,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清华校史和中国现代教育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有一类是他在《三松堂自序》等著作中对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三所著名大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对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回忆和评价。由于冯友兰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他的这些论著也主要与大学及学术有关。
学术独立是贯穿冯友兰教育思想的一根主线。早在一九二五年,他在《怎样办现在中国的大学》一文中,就将认清“中国现在须力求学术上的独立”的状况作为当时探讨如何办大学的前提之一。一九四五年在《大学与学术独立》一文中主张,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要做到“知识上底独立、学术上的自主”,要做到学术独立就必须扩充几个好的大学,使之成为国家的学术中心。一九四八年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提出:“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解放后即使屡受批判,他仍撰文论证“为学术而学术”的合理性。改革开放后他获得了自由,一九八七年在回忆清华的发展历程时,更加生动地称“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
学术独立,从消极的方面讲,就是主张学术不依附于宗教、政治、金钱等学术之外的东西,不受它们的随意干扰和束缚;从积极的方面讲,则是肯定学术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保持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冯友兰讲的“学术独立”,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面对西学东渐的世界学术格局,中国的学术要独立于西方,实现知识的自主,不做西方的附庸;第二,面对中国当时混乱的政局,学术要独立于政治,不受政府的恣意干预和束缚,对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第三,面对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学术要独立于“致用”心态,对大学不应有急功近利的要求。
一、中国学术独立于西方
冯友兰讲的“学术独立”第一个层面的意思是,中国的学术要独立于西方,实现知识的自主。他认为,在现代中国办大学,首先要认清中国学术不独立的现状。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可怜异常,有许多人想看书而无书可看”,“对西洋学术有较深的研究之人甚少”,中国“须充分地输入新学术,并彻底地整理旧东西”,以“力求学术上的独立”(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二○○○年版,30页)。这种学术不独立的状况曾在清华大学有过极端的体现。清华是庚子赔款的产物,其前身即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赔款设立的“游美学务处”,主管选派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事务。一九一一年成立清华学堂,成为正式的留美预备学校。上世纪二十年代,受教育独立思潮的影响,清华开始筹办独立的大学,但直到一九二八年罗家伦就任清华校长时,学校仍有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在行政管理方面,清华受外交部而不是教育部管辖,学校校长之上还有美国公使控制的董事会;在教员方面,职员的地位高于教员,外国教员的地位又高于中国教员;在学科方面,洋文高于中文,西方学问的课程高于中国学问的课程。这些不正常的情况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学术依赖于西方的现实。
这种现状是如何形成的呢?冯友兰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中国在过去数千年中当然有他的独立底文化。这个独立底文化,不仅支持了中国民族的独立,而且使中国民族在东亚取得领导的地位。”但在工业化过程中落后了,“西洋的工业化,造成了‘乡村靠都市,亚洲靠欧洲’的局面。中国的农业文化与西洋的工业文化,相形见绌”。这直接导致国人心态的转变,“中国人先是妄自尊大”,以天朝上国自居,鄙视西方文化,但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国家一次次打败之后,“又妄自菲薄,以为中国无论什么都非学西洋不可。不但要学西洋,而且中国人也需要到西洋去受教育”(《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156页)。积贫积弱之下,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心越来越弱,由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逐渐发展到激进派的“打到孔家店”,誓与传统决裂,全面倒向西方。这样一来,就在学术上、教育上失去了独立,形成了对西方的依赖。
然而,学术上的独立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冯友兰在抗战胜利时提出,原子弹等新作战工具的发明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的工具带来了新的战略,新的战略改变了战局。冯友兰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虽然日益强大,但是没有做到真正知识学术自主独立的地位,这就是他的失败根源”;而同盟国的胜利是“知识的胜利”。冯友兰明确表示,“现在的世界是斗智的世界。谁要知识落伍,谁就要归天然底淘汰”,中国要抓住战后的有利机会成为世界强国,“就要做许多事情,其中最基本底一件,是我们必需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底独立,学术上的自主”(《三松堂全集》第五卷,456—457页)。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知识上的独立和学术上的自主?在冯友兰看来,第一步还是要向西方学习,特别是要大规模地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我们要想叫现代学术到中国来,我们还是先教现代学术说中国话”,同时指出“这不是根本的办法,但这是根本办法的先决问题”(《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42页)。根本的办法则是办好中国的大学,树立几个学术中心,他将这种学术中心称为“大大学”,主张“把现有底几个有成绩底大学,加以充分底扩充,使之成为大大学”(《三松堂全集》第五卷,457页)。
二、大学独立于政治
办好大学首先要认清大学的性质。在冯友兰看来,大学不只是比中学高一级的学校,不只是一个教书育人的机构,更是一个研究和创造出高深学问的机构,“它不但要传授已有底知识,并且要产生新底知识。他应当是一代知识的宝库”。大学应包罗万象,研究各种学问,囊括各种专家,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大学都应有些权威的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从前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现在应当说一事不知,大学之耻”(《三松堂全集》第五卷,457页)。大学对文化的传承和人类的发展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实在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从这一角度来讲,并不是所有名为“大学”的机构都是真正的大学,有的大学只是承担教学任务,的确只是比中学高一级的学校而已。为了区别这些“大学”,冯友兰将真正的大学称为“大大学”,这种“大大学”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在世界各国中,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但每一个世界强国都必须有几个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大大学既然是包罗万象,成为一代知识的宝库,其中底组织,必然极其复杂,所用底人,一定是很众多。而现代学问,研究起来,又是很耗费底事情。”面对现代中国社会资源有限这一现实,他主张政府应集中人力财力重点建设几个基础较好的大学,“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底世界强国,我们必需集中人力财力,把几个已有成绩底大学扩充起来,使他们能够包罗万象,负起时代使命”。相反,如果无重点地平均分配资源,就会使所有的大学都弄成不大不小、不高不低的学校,无法形成中国的学术中心。他不是反对平均发展,而是认为在现阶段建立学术中心的工作更为重要,“有了这个中心,然后学术界才有是非的标准,一国的学术水准才能提高”(《三松堂全集》第五卷,457—458页)。
大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治权,政府不能随意干预大学的内部事务。冯友兰主张,由于大学是一个独立的、“自行继续”的团体,而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下属的一个科室,也不是政府的宣传机关,所以,政府不应随意干涉。具体来说,他认为,术业有专攻,精深的学术是专家的工作。“学问越进步,分工越细密。对于每一门学问,只有研究那一门底专家有发言权。大大学之内,每一部分的专家,怎样进行他们的研究,他们不必使别人了解,也没有法子使别人了解”。隔行如隔山,只有专家才懂得专门的学术,所以学术评价也必须在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