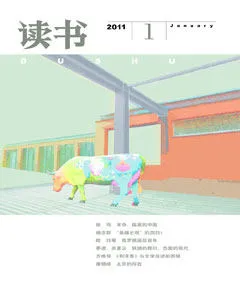“英雄史观”的回归?
谁也难以否认,“英雄史观”近些年衰败得如此厉害,在“社会史”和“新文化史”两面夹击的强势围剿下,几乎变得人人可诛。然遥想当年,“英雄”一直占据中国主流史学的中心位置。政治史的主角无疑是“帝王将相”,或是帝王将相的变种:那些“起义领袖”或“革命首领”。即使是官方理念主导下的“民众史”,也书写的是“变态”的英雄史,何出此言?君不见,主流史学一直打着民众推动历史进步的旗号展开叙述,但民众的现身往往不是在躬耕陇亩甚至也不是在啸聚山林之时,而是在揭竿而起席卷蔓延成所谓“农民起义”之后。虽然群氓造反,多不成事,但其统领除因殉道被剿杀之外往往是最大获利者,常常能登堂入室,成为改朝换代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刻满了历史的花名册,民众最终还是难免沦落为“历史的失踪者”。故打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招牌的各类历史书写,都可以看做变相的“英雄史观”。或许可称之为一种“伪民众史”。主流史学中的“人民大众”还极易为“变态”历史观中的许多神话表述所绑架,比如夸张地说他们能左右历史的“规律”“趋势”“进步”云云。
不得不承认,旧式“英雄史观”是极力要求删除历史发生的各种“常态”的,常见的例子是每隔几年史学界就要热闹一回,缘由是要纪念某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多少周年,或庆贺某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诞辰。“纪念史学”的规模如仪式似赶集,每逢集日,各色人等纷纷登场,痛说英雄创造历史的业绩,人们也经由此等“赶集”获取合法从事历史研究的通行证。不过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还真出现一拨儿不想赶这趟集的异类,就他们而言,对“常态”历史的成功关注成为分散抵抗主流叙事的一种最佳策略。在他们眼中,普通人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甚至构不成任何“事件”要素的某种“集体无意识”都能成为核心话题。更别说村庄里一个老农貌似平庸的私生活,甚至吃喝的种类成分、居所的位置朝向,乞佛拜香的灵签、黄大仙意识流似的“胡言乱语”,庙碑里的隐语秘言,都是他们穷搜极索的对象。对“日常生活史”的关注催生了人类学与中国历史学的结缘,也开启了“英雄史观”落寞的序幕。
人类学渗透进历史学直接诱发了具有中国特色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在我看来,推说中国地域辽阔,不可能一下子做出整体概括,而非得做切片式研究的看法,不过是历史研究转向底层的一个极其表面的理由。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盟均首先发生在东南地区是有其更深层原因的。东南沿海如广东、福建地区宗族网络发达,庙宇遗迹遍布且多保存良好,至今修谱拜神的风气鼎盛不衰,具有历史与当下的自然延续性则是个重要的地区性原因。出生于当地的人类学和历史学家熟悉本地语言习俗,又尽得近水楼台之便,使得“区域社会史”的兴起具有了鲜明的“在地化”特性。这倒不是说北方地区就不具人类学田野的特征,而是说人类学与历史学交汇集合后产生对话反应的要素更容易在东南沿海一带体现出来。其实,历史人类学所展现出的“在地化”特性与费孝通所说的“汉人人类学”的转型有关,由于观察对象被转移至文明程度较高的“汉人”社会,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没有西方传统人类学检视异族文化时那般容易产生与“他者”的隔阂。我们会发现,历史人类学的触角基本不会延伸到西南非汉人聚居的民族地区,故与传统“民族学”的研究路径鲜明地区分开来。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缘彻底终结了“英雄史观”横行的历史,史学的首要任务似乎是观察民众“常态”下的日常生活,捕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以便区别于“英雄史观”对“变态”历史的支配性阐释。人类学对社会结构中各类“象征”符号意义的解读同样引发了“新文化史”探索微观物质生活的热流。新文化史渗透的范围已波及到气味和声音、阅读与收藏、空间与身体等等相互关联的层面。甚至“香水”的弥漫和“钟声”的扩散这样难以捕捉的感觉都会被认真写成历史。不容置疑的是,“英雄”的落寞和消失也造成了一些问题,比如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过度迷恋导致研究的“琐碎化”,缺少了“英雄”角色,人们不禁会问:历史大线索靠什么来编织呢?充满着民众无意识行为和细节的历史反而在走向上显得更加模糊不清,说严重点甚至会使人们失去理解历史演变趋势的动力。区域化历史情形的细致深描能否替代整体历史的解释也是个未知数。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历史书写的“平庸化”,当早已习惯由“英雄”经验填充历史记忆的那些头脑,突然要适应阅读那些零碎不整的生活记录,还要努力说服自己承认其具有研究的合法性时,是需要相当大的心理承受力的。
王铭铭出生于泉州,按理来说其学术经历应该循序稳妥地步入人类学的典型“民族志”一脉。可泉州自古又是辐辏八方的世界级大港,来往多有东亚一带以及阿拉伯和内亚地区的商人,泉州文化包容开放的气质也许多少使王铭铭的思维受到感染,故其研究路数颇不安分寻轨,倒也好像少了某些汉人人类学学者有意无意表现出的“在地化”痕迹。除早期《社区的历程》和《闽台三村五论》外,王铭铭的心绪犹如泉州港里的大舶,漂浮不定,却总是连接着家乡以外的世界。从《逝去的繁荣》对泉州老城的考察到倡导“中间圈”即藏彝走廊历史的研究,都在反复印证他不安分的游走状态,隐隐昭示出一种不同于常规“在地化”的个性书写风格,以至于我们很难用“历史人类学”或“区域社会史”等熟识标签来规范他的思考。现在,王铭铭又开始倡导“人生史”的写作,这论题不但与渐具霸权特征的“区域社会史”主导研究取向渐行渐远,其大唱反调的举动难免易惹众怒,而且其选择犹如孤独远行的旅人,必须担当不确定行程所带来的各种风险。
为什么要打出“人生史”的旗号呢?它与“新文化史”已经习惯使用的“生活史”表述到底区别在哪里呢?王铭铭的解释是“生活史”的对象相当于社会科学所规定的“群体”,它们在特定学科术语描述的“人生礼仪”和“日常时间”中经历着历史流程。“人生史”的对象则是“非常人”的个体,比较接近古代史书中的“人物志”。对“普通人历史”的过度关注常常使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极易陷入“民粹主义”的窘境。对民众日常生活观察的痴迷很容易连带着对其行为方式进行无原则的肯定。史学过度“民粹化”的后果可能会表现为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在民族主义或革命史的解释框架下对民众集体无意识暴力行为的合法化。比如在“农民起义史”框架内,太平军对江南一带文化的蹂躏践踏被解释为反抗清政府暴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在“近代民族主义”叙事中,义和团虐杀教民的凶残也会被解释成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行动。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学者接受民族主义历史解释的过程,也就是树立民粹主义历史观的信仰过程。一旦树立此信仰,无论何种把“个体”融入“群体”的暴虐行为都因为是为历史必然性张目而自然而然变得合理合法。由此我们就可领会,曾一度热心鼓吹“新史学”,并把建构民族主义“国民史学”视为第一要义的任公,为什么到一九二二年以后思想会出现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闭口不提“进化”、“国民”等时髦字眼,而大谈似乎玄而又玄的“互缘”与“个人事功”?任公重拾“英雄史观”在那些奉行进化论史观的专家眼中,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对任公本人而言,转换另一个观察角度却无异于一次新生。
史学“民粹化”的另一个极端表现是,让过着平淡无奇生活的民众在特意设置的历史“常态”舞台上大唱主角。各类细碎庸常化的史实和描写,以及被重大历史事件所排斥的边缘角色及其活动,都被赋予了重要地位。其结果只能是,历史的演化主线被淹没,对庸常化史实的过度重视和描写必然带来史学思想的“平庸化”。王铭铭提出诊治史学庸常化的药方是回归“人生史”的写作。其目的是摆脱近代社会科学总是想把“人生”整合进民族国家秩序的僵化套路。从表面上看,这种整合趋向尊重“个体”价值,其实恰恰是想通过在关怀“个体”的语境中消灭“个体”,“个体”的个性一旦被削平,就恰似“庸人”猬集,最终促成结构对“个人”的全权监控。如福柯对敞景式监狱作为资本主义秩序隐喻的深刻揭露,表述的是权力对生命的控制,以及生命的反抗意愿,但仍无法对“个体”生命的真实意义做出更有价值的说明。
从“人生史”构想的提出可以看出王铭铭对费孝通晚年学术关怀的自觉延续。费老晚年曾大谈儒学的价值,谈孔子对人生与文化重建的作用,谈中国文明如何在当代世界中立足发展。在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密的情况下,这些似乎都不是受人类学训练的学者所应思考的问题,费老如此“越界”的表达却可以隐约彰显出当年任公晚年思考的影子。费老年轻时笃信“功能论”,“文化”在这个西化框架里只能服务于特定的实用目的。老年复出后费孝通一度关注中国农村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他曾在访谈中声称自己学术路径染有传统士人“经世致用”的浓厚色彩。可是到了八十多岁高龄,费老却大谈起“玄虚”而不够“务实”的文化价值问题,似与自己所受的专门化学术训练与事功追求不大合辙。然而费老的晚年转向却有特殊的深意,其抱负显然已不满足于早期人类学民族志过于局限在特定区域与过于强调功能意义的研究方式,而是要重建中国“文明论”的宏阔视野。这与任公那一代知识分子所怀抱的理想是暗相呼应的。我的理解是,“人生史”的提出也是想突破人类学民族志及深受其影响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自闭倾向,试图最大限度地避免田野调查方法局限于一隅而阙失整体视野的弊端,从更加广阔的范围考察内外“混合世界”的面貌。“人生史”也有意回避了国内社会史研究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士绅庶民化”方面的单一走向,认为对“士绅庶民化”的过度强调就是史学“民粹化”的表现,至少有屈迫士人混迹于庶民价值系统的嫌疑,长此以往,中国史学有可能失去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理念与表现方式的认知能力。
我对此颇有同感。当年我在论证“儒学地域化”概念的适应性时无疑受到人类学注重区域演变模式的影响,比较强调儒学资源有可能呈现出某种地区性形态,并有效支配着某群有区域背景的士人思想与行为活动的方式。以上看法遭到传统哲学史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如果把儒学置于区域化的视角内观察,无疑会分散和肢解其普世的价值观。我则认为,“儒学”实现地域化的过程并非意味着其整体性和普遍性的瓦解,虽然各地出产的精英所秉持的儒学理念具有区域性差异,但他们的行动却表现出跨地域的流动状态,并与各种近现代的政治运动有微妙的衔接契合关系。因此,如何通过区域性研究凸显士人在转型期的“文化”整体视野仍是我追求的目标。
在王铭铭的新著中,杨联和克虏伯的“文化论”成为论证“人生史”意义的最佳教本。杨联曾经在朝代更迭的分析中特意指出:文化形态的兴衰可以用“游艺说”(game theory)加以解释,因为艺术和文学的某种特定形式要遵守某一套规则,就像任何竞争性比赛需要技巧一样。在这些规则之下,只有一些有限的可能会被与赛者察觉,而那些察觉到最佳可能的人就成了杰出的大师。也就是说,文艺的游戏规则不仅操控在精英手中,而且更操控在“天才”之手。他们通过制订和运用规则导引社会历史的变化。其实,如果一旦把“游艺说”延伸开去,在政治经济乃至其他领域何尝不是各种“天才”在左右着历史的关键变化呢?我不知这种“天才主义”历史观到底和“英雄史观”有何区别,但很清楚它与人类学强调从土著和底层观点出发观察历史的平等主义策略是背道而驰的,与那些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意识形态史观和日益民粹化的社会史趋向也是不兼容的。
现代“个人主义”比较注意在社会政治条件制约下个人创造力的发挥与价值显现,这种对“个体”的尊重抹杀了某些具备天才特质的“非常人”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主义”也具有“平均主义”的品格。王铭铭以司马相如为例来说明在并不具备西方“个人主义”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非常人”也能凭借其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发挥常人难以企及的历史作用。司马相如足以担当“游艺说”所预设的那些察觉与掌控时代规则的角色,故可称为汉代的文化“大师”。在以后的朝代中也不时会出现这类人物,比如王安石、朱熹、王阳明诸人,他们对游艺规则的洞察与使用都有极致精彩的表现。就以“道统”在宋代以后的发明及其实践过程而言,适足以验证文化“大师”们具有相当强势的支配性影响。恰可为“人生史”的写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研究素材。
但我仍有疑问,那就是“游艺”标本的选择问题,从对司马相如个案的择取,可以看出王铭铭的选择意向偏于他所理解的具备“文化”特质的人群。那么我们不妨问问,“天才”的标准到底应该设在何处?是纯粹的“文化人”呢?还是应该包括“政治人物”,诸如帝王乃至官僚?如果仅限于“文化人”,那么“文化”的力量是否有被夸大的嫌疑?如果包涵“政治人物”,那么他们的行径一旦与“文化”价值构成对立冲突,将如何定位处理两者的关系呢?就如现今每个胸有点墨的人都会时髦地喊几句口号,声称要延续知识分子“道统”,似乎在当今权势的压迫下,人人都是一脸的真诚无辜。可一旦面对现实选择,采取合作态度者却远大于批判现实者。很明显,加入后一人群的成本肯定会高得令人难以承受,人们自小受到的教育也使得他们越来越精于计算,如此一来,“道统”的垮掉似乎早成雪崩之势,越谈越被“空心化”了。
很难相信,一代枭雄汉武帝仅仅是被司马相如的几首诗赋牵动了神经,乖乖地按其意志行事,《史记》中描绘的一些场景细节,乃至帝王发出的回应讯息更像是司马迁如花妙笔构造出的诱人图像,尽管这想象绚烂不已足可为想象标本却不可完全当真。我倒宁可相信,任何历史时段有关“世道人心”的建立都不可能只是某一类“天才”和“大师”单独能够完成的。只会吟诗作赋和只会弄权使计的单一“特异人种”都不可能独霸历史的设计程序。我更相信一种“合谋论”的存在,你尽可以把“天才”从凡人扎堆的民众中强行打捞上来,赋以游戏操控者的使命,但“天才”仍是有等级和类别的,不能指望“文人天才”包打天下,一路吆喝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不成了包治百疾的古代“张悟本”了吗?制订规则或者呈现规则的应该是那部分更强势的“天才”“大师”,一部分与“文化”的力量有关,一部分与“文化”的力量无关。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出,“恶”势力也常常是历史转折关头的支配者,它们恰靠对“文化”的控制得以成长,他们阴险、诡诈、手段高明、意志坚强,不仅经常制定游戏规则,而且足以掌控其他“天才”的命运。
李世民当年宣称天下英雄尽入罗网,不是一时冲动的得意,而是尽心控制的结果。再看清朝皇帝通过修书和文字狱的双重设计蹂躏“文人天才”的神经,就可知单一“文化天才”对控驭历史大势所表现出的无力感。我的建议是,在“人生史”的大格局之下,应该充分考虑各色“天才”所扮演的角色作用,更要注意观察他们之间交集互动时产生的效果,不压抑也不溢美。我们可以天真地自恋“道统”传承的纯洁,甚至不妨有限度地认可其在某些历史场景中所昭示出的所谓“超越性”,但不可剔除权力在其中所扮演的非道德角色。“人生史”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地放在无菌容器里进行试验,那很容易养成自我感觉良好的妄想症,而应该视为各个不同“天才”人群在其中混杂碰撞的带菌操作系统。故我认为,“生命政治”视角的介入似乎仍是必要的,至于如何在中国历史的情境中予以贴切的表达,那正是“人生史”推进所遭遇的最大挑战。
(《人生史与人类学》,王铭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年版,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