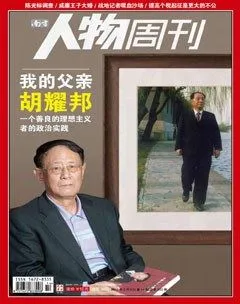这世界有那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
抬眼,是圣洁的梅里雪山;入耳,是隐约的藏歌;头顶上,满天的繁星,还有雪中的苹果花,醇酒似的可以把人晒醉的阳光……这是一个我们曾经熟悉的自然,这个久违的自然在《在藏地》一书中被一个名叫苏羊的女子叫醒了。
自然这个词,是此刻的我的言说。这本副题为“香格里拉支教随笔”的集子里,这个词没有刻意地现身。但是,从头到尾,自然鲜活的气息满溢在本书朴素的字里行间。
在云南德钦县的普利藏文学校,苏羊是一名来自大城市的支教老师。因为害怕浪费生命,也因为厌倦了虚伪的城市生活,她的内心一定有什么东西需要她坚定地去守住,于是,在2006年的夏天,她只身去了云南,在辽阔的山水中坚持去做“一粒被流水冲刷过的鹅卵石”。整整一年,她与藏区的孩子为伍,教他们学习汉文。她像一个母亲关爱自己亲生骨肉那样关爱她的学生。她获得了孩子们由衷的爱戴。作为一名志愿者,她那时是这样的愉快而满足,如一个自在的小宇宙。但这个行事极有主见的小宇宙并没有满溢,在这本随笔集的后记中,她不无谦卑地回顾道:“那一年,我所得到的东西,远远多过我所付出的。”
我们不必像书中写到的那位北京来的导演,带着愚蠢的偏见去猜测志愿者为什么放弃优渥的城市生活而去穷困的藏区支教——一个多么傻不拉几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倒可以站在普利藏文学校的立场上反躬自问:面对藏区稀缺的教师和藏族孩子渴望的眼睛,为什么我不向前跨出这一步,偏是这名薄弱的年轻女子,毅然决然地前往一所简陋的藏文学校支教?
依照世俗的观点,那地方很苦,物质上极其贫穷,而且道路极其坎坷难行。诗人、也是志愿者之一的马骅就是在那里因所坐汽车翻入澜沧江而遇难的。这是她到了那里之后知晓的事情。
支教的学校在山谷里,原是一座寺院的仓库,不通车,经常停电,一到夏天,雷电交加是常有的事。自种的土豆是一年四季最主要的菜肴。作者满怀真情地记录了这样一顿“丰盛的晚餐”:一点咸菜加三分之一的粑粑,两个芋头,少许的土豆,两大砂碗粥……可是这小女子却越吃越香,津津有味,还一个劲儿地感慨:好吃好吃真好吃!而关于吃,读者如我,恐怕这辈子都忘不了书中一个奇特的场景:一大帮人,盘腿坐在牛粪上,一手抓着菜,一手掰着粑粑——他们吃得那么津津有味。
这不是面对镜头表演给你看的一个姿态,而是作者发自内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赞叹。这些文字,不事雕饰,粗服乱头,皆是好的——它原初就不是想写给大家分享的一本书的文字,只是一名擅长文字的志愿者个人的抽屉记忆,是好心人促成了《在藏地》这么一本小书的面世。书的出版所得,作者全部捐给了支教的学校。作者苏羊有一个愿望,她要用这一点微不足道的资金为学校建立一个医疗基金,因为那儿太缺少药品了,就在她离开之后,有孩子因为生病看不起医生而去世,让这位曾经的志愿者揪心不已。
简朴的生活,需要慎重打量,也需要掐着指头计算每日的开销。在《世界的原本面目》那一小节,作者像一百六十多年前的美国人亨利•梭罗一样,动用了自己不太擅长的数字的书写,“这个月只用掉了二百多一点”,她不无感慨地计算着。当然,即使如此,《在藏地》也不是一本向梭罗致敬的书,它压根儿就没提到这位美国人。不过,这本薄薄的小书,与梭罗那本伟大的书的精神气息——说到底,还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
开销明显地减少了,那是摒去了物质生活的缘故。一面是放弃,一面却是获得。志愿者的精神生活开始少有地饱满起来——且让我们听一听她的絮叨:
我的世界,反而复原到了它原本的面目:快乐、清平、原始,像一棵巨树的树皮那样,虽然粗糙,却纯朴:天黑即眠,黎明即起;一盘菜、一碟汤、一碗饭就足以填饱我的肚子,并使我感到心满意足,快乐安宁。
不必过多地占有物质,简单,却快乐,而且精神饱满,这是梭罗传下来的优秀品质。于是,这名来自大城市曾经享受过精美食物的女子有了一个引用苏格拉底的十足理由:这世界,有那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这话语中有着一种决绝的勇气——的确,苏羊有勇气将这一行警世的文字印在她这本书的封面上。
生活有时候其实就是一道加法或一道减法的题目。如果城市生活是加法的话,那么,藏地的生活就是在做减法——尽可能地减去物质的同时,宁静就会前来填满一个人的日子,而这是一颗丰富的心灵所需要的。
当然,藏地的支教生活,除却宁静而满目生动的大自然,就剩那些嘻哈打闹的自然的孩子们了——作者满怀爱意地称之为天使。《天使素描》是本书最长的篇幅了,她一口气写了九位:阿木、卓玛拉楚、丁争取品、此里旺楚、白顶、小公布此里、格茸尼玛、立青顶柱、扎西江层……还有别的小节提到的斯那旺姆、此里卓玛、卓玛英宗……她用文字画下他们的素描,于是,脸蛋儿红扑扑的他们成了这本简静的书的主体——也正是有了这一群小天使,自然才有了纯朴的人类气息——惟其如此,才值得铭记和回忆,也值得那些等不上灵魂的都市人停住脚步,扪心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