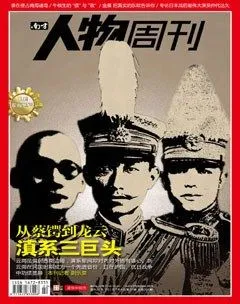来信
“环球”同此凉热
他和他所执掌的《环球时报》,这些年成了官方话语体系一个“异端”,或许还可能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异数”,这份报纸拥有百万以上的读者,虽附属于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却在体制内创造了一个准“都市报”经营的范例。固然,“商业民族主义”的质疑,也许是这个成功范例的另一个注释。
和那些被人为贴上政治标签的公众人物一样,胡锡进的言论,总是先入为主地成为各种批评攻击或“污名化”想象的靶的。面对这些,他表现得坦然,在现时的体制内,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涵养和风度。
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的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环球”的舆论场,也只是众声喧哗的组成部分,在话语体系的钟摆效应中,它也在积极寻觅自己的定位,只是很多时候身不由己,果然人在江湖。
它拒绝平庸,很多人更希望同时也拒绝脑残。
“环球同此凉热”。
此言不虚!
杨锦麟(资深媒体人,香港卫视执行台长)
《“环球”不高兴》
《南方人物周刊》最新一期把对我的采访做封面故事,但用《“环球”不高兴》做总标题,我认为不妥。这是把我和《环球时报》脸谱化。我们没有不高兴。中国很复杂,面对的各种问题尤其复杂、艰难,但这是中国崛起和转型过程中必须承受的。中国没理由叫屈。我个人也没理由为自己受到的非议叫屈。做事就得担当。
——胡锡进
什么东西都是要有自己的判断的,《环球时报》可能民族主义色彩多了些,这在国内众多知名刊物中也是比较少的,它的确吸引了一部分人的目光,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相当多元的社会,很多你觉得无法存在的东西都有它的市场,而且我觉得它也不应该消失掉,它是社会多元声音中的一元。只有多元了,我们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力,才知道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什么情况下该左什么情况下该右,等等。例如台湾的《自由时报》,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它的一些文章,有些没有考证的虚假报道,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上的报道,但它同样有它的受众,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事件、了解观点的途径,没有了它,世界可能就少了很多色彩。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到完全中立,在不同人的眼里,中立是有很多偏差(它不可能是在一个点上,或一条线上,它更多的是在一个范围内)的,如果你已经在脑海中形成了中立的标杆,那么很不幸,你已经洗脑了。我们只有在看过众多媒体对一个事件的一系列报道后,才有可能形成自己对这个事件的看法、观点,而不能想着通过一家媒体、一个网站来认识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那么你认识的世界也仅仅是一个面而已。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丰富,远不是通过规范硬件(媒体)就能解决我们软件(思想)的世界。
——网易陕西省西安市网友
音乐疯子
本刊记者王大骐
因为关注久石让音乐会,我看到了其中首席大提琴竟是我两年前第一篇像样稿子的采访对象。至今我还记得在广州星海音乐厅,演出中一个孩子开始嚷嚷,母亲迅速捂住他的嘴,朱老师停止了演奏,大声说道:“够了!我们的孩子就是从小被这样捂了一辈子的嘴。”因为被他的音乐,或者说是理念和激情所震动,我开始约访他,没想到凌晨两点的一封校内网站内信竟然就促成了一次采访,那封信在3点前就得到回复。
懵懂的我把初稿写出来后发给他看,结果被他狠狠地训了一顿。他用两个小时通篇改正了我的文章,对我说:“中国满地都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我希望你认真起来。”
两年后,还是深夜3点发信,5分钟后得到了他的回复,接着我们聊到4点。朱老师的大提琴室内乐队组建已有7年,目前还是中国唯一一支小型古典游击乐队。朱老师善于从冗长的古典乐作品中提取出5到10分钟的精华,再配以讲解后演奏,为的是适应中国人吃小菜的习惯。
周日在北京前门一餐厅,朱老师面对寥寥几十人,依旧兴奋异常,他想表达的理念两年后丝毫没变,还是惊叹于中国人在一起时太过于协调统一。他这样解释和谐:“在古希腊语里,只有对立才能和谐,在古典音乐里,音乐家各干各的才有和弦。”他还是痛恨勤奋,那跟灵感根本扯不上关系。他还是深信音乐生而平等,绝无高雅低俗之分,唯有动人与否。
外面黄土满地,屎尿味十足的工地上,起重机巨大的铁钩缓缓从窗边掠过,朱老师和3个学生奏起了瓦格纳的《盛大的典礼》——希特勒的党卫军的精神之歌,屠杀犹太人时毒气室里播放的乐曲。最后竟响起了婚礼进行曲的旋律,美得令人窒息。
追星的朋友
本刊记者马李灵珊
做律师的朋友找我:下周去你家住一晚,我要去上海电影节。不用问我都知道,她是来追星的。
我们俩相识于7年前,其时我16岁,她大学毕业没多久,已有工作却还在为司考焦灼。我们共同喜欢一个球星一个影星,于是网上勾勾搭搭,就成了朋友。
后来我考到她的城市上大学,常常去找她蹭吃蹭喝。她从初入社会的菜鸟成为刑法律师再改作商业律师帮人IPO,薪水噌噌往上冒,人也渐变得冷静老练,不变的还是爱追星。
我大一时她喜欢港乐,大二时她追快男,大三时她对《士兵突击》萌得死去活来,大四时一个台湾明星让她跑遍了半个中国,到我工作这一年,她又爱上一个电视剧明星。
她工作愈加繁忙,也不谈感情,追星几乎是她最大的业余爱好。到上海,回到我家打开电脑就开始赶一份文件,工作到夜里2点,匆匆卸妆睡5个小时,就起来赶高铁回去开会。隔一天再拎着行李箱赶来去某个首映礼为她的偶像呐喊助威,第二天一早再出差去几千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临走时抱怨:我这一个月每天最多也就睡5个小时。
她绝非特例,我的另一个朋友,高薪,美丽,有夫有子,在某著名的忙碌行业工作。累得七荤八素仍然会买最贵的演唱会VIP票,一边看偶像在另一个城市的演唱会,一边还在手机上处理邮件。她的下属,平素节省得要命,却肯花2万块,跟着偶像一个周末又一个周末地去看巡演,甚至把偶像CD拿去大老板面前推销。
我看着她们,谈不上羡慕也谈不上看法,只觉得人这一世,有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还能坚持,还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殊为不易。如果快乐和满足是能用钱和时间换来,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