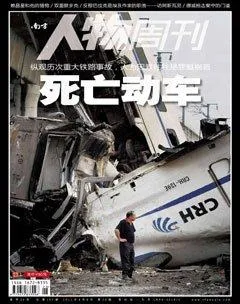来信
读书人的精神坐标
曾专门到广州中山大学寻觅陈寅恪的故居,那是一个盛夏的早晨,我在黒石楼附近询问了多位路过的学生,得到多是令我失望的回答,几乎都表示不清楚、不知道。
终于在一位晨运的老师指点之下,我来到了那一座故居小楼前。小楼附近的石阶,一位男生正在那苦读,我问男生,可知陈寅恪,他笑着回答,知道,他是一位大师。
1949年他选择留在大陆,为这一人生最关键的选择,他和他的家人付出了代价,但这只是百年来中国读书人为追寻独立与自由精神付出代价的个案。
大师在岭南的20年,最后的悲惨终局,令世人嗟叹。几近失明的大师在红卫兵高音喇叭喧嚣下惊吓而逝。临终的那一刻,他想说些什么?
他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坐标,也是一位殉道者。
我深深地在大师故居前鞠了3个躬。
杨锦麟(资深媒体人,香港卫视执行台长)
《陈寅恪家族 百年悲欣》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前年在庐山,经过庐山植物园而不入,后来才知先生之墓在里面。去年在杭州九溪,见陈三立先生墓碑。唏嘘。
——左岸旧友(新浪网友)
不用特别去写了,他的遭遇就成了一部史,告诫后人黑暗之残酷,扼杀学术、扼杀脊梁、扼杀未来。
——山顶黑牛凶(新浪网友)
向中国最博学的人、近现代史学巨擘致敬。虽然一生受尽苦难,经历晚清、抗战、内战,但最让他伤心的是“文革”的10年动乱,众多文稿被破坏,含恨而终。
——山微人峰(新浪网友)
《投奔香港》
我不说香港有多好,只是感慨它的教育制度,真正是为了培养服务社会的人才,而不是制造只会考高分的机器。相反,我们所谓的教育改革,从试点到推广,从文理分班,到现在综合试卷,从课间操改团体舞,还有无数次的课本改革等等。这么多年过去了,教育的实质还是这样子。社会上补习班层出不穷,奥数班、舞蹈、美术等特长班多如牛毛,我们的小孩依旧背着日益丰满的书包,出没于城市的各种培训机构。
——网易陕西省西安市网友
《利比亚见闻》
警察再多,也多不过百姓,警察也好,军队也好,用斯大林的话说:都是穿军装的农民。卡扎菲垮台不是因为警察少,手段不够黑,而是失去了民心。
——Jkhenry(新浪网友)
沾满人民鲜血、杀人如麻的极权统治者,等待他们的是良知与正义的审判,是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希特勒、斯大林、齐奥塞斯库、萨达姆纷纷倒下了,跳梁小丑的卡扎菲还能苟活多久?
——恋上自由博爱(新浪网友)
匹萨饼开罗
本刊记者 杨潇
就历史来说,开罗是个层次特别丰富的城市,而且这种丰富不需要你掘地三尺,它把各个年代的街区都像匹萨一样摊给你看。最大的那块叫伊斯兰开罗。公元969年,崛起于突尼斯的法蒂玛王朝攻占了埃及,建立了一座新城,并取名为“胜利之城”,这就是开罗,也就是后来的伊斯兰开罗。从爱资哈尔清真寺的楼顶看过去,四周全是清真寺新月形状的塔尖,这里藏着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基因。
与伊斯兰开罗隔尼罗河相对的是吉萨高地,一百多年前西方游客登上高地参观大金字塔,还需要雇佣士兵防止贝都因游牧部落骚扰,如今这里被疯狂的“导游”占领,有一个甚至直接跳上我们尚在行驶的出租车。如果把古埃及的首都孟菲斯也算作开罗一部分的话,那这座城市的历史就直接延伸到公元前3000年——其实如今的埃及和古埃及关联并不大,但孟菲斯人至少有一个特长被开罗人延续至今:对垃圾极强的包容心。考古学家发现,在孟菲斯被挖掘出的街道里,满是残破的纸莎草和陶器。
在法老与先知穆罕默德之间有一块耶稣基督的飞地:科普特开罗。它纪念的是埃及改宗伊斯兰之前的基督教时代,如今埃及仍有近10%的科普特基督教徒。周日的下午,我看到他们带着孩子在教堂外面的小广场嬉戏,在开罗,能一次看到这么多不戴头巾的女性,恐怕也只有这儿了。
最后当然要说说市中心,这里看上去就像上海的外滩或者广州的沙面,但显然不只是几栋欧式建筑这么简单,它象征着开罗一个失去的美好时光:19世纪末到20世纪头30年的西化改革。而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无论政治倾向多么不同,在建筑及城市规划上却是相同得乏善可陈。过去60年,这张匹萨饼最大的变化,就是长出了毛边——大量非法建筑及由它们堆积而成的社区包围了开罗。一月的革命,第一支抵达解放广场的游行队伍就从这样的社区走出。此前,他们通过卫星电视知道了突尼斯人的胜利,并倍受鼓舞。法蒂玛人肯定不会想到,一千多年后,他们的子孙以这样的方式重返埃及。
一把大手
本刊记者 陈磊
半夜睡不着,想起采访过的很多一把手的故事。
做袁伟民稿子的时候,曾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向我回忆,80年代,袁伟民率女排打出“三连冠”,扬名世界。有一次,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接见他,把袁伟民也叫去了。当着二人的面,胡耀邦说,袁伟民做出了那么大的成绩,说明这个人是很有才能啊,可以当副主任么!不久,中组部就过来考察袁伟民的情况,尽管李有不同意见,袁还是从国家女排主教练被破格提拔为体委副主任,直升四级!
做程维高稿。程也和人讲过一个故事:你说省委书记权力有多大?打个比方,我要看中了谁,直接把组织部长叫过来,说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见到那谁,感觉他思路不错。其他都不要说,这个话,朝这个地方一落,马上组织部,会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然后会拿到常委会上来讨论……
前几天去了某中部省份,该省新来的书记发现省党报发行量“与经济大省、新兴工业大省、人口大省和有影响的文化大省的地位不相适应”,因此“多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扩大党报的覆盖面”。为此,该省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下文,明确财政必须足额保障订阅经费。该省党报的发行量一下子从二十多万蹿升到五十多万。不过,按照飙升20万计算,每份党报一年200元,也有6000万各级财政费用支出。这还不算各级部门为扩大发行摊派、公关的成本……
一把手,一把手,好一把大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