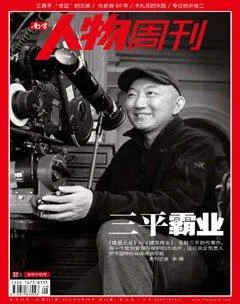吴宏聪 师道的传承
“面对死亡,父亲看得很淡然。”儿子吴嘉乐说。早在几年前,吴宏聪就要学生把自己的铭文刻在妻子的墓碑上。当时学生十分犯难,吴宏聪却始终泰然处之。
7月底,吴宏聪病重入院,学者陈平原前来探望。上世纪80年代,陈平原是吴宏聪的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吴老师是大转折时代的人,”陈平原说,“他身上体现的眼光和胸怀,传承了上一代人的格局和胸襟。”
1938年,吴宏聪考入国立西南联大中文系,先后受教于冯友兰、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王力等大师,后留在群英辈出的西南联大当助教。他在《学术自传•八十自述》中说:“我认为西南联大最令人难忘的是学风,最值得珍惜的是师缘。”
陈平原这样描述那段历史:“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象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吴宏聪则把自身作为一道桥梁,用一生孜孜以求的教书,传承了“师道”和“神话”。
陈平原师从吴宏聪时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吴先生有一次明确表示不同意我某篇文章的观点,但仍将其推荐给《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发表。吴先生的这种胸襟,除了个人气质,还得益于毕业自西南联大的学历背景。当年朱自清、闻一多指导吴先生时,也都是这么做的。”
在西南联大时,吴宏聪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曹禺戏剧研究》,导师是杨振声和沈从文。当他把论文提纲送给两位导师审阅时,杨先生不同意其中一些观点,沈先生却认为提纲尚有可取之处。论文写好后,吴宏聪不敢去见杨先生。没想到,几天后杨先生主动找到他,问明缘由。杨先生说:“虽然我们的观点不同,但是我尊重你的观点,作为你的导师,我要帮你完善你的观点。我尊重你选择的权利。”
1984年,陈平原提前半年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对于这名优秀学生,吴宏聪用行动表达了自己的钟爱。“他用在学校曾经做多年行政工作的‘便利’,为我安排在‘黑石屋’进行论文答辩。”“黑石屋”是中大最悠久的建筑之一,学校用来接待贵宾的,吴宏聪的良苦用心,陈平原终生难忘。毕业多年,每年中秋节陈平原都能收到吴宏聪从广州寄过去的月饼。
1946年,吴宏聪来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在这里,他开始了对鲁迅的研究。鲁迅1927年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和中文系主任,吴宏聪希望能把鲁迅的风骨一直留在这里。中大中文堂落成时加建了鲁迅广场,也是他和教授们一起努力争取的。
在吴宏聪的带动下,1979年入其门下的嫡传弟子、中大中文系教授邓国伟后来也走上了研究鲁迅的道路。
由于各种原因,吴宏聪编纂的《徐志摩全集》一直未能出版,邓国伟感叹:“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吴宏聪在学术上的造诣,不能仅以论文页码等衡量,他培养出这么多学生,这是他最大的学术成果。”在文学评论家黄树森看来,吴宏聪完全可以称为岭南学术精神的标杆式人物,“他是中山大学学术信仰的体现,好大学不能只看大楼、大师,还要看出了什么学生。”
退休以后,吴宏聪仍然非常关心弟子们的科研情况。弟子每有新作面世,他都要先睹为快。邓国伟说:“吴先生即便有不同意见,也都是平等探讨,不会以师压人。”
“凡有弟子上门拜访,他都要亲自回访。”从中大东区步行到西区,平常人不用二十分钟,而九十多岁的吴先生在家人搀扶下则要走上近一个小时。
“他怕我阻拦,快到门口了才给我打电话。而且但凡上门都要带礼物,他总说这样亲自上门好。他就是有着坚固的道德标准,在他身上,坚守着老一辈学者的道德风范。”金钦俊教授如是说。直到病重住院时,吴宏聪还叮嘱弟子:“要多写文章,不断积累,不要在乎能不能发表。”
“儿不嫌娘丑”,吴老生前多次讲过这句话,让儿子印象深刻。改革开放初期,年轻人很容易自我否定,觉得外面世界很精彩,本国的价值观、传统不如西方。对此,吴宏聪说了两句话:儿不嫌娘丑;努力工作,不要一味抱怨。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几乎听不见了。为了和学生交流,他弄了块小黑板,用粉笔刷刷地写。医生让他休养,禁止他看电视,他硬是拿着放大镜,每天坚持看完6份报纸期刊。即使在身体最衰弱的时候,也一定要把标题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