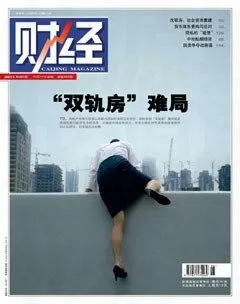谁在反对卡扎菲
利比亚政局的天平,在卡扎菲和他的敌人间高速摇摆。
格林尼治时间3月9日下午6时48分,路透社报道称卡扎菲的军队控制了扎维亚(Zawiyah)市,首都的黎波里以西约48公里外,一个反对派聚集的城市。8分钟后,路透社发布消息说,反对派夺回了市中心广场,并将政府军逐出城外1公里。10日,政府军再度发起攻击,截至记者发稿,扎维亚市中心的拉锯战仍在继续。
扎维亚,就像利比亚政局的缩影——卡扎菲想一战扭转乾坤不易;而弥漫在反对派中的乐观情绪也开始消散。
扎维亚的守卫者将9日的战斗描述为“一场生死之战”。部分当地人开始担心,一旦卡扎菲的军队夺回扎维亚,其坦克就将掉头向东,直捣班加西这个反对派的大本营。
僵持之际,利比亚内战双方都试图争取西方的支持。
3月8日夜,卡扎菲在动乱发生后,再度接受外国媒体的专访。他一边警告西方如果设立禁飞区将遭到武力还击,一边继续将利比亚内乱描述为基地组织控制整个北非的阴谋,“如果基地组织夺取了利比亚,这将是个巨大的灾难”。
针锋相对的是,班加西各反对派组成的全国过渡委员会(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自成立之日起,就呼吁美欧设立禁飞区。
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仍未对禁飞区的提议统一意见。3月8日,英法开始起草设立禁飞区的决议案,10日,法国率先承认班加西政权;中国和俄罗斯对武力干预他国内政持保留态度;而美国内部仍然争论不断。奥巴马总统只是说,美国正在研究。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10日表示,下周她将与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会面。
针对美国的迟疑,英国防卫与安全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研究员约什(Shashank Joshi)对《财经》解释说,西方国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吃过亏,他们发现反政府武装力量私底下往往有既不民主也不尊重人权的目的,而内战可能把一个专制军事政权推向前台,让战后的国家同样没有希望。
看不清的反对派
当2月15日利比亚反政府示威游行爆发时,美国政府的反应一度十分高调,奥巴马23日强烈谴责利比亚政府暴力镇压游行的反对派,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24日甚至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出兵利比亚,采取禁运措施等制裁方式。不过,2月26日,当背叛卡扎菲的利比亚驻联合国临时代表沙勒加姆(Abdurrahman Mohamed Shalgam)在安理会1970号决议讨论过程中,请求联合国设立禁飞区后,欧美国家的态度开始分化。
设立禁飞区,就意味着控制卡扎菲强大的空军力量,在2月27日班加西全国过渡委员会成立前,反对派并不热衷禁飞区的设想,他们害怕外国干预会影响革命的结果。但在和卡扎菲的僵持中,班加西政权装备和燃料供给的劣势慢慢显露出来,他们这才多次请求国际社会提供设立禁飞区等援助。
英国等欧洲国家积极响应,但美国的立场却摇摆不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克里(John Kerry)要求美国对利比亚局势立刻做出反应,包括实行禁飞区来阻止更多平民伤亡。但白宫办公厅主任达利(William Daley)对NBC说:“很多人在谈论禁飞区那样的词——他们讲得跟玩电脑游戏一样。”
约什告诉《财经》记者,国际社会不应夸大设立军事禁飞区的风险,如果不采取行动,卡扎菲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方法对付平民,包括使用尚未销毁的化学武器。他进而指出,卡扎菲的军事力量比较集中,国际社会只需要在首都的黎波里、卡扎菲掌握的运输要道及其追随者控制的几个城市上空设立禁飞区,就能有效遏制其空军力量。
从技术角度而言约什的想法很自然,但他忽略的是,美欧国家事实上越来越看不清班加西反对派的组成。“设立‘禁飞区’似乎既能保持中立又能彰显人道主义,但是在一个内战中的国家你不可能中立,不久你就会发现你在帮其中一方攻打另一方。”意大利政治分析师罗曼诺(Sergio Romano)说。
中国中东协会副秘书长、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说得更直白,利比亚的反对派混杂了很多人,既有伊斯兰极端势力也有部族武装,既有学生组成的团体也有新兴的商业精英,甚至还有基地组织的影子,外界很难搞清楚反对派内部的结构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知道自己在帮助谁。
美欧和班加西之间不仅互不了解,甚至很可能互存戒心。宗教极端组织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LIFG)就是西方社会心存疑虑的重要原因。利比亚东部昔兰尼加(Cyrenaica)山区是LIFG活动区, LIFG在1996年曾策划刺杀卡扎菲,但现在不少在班加西服刑的LIFG成员重获自由。华盛顿智库维护民主基金会副主席施塔特(Jonathan Schanzer)在为《财经》撰写的文章中表示,LIFG可以看作是一个大范围基地组织的核心成员。美国国务卿希拉里3月2日表示担心利比亚会成为第二个索马里,那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横行。
《泰晤士报》3月6日的一条消息加剧了这种担忧,消息称,班加西政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逮捕了英国政府派往当地的八人“外交小组”。
不过,尽管在设立禁飞区问题上无法统一,但西方国家大致同意将采取一致行动应对利比亚危机。希拉里3月8日表态说,即使设立禁飞区,也应由联合国出面,而不是美国挑头,“因为那是利比亚人自己的示威。”
部落政治窠臼难破
和突尼斯与埃及的示威不同,利比亚的反卡扎菲示威游行始终和部落斗争缠绕在一起。虽然最先走上街头抗议的是不满现状的年轻人,他们追求更多的民主权利,期望更好的经济生活,但在关键时刻推动了反卡扎菲政权斗争进展的,仍是部落政治。
2月21日,示威活动开始六天后,第一大部落瓦法拉(Warfalla)宣布加入反对阵营。瓦法拉部落聚居的米苏拉塔地区(Misurata District)地处班加西和的黎波里之间,其倒戈当天,利比亚政府就丢掉了对班加西的控制权,而靠近米苏拉塔地区的阿尔辛塔(Al-Zintan)则成为卡扎菲政权失去控制的第一个西部城镇。一天后,第二大部族图阿里(Tuareg)在瓦法拉影响下倒戈。
部落倒戈的主要原因更多是部落恩怨,而非突尼斯-埃及式的民主诉求。
其实和长期受卡扎菲政权打压的东部昔兰尼加诸部落不同,瓦法拉部落一度是卡扎菲政权的盟友。1951年独立的利比亚由的黎波里尼亚(Tripolitania)、昔兰尼加和费赞(Fezzan)三个原本互不统属的地区组成。1969年,卡扎菲政权成立后,来自的黎波里尼亚的卡达法(Qadhadhfa,卡扎菲出身此部落)、瓦法拉(Warfalla)和马格拉哈(Maghraha)三个部落成为该政权的支柱。但1993年瓦法拉部落与卡扎菲反目成仇,该部落因不满卡扎菲将空军垄断在自己的部落手中发动政变,政变最终失败,八名瓦法拉军官被处决。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中东和非洲问题高级研究员魏茨曼(Bruce Maddy-Weitzman)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分析道,利比亚是一个“拼凑在一起的国家”,它维持着原始的部落统治,缺乏基本的社会凝聚力,国家组织结构不尽完善。卡扎菲的统治手法,就是在丰厚石油收益支持下,玩弄部族政治,搞平衡,最终将实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杰夫(George Joffé)的研究表明,为了维系少数部族统治多数部族的政权,卡扎菲1997年向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开放了边境,大批移民随之涌入。卡扎菲一方面把这些不可控的移民潮作为施压近邻意大利的砝码,另一方面把其中一些人征召进其最精锐的特种部队第32旅,这支由卡扎菲的儿子哈米斯领导的雇佣部队,很可能是这次卡扎菲最后的防线。
部族矛盾容易引发事端,但部族斗争的指向未必是一个较民主的政权。
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王林聪告诉《财经》记者,利比亚的大小部落在本次动乱中起了主导性作用,如果班加西推翻卡扎菲,以后的政府如何平衡部落间利益将成为悬念。卡扎菲是通过强权政治来压制部族内部的矛盾,不给它发泄的机会;但如果没有强人政治,利比亚社会则可能要经过一个漫长博弈过程才能找到平衡石油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的最终方法。
改革派在哪里
其实,除了无权无势的年轻人,以及囿于部落政治窠臼的长老,利比亚政府中也有过温和的改革派。
2003年6月,美国塔福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博士、时任总理的加内姆(Shoukri Ghanem)开始了卡扎菲政权3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改革。依循美国当年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路,加内姆把经济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引进外资、私有化国企、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上。
他那时准备用五年时间私有化360个国有公司,取消政府对基本商品的补贴(当时利比亚90%的商品都享受政府补贴),放宽针对外国公司的进口限制。
改革实行后,利比亚GDP开始攀升,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到2005年,国内燃油价格增长了30%,电力价格翻倍,外国商品的涌入让竞争力薄弱的本地企业前景堪忧。
2006年加内姆在内阁改组后去职,但打倒他的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利比亚1969年革命以来僵化的政治结构。
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室主任贺文萍对《财经》记者评价说,利比亚政府不是没有进行改革,只是它的政治结构太落后,改革的速度太慢、效率太低,赶不上民众的期待。
卡扎菲设立的1969年体制下,没有宪法,不允许政党存在,政府架构在兼具行政和立法职权的全国人民议会上。全国人民议会名义上由总理领衔的人民委员会领导,但它的实际领导是卡扎菲。在全国人民议会外,还有一股独立而强大的政治力量——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也由卡扎菲总领,下设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和12人组成的指挥委员会。“革命”系统不经选举产生,有权指导和监督“人民”系统,并左右其决策权。
英国NGO新国家组织(New Nations)的一份报告解释说,加内姆的改革在议会内部曾引起了激烈讨论,讨论的混乱揭示了一个问题:由于没有宪法和政党,“改革派”无法整合力量来达到预期目标。更糟的是,革命委员会的一些“老兵”觉得改革影响了社会稳定,同时私有化的过程以及新商业领袖的出现,触碰了这些人在国企里的利益。于是,革命委员会在2006年轻易地进行了内阁改组,撤下了加内姆。
约什告诉《财经》记者,包括加内姆改革在内,卡扎菲进行过一系列面子改革,但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其统治而并非让人民生活得更好,所以此次游行爆发后,卡扎菲政权宁愿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也不愿改变以前的政体。
石油纽带
虽然国际社会举棋未定,利比亚内部诸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仅仅因为石油,世界就不可能对利比亚置之不理。
2010年6月发布的《BP世界能源数据》显示,2009年利比亚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为443亿桶,实际日产量约16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贸易量的2%。埃及爆发反政府游行后,由于市场担心埃及关闭苏伊士运河,切断中东原油供应途径,国际油价开始飞涨。示威游行蔓延到利比亚时,北海布伦特原油曾一度上涨至每桶120美元。在沙特阿拉伯宣布增加产量以弥补利比亚减产缺口时,油价才应声回落至每桶115美元。
中东智库海湾研究中心(Gulf Research Center)经济室主任沃尔茨(Eckart Woertz)对《财经》记者表示,如果国际油价上涨,受影响最大的将是亚洲国家,“亚洲国家是中东石油最大的消费群,它们的替代进口国从路程上来说比中东遥远得多,再加上亚洲国家进口的石油一般以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定价,它比纽交所石油期货价格更容易受国际形势影响,波动性很大。”
卡耐基中东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安琪(Lahcen Achy)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告诉《财经》记者,高油价将减慢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它们比欧美国家更依靠高油耗的技术。据他预测,如果游行继续蔓延,油价可能超过每桶150美元。
不过,许多分析师也指出,只要沙特等主要石油出口国保持稳定,国际油价就不太可能受到过度冲击,仅就利比亚局势而言,受冲击最大的不是全球油价或亚洲经济,而是欧洲经济。
意大利埃尼石油公司、法国道达尔公司、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德国巴斯夫旗下油气开采分公司Wintershall、英国皇家壳牌等八家外国石油公司占据利比亚原油总产量的72%,政治动荡引发的停产减产直接影响了欧洲石油供应。受害最深的国家恐怕是意大利,该国四分之一的原油和10%的天然气依靠利比亚进口,并在金融、基建等领域与之有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往来。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副主任熊厚对《财经》记者分析说,石油等能源市场价格出现波动,将引发资金流向的改变,部分溢出资金可能会流向相对比较安全的欧元区,从而加剧欧洲市场资产价格的波动;与此同时,欧盟2010年12月的通胀率首次突破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上限,高企的油价将助推通胀趋势,延缓欧洲经济复苏。不过,他同时表示,利比亚动荡究竟对欧洲经济产生多大影响,还要看动荡持续的时间。
无论国际社会在介入前如何计较得失,利比亚民众感受到的是每时每刻近在眼前的威胁。据联合国统计,动乱已经至少造成1000人死亡,约20万难民涌入邻近的突尼斯、埃及和意大利等国。
在利比亚生活了六年的石油工程师莫里斯(Ivascu Marius) 通过电话告诉《财经》记者,他刚撤出的黎波里,目前正在四处找工作。他说,“开足马达的炼油厂可受不了四处横飞的子弹,利比亚的形势可能导致长期无法开工,我愿意搬到任何一个社会稳定的国家去工作。”
3月11日,欧盟和阿盟同时召开峰会,寻找对策。美国态度尚未彻底明朗,英法正积极绸缪禁飞区计划。
约什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反对派身上,他建议,国际社会应向班加西派出先遣外交小组,尽量多地接触反对派领袖,搞清楚各反对派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想通过什么手段达到什么目的后,再做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