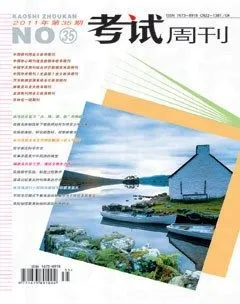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英汉“一量多物”现象分析
摘 要: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大量存在着“一量多物”现象,本文以意象图示理论为视角,解析英汉“一量多物的认知缘由,从而总结出英汉“一物多量”现象是意象图示范畴化﹑视角化和类比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一量多物”现象 意象图式理论 范畴化 视角化
1.引言
“一量多物”现象是指同一个量词可用来计量不同的事物。英语汉语和中均大量存在“一量多物”的量词使用现象。如英语中的“a flock of sheep/goats/rabbits/ birds/geese;a pack of cigarettes/hounds/sugarless gum/horse/chewing tobacco”等。汉语中的“一串钥匙/项链/葡萄/糖葫芦;几片雪花/饼干/牛肉”等。下面以意象图示理论为视角,解析英汉“一量多物的认知缘由,旨在总结出英汉“一物多量”现象是意象图示范畴化﹑视角化和类比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
2.意象图示理论
意象图示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也是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是由意象理论和图示理论演化而来。
2.1意象理论
意象是认知心理学的术语,是对事物的感知在大脑中形的表征,但这种表征不是丰富的形象,而是删除具体细节的有组织的结构,是客体或事件在大脑中的一种抽象类比物(赵艳芳,2001:131)。在认知语法中,兰盖克的意象指人们以不同的视角﹑选择不同的注意点和辖域﹑凸显不同的方面来观察某一情景,形成不同的意象,以便理解和把握某一感知到的事物和情景的能力(赵艳芳,2001:132)。后来,Langacker(1991:15)对意象概念作了细微调整,认为意象是指人们以交替的方式识解一种被认知的事物。
2.2图示理论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81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曾使用过“schema”这一术语,认为图示既与经验有关又与范畴有关,它既不是事物的具体形象,也不是经验的概念,而是一种介于概念与具体事物感性形象之间的抽象的感性结构。真正探讨这一问题的是英国心理学家Bartlett。Bartlett(1932)明确指出,人的记忆能把各种信息和经验组织为认知结构,逐渐形成常规图式,遇到新事物时,只有把这些新事物和已有的图式相联系才能被理解。
2.3意象图式理论
意象与图式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表现在图式是意象的一种,是指人类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抽象知识表征,而并不是对客观事物充满细节的心理印象。个性表现在意象更侧重于人在头脑中储存信息的形式,而图式是一种认知方式,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固化的反应模式,是一种认知结构。意象图式就是“意象”和“图式”的统称,是人在对外界的日常交往中所形成的一种简单而基本的认知结构(Ungerer & Schmidt,1996:160)。Johnson(1987:29)认为,意象图式是我们认知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结构,这种结构构建我们理解和推理的基础。我们认为,英汉两种语言中大量存在的“一量多物”现象正是意象图式的表现形式。如英语中的“a pack of cigarettes/hounds/sugarless gum/horse/chewing tobacco”等。汉语中的“一串钥匙/项链/葡萄/糖葫芦;几片雪花/饼干/牛肉”等。正式因为人类在认识这些事物给这些事物定量时,摆脱了每个事物具体而丰富的形象,反映出诸事物被抽象了的认知结构。
3.英汉“一量多物”意象图式化认知方式的具体体现
3.1范畴化
范畴化是人类认识世界诸事物的认知基础。Croft & Cruse(2004:74)认为,范畴化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活动之一,牵扯到对某一个体及某一特定经验的理解,并将这一个体或经验理解为更为抽象的事物,而这种抽象事物也包括其他实际的且具有潜在性的诸种具体化例子。范畴化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对事物的属性或特征进行认识和判断。事物之间若有相似性,便可归为一个范畴。量词所描述的各种对象由于具有客观上的相似性而形成了家族相似性。根据Wittgenstein的观点(Taylor,1995:38-39),家族相似性是指某一范畴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如同某一家族的不同成员,某个方面具有相似性,却不完全相同。“一量多物”中的量词所计量的各事物可能会千差万别,如英语中的“a flock of sheep/goats/rabbits/birds/geese ”和汉语中的“一串钥匙/项链/葡萄/糖葫芦”。但是,人们在对这些事物识解的过程中将注意力聚焦它们的外形上,使得事物成群的蜂拥状和成串状特征得以凸显。我们把与“片”搭配的名词分成核心成分(典型范畴)和外围成分,核心成分是指直接认知能够理解的搭配,而外围成分是指通过隐喻﹑转喻等转换而理解的搭配。从核心成分到外围成分是一种放射状范畴,又称“辐射状”范畴。
3.2视角化
视角指人们对事体描述的角度,涉及到观察者与事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王寅,2006:28)。我们所说的视角化,是指人在识解某一事物的特征或特性时采用某一视角,而这一视角往往会固化为识解这一事物时的习惯性视角。视角的选择与“背景”“凸显”密切相关(王寅,2006:28),如英语中的“a lump of coal/raw quartz/frozen meat/frozen rock/polished glass/gold/clay/money”和汉语中的“一头牛/骡子/猪/羊”。很明显,英民族将视角定格在成疙瘩或成团成块的一堆事物上,而不是各个事物的用途功效或其他特征。汉民族将视角聚焦于动物的头部而不是四肢,忽略了个动物的形态差异。久而久之,人们的这种视角方式被语言社团所认同,随后得到普及逐渐发胀为格式化的一线图式表征,表现为意象图示性的视角固定模式。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往往把视角聚焦在某一特征上,如汉语中可以说“一峰骆驼”,我们就是借助对骆驼驼峰的聚焦来表征骆驼的数量单位。客观事物某一特征的凸显正是由于这一特征得到了视角聚焦。所以,视角化是认知凸显的前提,而认知凸显是视角化的结果。
3.3类比思维
在根本不同的事物被范畴化为同一范畴并接受同一量词计量时是类比思维这一认知机制将我们的思维由一事物推及另一事物。英语中的“lump”可以计量:固体事物,如“gold/sugar/rock/meat”也可以计量抽象事物,如“vanity/probability/creativity”。汉语中的量词“缕”可以表示细的东西,如“一缕麻绳/炊烟”也可以表示抽象事物如“一缕哀愁/相思/香气”。但是,类比思维往往就有或然性,即有可能性,但不具备确定性。如“soap”可以类比出“a cake of soap”也可以类比出“a lump of soap”、“a loaf of soap”和“a slice of soap”。汉语中“狗”可以类比出“一只狗”、“一条狗”和“一群狗”。
4.结语
Langacker(1991:164)指出:虽然量词系统表征了各种千差万别的语义范畴,如有灵性﹑坚硬度﹑数量﹑社会地位等,但形状也许是最具有典型性的,反映出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不论是英语还是汉语,人们在使用量词计量事物时,都选用某一视角,将聚焦点放在事物最具明显感知的外形上,而事物之间外形的相似性为人类的类比思维创造了客观条件,从而产生了英汉语中“一量多物”现象。
参考文献:
[1]Bartlett,F.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
[2]Croft,W. & Cruse,D.Cognitive Linguistics[M].Cambridge:CUP,2004.
[3]Johnson,M.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Reason and Imagination[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4]Langacker,R.W.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Ⅱ:Descriptive Application[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5]Taylor,J.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M].Oxfor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6]Ungerer,F. & Schmidt,H.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London:Longman,1996.
[7]褚佩如,金乃逯.汉语量词学习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刘子平.汉语量词词典[M].内蒙古: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
[9]王文斌.汉英“一量多物”现象的认知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4).
[10]王寅.认知语法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1]朱晓军.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个体量词搭配——以条为例[J].语言与翻译,2006,(4).
[1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